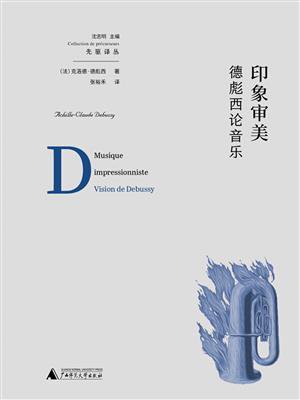国家歌剧院

国家歌剧院是人所皆知的,至少也是久闻其名的。看到它仍是一成不变的老样子,我甚感遗憾。对一个不明真相的过路人来说,它总像个火车站;一旦走进去,又会错以为走进了土耳其澡堂子。
国家歌剧院继续在上演一些怪腔怪调的玩意儿,花钱去听的人士就把这称为音乐……这些人是丝毫信不得的。
这座歌剧院,由于享受国家的特殊待遇和津贴,什么玩意儿都上演。演什么已如此无关紧要,以至于歌剧院设有精致豪华的“客厅式包厢”。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包厢比较舒服,可以完全不再听音乐——这是借以聊天的、最新式的客厅。
我说这些话,丝毫无意于攻击经理们的办事才干,因为我确信,遇到顽固不化的官僚主义墙壁,最良好的愿望也会碰得粉碎。这墙壁既牢固又森严,任何启发性的亮光也透不进去。况且,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除非来一次革命,尽管革命家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宏大的建筑物。或许人们希望失一次大火,只要大火不过于盲目,不殃及那些确实无辜的好人。
这地方对别人的意见故意规避,不闻不问。不过,我们在改变这种态度的同时,还是可以上演一些好东西的。我们不是可以在那里完整地上演瓦格纳的四部连台本歌剧吗?早就可以这样做了。首先,这样做,我们也算了了一桩心事,拜罗伊特的朝圣者们再也不会用他们的见闻来烦我们了……演出《名歌手》,很好;演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更好。(肖邦动人的心声出现在这部作品的一些紧要关头,并驾驭作品的感情。)
不把我们的牢骚扯得离题太远,让我们来看看歌剧院是如何为我国的歌剧发展服务的。
歌剧院上演了雷依埃的许多作品,其成功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有些人,他们观看风景,无动于衷,就像反刍动物那样;同样是这些人,在听音乐时耳朵里塞了棉花……
圣—桑
 以不知改悔的老交响乐家的心灵写过一些歌剧。难道这就是未来的人继续欣赏他的作品的理由吗?
以不知改悔的老交响乐家的心灵写过一些歌剧。难道这就是未来的人继续欣赏他的作品的理由吗?
马斯奈看来已经成了他的贵妇人听众拍扇子的牺牲品。扇子拍得噼里啪啦响,经久不息地为他喝彩。马斯奈竭尽全力,想在他的名字上留住那些香喷喷的扇面儿的跳动。可惜,这等于是把一群野蝴蝶变成家蝴蝶……也许他缺少的只是耐心,并且不懂得“沉默”的价值……他对当代音乐的影响是很显然的,但有些人多亏了他的影响却不承认他的影响。他们巧舌如簧,为自己辩解……真是不要脸!
还有许多其他歌剧,一一列举会令人乏味。我们也许可以记住布尔果—迪古德莱
 的《塔玛尔》。该剧虽然受欢迎的程度平平,但前景如何,现在还难以预料。
的《塔玛尔》。该剧虽然受欢迎的程度平平,但前景如何,现在还难以预料。
在多得不可胜数的蹩脚芭蕾舞剧中,有一部作品可称得上是佳作,即爱德华·拉罗
 的《纳姆娜》。不知哪个阴险狠毒之人将其打入了冷宫,以致再也无人问津……对音乐作品来说,这是很可悲的。
的《纳姆娜》。不知哪个阴险狠毒之人将其打入了冷宫,以致再也无人问津……对音乐作品来说,这是很可悲的。
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没有任何创新的尝试。有的只是一种工厂的轰鸣,没完没了的重复。好像音乐进了歌剧院就穿上了规定的制服,犹如服刑的劳役犯穿上了号衣。音乐在歌剧院里也变成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规模庞大得不切实际,这就好比那(两翼合抱的)著名“大台阶”,透视的误差或者过多的装饰细节,最终都会使其看上去显得……狭小。
* * *
这是众多歌剧中的一个……历史题材歌剧,既然讲的是暗杀纪兹公爵的故事。
 首先,这并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因此没有必要加上音乐来让我们回顾它。此外,当时的人衣品很差。男人似乎系着不雅观的救生腰带,女人的腰身长在最合理的欲望最不想看到的地方。如果有人真想把歌剧变成历史课,为什么不努力挖掘一些不那么被滑稽可笑的政治阴谋玷污的情节呢?(我想指出,路易—菲利普时期是一块尚未开发过的,但极其肥沃的土地……)乔治·俞
首先,这并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因此没有必要加上音乐来让我们回顾它。此外,当时的人衣品很差。男人似乎系着不雅观的救生腰带,女人的腰身长在最合理的欲望最不想看到的地方。如果有人真想把歌剧变成历史课,为什么不努力挖掘一些不那么被滑稽可笑的政治阴谋玷污的情节呢?(我想指出,路易—菲利普时期是一块尚未开发过的,但极其肥沃的土地……)乔治·俞
 先生为这个情节谱写了太多的音乐,以致歌剧的唱词听不见了。唱词看来曾受到令人难忘的大才子、一对活宝布法尔和白居榭
先生为这个情节谱写了太多的音乐,以致歌剧的唱词听不见了。唱词看来曾受到令人难忘的大才子、一对活宝布法尔和白居榭
 的启发。
的启发。
* * *
瓦格纳给我们留下了种种让音乐适应戏剧的方法,可是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些方法没有任何用处。出于特殊的原因,他为那些在分谱中寻不到方法的人制定了“主导主题”,这很好,可以使主导主题发展得快一些……比较严重的是,他使我们习惯于让音乐卑躬屈膝地为剧中人物负责。就此情况,我想说明,在我看来这是当今戏剧音乐状态混乱的主要原因。乐曲有节奏,节奏的神秘力量支配乐曲的发展;内心的冲动有另一种节奏,这种节奏本能地比较笼统,并服从各种各样事件的支配。这两种节奏的齐头并进,就会产生无休止的冲突:要么音乐气喘吁吁跟在人物后面追赶,要么人物在一个音符上停顿下来,让音乐来追赶他。这两种力量奇迹般齐头并进的情况也是有的。瓦格纳就曾有几次实现过这种奇迹般的齐头并进,他可以此为荣。但这种齐头并进只是偶然的巧合,在更多的情况下不过是表现笨拙和令人失望罢了。总之一句话,把交响乐形式用于戏剧情节,很可能最终扼杀了戏剧音乐,而不是如人们在瓦格纳显然统治了歌剧舞台的时候得意扬扬地宣布的那样,发展了戏剧音乐。
左拉先生和布吕诺先生的歌剧借助了许多象征性的符号。我承认,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象征性符号。人们似乎忘了,最重要的还是音乐。自然,符号会引出“主导主题”。这样作品又不得不塞满反复出现的和不顾一切要让人家听见的短小乐句。总之,认为某个连续出现的和弦将表达某种感情,某个乐句将表达某个人物,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按图索骥的把戏。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这里,我是对布吕诺先生说的。我认为,凭他的想象力是能够找到妙招的。在所有音乐家中,他是对因循守旧颇为蔑视的人。他运用和声从不考虑作曲规则上的音响效果。他首创的旋律的连接,有人轻率地称为“怪异”,其实那只不过是“不常见”而已。我觉得,这出戏的第三幕是最成功的。音乐震撼人心,使人有断肠之痛,并且比常见的悲剧情节走得更远。情节的发展本可以快一些,不要停留在对两个人物嫉妒程度的心理讨论上。此外,音乐不小心挤了台词,好像跟台词说:“请不要挡我的路,你明明知道我比您强。”这样就一切都布置好了……我不大喜欢吕吕这个人物的处理方法和他所代表的符号。本应该有些特殊的东西,梦幻般地处于整个音乐氛围之外的东西,不是吗?我明显地感到了魅力,但没有感到深度,不断更换的布景也没有能够吸引我。
看样子,我似乎对这部作品有所保留。其实,对这部作品持保留意见是很难的,因为这是一部要么取、要么舍的作品。要喜欢,缺点、优点一起喜欢。否则,你会又一次觉得作品不可忍受。总之,作品讲的是一个在痛苦中寻找真理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不同寻常的。现在有那么多所谓的“大师”,在虚构的传统中只寻求“凤毛麟角”,而这传统是一个比他们所有人都伟大的人遗传下来的。
我没有资格评论爱弥儿·左拉先生的诗体唱词。我觉得,他写“情景”要强于写严格意义上的歌词。
我不懂人们为什么再次祝贺阿贝尔·卡雷
 先生实现了奇迹。有人曾经想到寄张贺卡给“统治宇宙的那位”,祝贺他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绚丽的日落吗?……
先生实现了奇迹。有人曾经想到寄张贺卡给“统治宇宙的那位”,祝贺他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绚丽的日落吗?……
戴娜小姐演的悲剧角色很合我的心愿,罗奈小姐演得美轮美奂,吉罗东小姐是奇珍异宝,加上波尔邦先生、杜弗兰先生和马海侠先生,这就是演员队伍的全部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