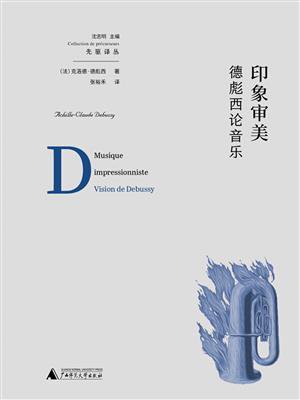小议迷信种种和歌剧一出

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那迷人的古老森林,因此在秋色斑驳的乡下多待了几天。那儿,黄叶纷飞,为树木送终;祷钟频响,催田野入睡。这境界发出轻柔而恳切的声音,劝人忘却一切。落日独自归寝。没有一个农夫想到在它面前驻足观赏。牲畜和农夫默默无闻地劳动一天之后,安详平静地向庄园走去。这种默默无闻的劳动给人一种特殊的美感:它既不恳求别人的鼓励,也不恳求别人的批评……我远远地离开了有关艺术的讨论。在那些有关艺术的讨论中,大人物的名字有时会成为骂人的“粗话”。我已经把那为“首演”而炒作出来的、令人厌恶的狂热,忘得一干二净。我独自一人,无所牵挂,怡然自得。这期间,我从不曾听人谈论音乐,可我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更爱音乐。音乐的美,完整地呈现在我的面前,而不是呈现在交响曲或歌剧的鸡零狗碎的片段里,狂热的、局部的片段里。我有时想起克罗士先生。他外貌端庄,瘦骨嶙峋,随便把他放在什么景色里也不会损害景色的轮廓。然而,我受了迷信城市的驱使,终于离开恬静的欢娱回来了。对城市的迷信使许多人情愿在城里被碾死,也不肯脱离那种“运动”,再说,他们也都是这种“运动”
 上受苦的、不自觉的齿轮。一个阴冷的黄昏,我正沿着美丽平坦的马泽布大街前行,忽然瞥见了克罗士先生瘦削的身影。他以特殊的方式允许我挨近他,我也没有说句打招呼的话。他向我扫了一眼,让我放心,表示同意我这样做,并立即用他那哮喘病人的低沉嘶哑的嗓子说起话来。生硬的语调更加重了嗓子的低沉和嘶哑,但奇怪的是,他说的一字一句都能使人听得很清楚……
上受苦的、不自觉的齿轮。一个阴冷的黄昏,我正沿着美丽平坦的马泽布大街前行,忽然瞥见了克罗士先生瘦削的身影。他以特殊的方式允许我挨近他,我也没有说句打招呼的话。他向我扫了一眼,让我放心,表示同意我这样做,并立即用他那哮喘病人的低沉嘶哑的嗓子说起话来。生硬的语调更加重了嗓子的低沉和嘶哑,但奇怪的是,他说的一字一句都能使人听得很清楚……
“在法国引以为荣的建制中,您知道有哪个比设立罗马奖学金更可笑的事吗?我知道,这件事人家已经谈得很多了,写成文章的则更多。可是,既然罗马奖学金仍然存在,并将以其显而易见的荒谬主张和那种可悲的顽固继续存在,将说的和写的都没有明显的效果……不是吗?”我壮起胆子回答他说,罗马奖学金的设置
 ,可能在某些艺术科系里已经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所以才长盛不衰……获得或没有获得罗马奖学金,解决了知道人家是否有才能的问题。虽说这不太可靠,但这至少比较方便,并为公众舆论准备了一本易于管理的账目。克罗士先生从牙缝里发出嘘声,我想,这是嘘他自己……“对啊,您已获得过罗马奖学金……请注意,先生,我完全同意,人们为青年人到意大利,甚至到德国,安安静静地游学提供了方便,但是为什么把游学限制在这两个国家呢?尤其是那张不幸的证书,为什么会把年轻人跟肥肥的牲口等同起来呢?
,可能在某些艺术科系里已经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所以才长盛不衰……获得或没有获得罗马奖学金,解决了知道人家是否有才能的问题。虽说这不太可靠,但这至少比较方便,并为公众舆论准备了一本易于管理的账目。克罗士先生从牙缝里发出嘘声,我想,这是嘘他自己……“对啊,您已获得过罗马奖学金……请注意,先生,我完全同意,人们为青年人到意大利,甚至到德国,安安静静地游学提供了方便,但是为什么把游学限制在这两个国家呢?尤其是那张不幸的证书,为什么会把年轻人跟肥肥的牲口等同起来呢?
“此外,法兰西学院的那些评委先生,以学院派的冷漠态度,在所有参赛的年轻人当中指定谁将是艺术家。这种学院派的冷漠以其憨直使我大为惊讶。他们怎么知道谁会是艺术家呢?他们有把握自己就是艺术家吗?他们从哪里来的权力操纵神秘莫测的命运呢?真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好还是使用简单的‘抓阄’的办法。谁知道呢?有时候运气是那么灵验……可是不行,必须寻找其他办法……不要根据命题的作品和某种形式的作品来判断,那样是无法知道这些青年人是否懂得音乐家职业的……假如一定要给他们发个什么东西,那就发给他们一张‘高校肄业文凭’,而不是‘有想象能力’的证书,徒然令人好笑!一旦办完了发证书的手续,就让他们到欧洲各国去旅游,让他们自己给自己选择导师,或者,如果碰得到的话,选择一个能告诉他们艺术不一定局限在国家资助的纪念性建筑物里的老实人!”
克罗士先生停了下来,费力地咳了一阵,并向熄灭了的雪茄烟表示歉意……他指着雪茄烟说道:“我们在争论,它却熄掉了,以此讥讽我话说得太多,并警告我,它最终会用‘聚集起来的烟灰’把我埋葬掉。确实,这倒是个不错的泛神论的火葬场,这也委婉地说明,一个人不应该自以为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该把生命的短促看成最为有益的教训……”然后,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说道:“上星期天我去听拉姆赫音乐会了。那天有人为你的乐曲喝倒彩。你应该感谢这些人。他们不辞劳苦,拿钥匙当口哨吹,喝倒彩,已经是够热情的了。一般说,钥匙是不能当作战斗武器的,因为人们正确地视钥匙为家庭用具。肉店里的小伙计曲起指头吹口哨的方式要值得推崇得多……(人们真是活到老学到老)遇到这种场合,舍维雅先生再次表现出他对音乐出奇的、多种多样的理解。至于合唱交响曲,他好像一个人在进行演奏一样,因为演奏时,他运用了那样多强有力的处理手法,这就超越了人们惯常对他的称赞。”
我只能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补充说,我进行创作是为了尽可能好地、专心一意地为音乐服务,所以我的音乐作品有可能不讨某些人的喜欢,这是合乎逻辑的。这些人爱“一种音乐”爱到忠心耿耿、始终不渝的程度,即使他们已满脸皱纹或涂满脂粉!
克罗士先生继续说道:“我们谈到的这些听众是无罪的。还是怪那些艺术家吧,他们做的是件苦差事:既要为听众服务,又存心把他们维持在懒懒散散、要求不高的状态……除此之外,这些艺术家善于进行一时的战斗,这正是为了在市场争得一席之地所必须做的。可是,一旦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有了保障,他们便急剧后退,似乎在向听众表示歉意,因为曾经有劳听众承认了他们。他们决意背叛青春,躺在已经获得的成就上睡大觉。有些人献出毕生精力,探索感官世界和形式世界的不断更新,怀着已经完成了真正使命的愉快信念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人获得的光荣,他们是永远达不到的。这些人获得的,可称为‘最后’的成功,如果‘成功’一词不会因为和‘光荣’一词并列而贬低意义的话。
“最后,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举出最近的一个例子。我伤心地看到,要保持对一位艺术家的尊敬是多么困难,而这位艺术家自己也是个满腔热情、追求真正荣誉的人……先生,我讨厌感情用事!但我情愿忘记他名叫卡米耶·圣—桑!”
我简单地反驳说:“我最近看过他的歌剧《野蛮人》。”
克罗士先生以我料想不到的激动情绪继续说道:“圣—桑先生误入歧途,怎么会到这种程度呢?他是个对世界音乐最了解的人。他怎么忘了是他让我们认识和接受了李斯特奔放的天才和他对老巴赫的崇拜?
“为什么会有这种谱写歌剧的病态需要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从路易·加莱
 跌到维克多里安·萨杜
跌到维克多里安·萨杜
 水平的病态需要呢?这是在传播应该‘搞歌剧创作’的可恨的错误,是永远不会跟‘搞音乐创作’协调一致的。”
水平的病态需要呢?这是在传播应该‘搞歌剧创作’的可恨的错误,是永远不会跟‘搞音乐创作’协调一致的。”
我试图用这类胆怯的异议来反驳他:“比起其他许多你没有提到的歌剧来,难道《野蛮人》要更糟吗?”以及:“难道我们因此就该忘记圣—桑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吗?”
克罗士先生蓦然打断了我的话:“因为这部歌剧出自圣—桑先生的手笔,所以比其他歌剧更糟糕。为了对他负责,更为了对音乐负责,他不该写作这部歌剧。这部歌剧里什么都有,甚至有被人称赞为古色古香的普罗旺斯的土风舞。其实那不过是在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得成功的开罗街
 的陈旧翻版而已。说是古色古香,我看不见得。整个歌剧由于受剧本的影响,极力追求效果。脚本里的唱词有些是郊区用的‘语言’和一些——毋庸说——会使音乐变得可笑的情节。歌唱演员的滑稽表情,沙丁鱼罐头似的场面调度(这是国家歌剧院死死抱住不放的传统),扼杀了戏剧和一切艺术的希望……难道没有一个喜欢圣—桑的人对他说,他写的音乐作品已经够多了,最好还是去修炼修炼他那晚到的探索的志向吗?”克罗士先生点燃另一支雪茄烟,以告别的口吻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想糟蹋这支烟……”由于已经走过了我的住宅很远,我便转身往回走,脑子里思考着克罗士先生不偏不倚的指责。有些人我们过去非常喜爱,他们稍有改变,就被我们视为背叛。想来想去,克罗士先生的指责里包含了一些我们对这些人的气恼。我也试着回想《野蛮人》首演那天晚上圣—桑先生的样子。我记得在向他致敬的掌声里,也有向交响诗《死神之舞》首演喝倒彩的声音。我相信,这一记忆是不会令圣—桑先生不愉快的。
的陈旧翻版而已。说是古色古香,我看不见得。整个歌剧由于受剧本的影响,极力追求效果。脚本里的唱词有些是郊区用的‘语言’和一些——毋庸说——会使音乐变得可笑的情节。歌唱演员的滑稽表情,沙丁鱼罐头似的场面调度(这是国家歌剧院死死抱住不放的传统),扼杀了戏剧和一切艺术的希望……难道没有一个喜欢圣—桑的人对他说,他写的音乐作品已经够多了,最好还是去修炼修炼他那晚到的探索的志向吗?”克罗士先生点燃另一支雪茄烟,以告别的口吻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想糟蹋这支烟……”由于已经走过了我的住宅很远,我便转身往回走,脑子里思考着克罗士先生不偏不倚的指责。有些人我们过去非常喜爱,他们稍有改变,就被我们视为背叛。想来想去,克罗士先生的指责里包含了一些我们对这些人的气恼。我也试着回想《野蛮人》首演那天晚上圣—桑先生的样子。我记得在向他致敬的掌声里,也有向交响诗《死神之舞》首演喝倒彩的声音。我相信,这一记忆是不会令圣—桑先生不愉快的。
附记:《白皮文艺双月刊》的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瓦格纳论贝多芬》一书的精美译本。对喜爱瓦格纳的人来说,这个译本又一次提供了崇拜瓦格纳的机会;对不喜欢瓦格纳的人来说,瓦格纳在书中亲自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理由……不管从什么角度看,这足以说明,亨利·拉斯维涅先生的译本是多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