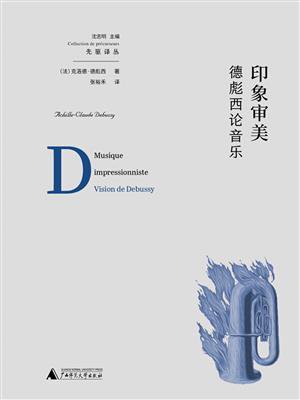圣—莫尔的莫扎特

《蓝色小报》最近告诉我们,有一个稍稍早熟的音乐天才,被称为“新莫扎特”。这位小天才名叫皮埃尔·夏农,生于1893年,年龄在12岁左右。莫扎特在这个年纪已经写了一出歌剧,不错,手笔很稚嫩,但毕竟写出来了,这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做到的。(幸好不是所有孩子,我的上帝!)到目前为止,小皮埃尔·夏农只得到一张跟乔治·桑的画像配在一起的莫扎特的画像(为什么给他这样一张调情画像呢?这只能使那位可怜的肖邦恼火
 ),写过一首《啊,救世主!》——“在圣—莫尔教堂演奏,获得巨大成功”,他父亲说。
),写过一首《啊,救世主!》——“在圣—莫尔教堂演奏,获得巨大成功”,他父亲说。
不管怎样,有一个小神童,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漠不关心的。一般来说,这样的天才只有与我们竞争的邻国才有。因此,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一点上又占了优势,是很令人感到宽慰的。虽说这显然不能认为可以补偿我们失去的两个省
 ,但毕竟是回事儿。我们这个时代好似一个有点儿熟透了的水果,或者是因为气温太高。我们从极端的复杂走向最彻底的无能。我们不肯花任何代价来接受一位学派领袖
,但毕竟是回事儿。我们这个时代好似一个有点儿熟透了的水果,或者是因为气温太高。我们从极端的复杂走向最彻底的无能。我们不肯花任何代价来接受一位学派领袖
 (这也许是绝对无用的,但肯定是合适的)。最后,我们对自己没有很大的信心,既然我们到国境以外的邻居那儿寻找我们的发展方向!一个年轻天才来整顿秩序,重新鼓起我们已经失去的信心,也许是需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我希望小皮埃尔·夏农做个给我们指路的人。但我希望他不要有太大的名声……我们不想知道《蓝色小报》的编辑是如何发现他的,看到这么稚嫩的脑袋周围如此闹闹哄哄,我们真放心不下。由于获得成功太过容易,有些事会使他思想混乱,或者使他忘记未来的光荣使命。
(这也许是绝对无用的,但肯定是合适的)。最后,我们对自己没有很大的信心,既然我们到国境以外的邻居那儿寻找我们的发展方向!一个年轻天才来整顿秩序,重新鼓起我们已经失去的信心,也许是需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我希望小皮埃尔·夏农做个给我们指路的人。但我希望他不要有太大的名声……我们不想知道《蓝色小报》的编辑是如何发现他的,看到这么稚嫩的脑袋周围如此闹闹哄哄,我们真放心不下。由于获得成功太过容易,有些事会使他思想混乱,或者使他忘记未来的光荣使命。
在一个人拥有的天赋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未知数,并且要(好像是出于一种谨慎)害怕承认有才,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否则就会得罪令人敬畏的神灵——神灵在我们额头上打上被上帝选中的标记,或者比较简单地注上“跟大家不同的人”。——再说,小皮埃尔的父亲,已经抱怨他儿子没有一架好钢琴,一星期只能去一次音乐学院!……这两点不足之处是很容易弥补的:让他儿子不要去音乐学院,把交通费省下来,用来买一架比较好的钢琴,既实用又快乐。(我不知道是否被大家正确理解了。)
* * *
上星期一,民族音乐社在普莱伊尔大厅举行音乐会,我们这时代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的里斯勒先生
 和罗奈太太扮演主角。先是里斯勒先生和小贝纳布勒先生演奏一首贝多芬为钢琴和法国号写的奏鸣曲。这也是法国号和奏鸣曲的早期作品。而且,你知道的,“法国号的声音在普莱伊尔大厅里面听起来是多么的苍凉”!
和罗奈太太扮演主角。先是里斯勒先生和小贝纳布勒先生演奏一首贝多芬为钢琴和法国号写的奏鸣曲。这也是法国号和奏鸣曲的早期作品。而且,你知道的,“法国号的声音在普莱伊尔大厅里面听起来是多么的苍凉”!
接下去演奏的是撒马宙伊先生的钢琴组曲……作品充满了诚意,但,我觉得不够老练!我的意思是说,作品还有点儿生涩,而撒马宙伊先生急于拿出来示人。该作品有许多万桑·丹第
 先生的影子。这样一位大师不仅是值得尊重的,而且可以让我们对他的弟子萨马宙伊先生以后的作品寄予厚望。
先生的影子。这样一位大师不仅是值得尊重的,而且可以让我们对他的弟子萨马宙伊先生以后的作品寄予厚望。
罗奈太太怀着深厚的感情演唱了肖松
 根据梅特林克的诗集《暖房》创作的一组歌曲。这些歌曲都是一个个充满沉思遐想的小故事,肖松用音乐加以诠释,并不使之变得沉重。我们甚至希望在他极富个性的音乐诠释里,凡是让人感到激动的地方,能留下较多想象的空间。最后,保尔·杜卡根据拉莫的一个主题写的变奏曲,再次表明他具有高超的驾驭写作的技巧——在那么多装饰性的乐句里,有时候拉莫本人可能也找不到自己的主题。
根据梅特林克的诗集《暖房》创作的一组歌曲。这些歌曲都是一个个充满沉思遐想的小故事,肖松用音乐加以诠释,并不使之变得沉重。我们甚至希望在他极富个性的音乐诠释里,凡是让人感到激动的地方,能留下较多想象的空间。最后,保尔·杜卡根据拉莫的一个主题写的变奏曲,再次表明他具有高超的驾驭写作的技巧——在那么多装饰性的乐句里,有时候拉莫本人可能也找不到自己的主题。
可是我想,杜卡仅仅是想解开难以捉摸的谜吗?他解开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谜。所以,在这些《变奏曲》中,我们应该只看旋律奇妙的变化,我讲的是真实的想法。我宁愿要杜卡的变奏,而不要拉莫的主题。
在这么多风格迥异的作品中,里斯勒先生的演技千变万化,熟练准确,令人十分钦佩。
* * *
最近担任拉姆赫
 交响乐团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跟《蓝色多瑙河》的作者约翰·施特劳斯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于1864年出生在慕尼黑,他父亲是王室的乐师。他在年轻的德国几乎是唯一别具一格的音乐家。他指挥乐队时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很像李斯特;他把音乐支撑在文学之上的用心,又很像我国的柏辽兹。他的交响诗的标题——《堂吉诃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调皮捣蛋的蒂尔》即是证明。在最后这首交响诗里,我们没有料到音乐竟能叙述任何情节,乐队竟能跟任何文本的夸张的插图媲美。因此,乐曲里单簧管描写着疯狂的抛物线,小号总是捂着号口,法国号预料它们又要打闷喷嚏,连忙说了句客气话:“长命百岁!”大鼓敲得“嘣嘣”响,好像在为马戏团小丑的脚步伴奏;嘎嘎作响的转鼓,以其集市狂欢的吵闹声压倒了一切。理查·施特劳斯先生的艺术,肯定并不总是这么特别和异想天开,但他肯定是用五颜六色的形象来思维的。他好像是用乐队来描绘他乐思的线条。这是一种很少使用的、不同寻常的方法。此外,在作品中,理查·施特劳斯先生有一种完全独特的展开乐思的方式。这不再是巴赫或贝多芬的严格的结构方式,而是一种节奏色彩的展开。他沉着镇静,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调性重叠在一起,丝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撕心裂肺的”噪声,而只考虑可能有的“生动活泼的”效果。
交响乐团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跟《蓝色多瑙河》的作者约翰·施特劳斯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于1864年出生在慕尼黑,他父亲是王室的乐师。他在年轻的德国几乎是唯一别具一格的音乐家。他指挥乐队时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很像李斯特;他把音乐支撑在文学之上的用心,又很像我国的柏辽兹。他的交响诗的标题——《堂吉诃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调皮捣蛋的蒂尔》即是证明。在最后这首交响诗里,我们没有料到音乐竟能叙述任何情节,乐队竟能跟任何文本的夸张的插图媲美。因此,乐曲里单簧管描写着疯狂的抛物线,小号总是捂着号口,法国号预料它们又要打闷喷嚏,连忙说了句客气话:“长命百岁!”大鼓敲得“嘣嘣”响,好像在为马戏团小丑的脚步伴奏;嘎嘎作响的转鼓,以其集市狂欢的吵闹声压倒了一切。理查·施特劳斯先生的艺术,肯定并不总是这么特别和异想天开,但他肯定是用五颜六色的形象来思维的。他好像是用乐队来描绘他乐思的线条。这是一种很少使用的、不同寻常的方法。此外,在作品中,理查·施特劳斯先生有一种完全独特的展开乐思的方式。这不再是巴赫或贝多芬的严格的结构方式,而是一种节奏色彩的展开。他沉着镇静,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调性重叠在一起,丝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撕心裂肺的”噪声,而只考虑可能有的“生动活泼的”效果。
所有这些特点,在交响诗《英雄的一生》中达到了顶峰。理查·施特劳斯先生是第二次在巴黎演奏这部作品了。因其近乎平庸或近乎夸张的意大利风格,人们可以不喜欢某些乐思的开端,但过一会儿,人们就被乐队神奇的变化所吸引,然后又被疯狂的速度所吸引;人们被卷入其中,沉浸在里面,要多久有多久。人们不再有力气控制自己的感情。人们甚至发现,这首交响诗超出了人们听此类乐曲演奏所常有的耐心。
这又是一本画册,甚至是电影……应当说,以如此一贯的努力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人,几乎就是个天才。
音乐会一开始演奏了他的幻想交响曲《意大利》,共四个乐章(年轻时的作品,我想)。
 理查·施特劳斯未来创作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已见端倪。我觉得乐曲的展开稍微长了点儿,而且也没有特色。然而第三乐章,题为《苏莲托港湾》,非常好听,色彩鲜艳……接下去是从他的近作歌剧《节日夜晚的篝火》中抽出的一个爱情场面。这样脱离作品的背景,使这场戏失去很多东西。由于节目单上没有任何的说明,曲子的布局完全无法理解。这样一段曲子像奔腾咆哮的洪流,对爱情场面来说,似乎很惊心动魄!也许在歌剧里,这奔腾咆哮的洪流可能是有道理的。对音乐剧来说,这也许是上演一些新东西的机会。因为我不认为,上演年轻意大利的现代歌剧,可使我们学到任何东西。这些意大利的现代歌剧,都是法国音乐作品的巧妙的或粗劣的仿制品,除非是相反。这种误会我已经谈过了,再强调也许就无聊了。
理查·施特劳斯未来创作的独特个性在这里已见端倪。我觉得乐曲的展开稍微长了点儿,而且也没有特色。然而第三乐章,题为《苏莲托港湾》,非常好听,色彩鲜艳……接下去是从他的近作歌剧《节日夜晚的篝火》中抽出的一个爱情场面。这样脱离作品的背景,使这场戏失去很多东西。由于节目单上没有任何的说明,曲子的布局完全无法理解。这样一段曲子像奔腾咆哮的洪流,对爱情场面来说,似乎很惊心动魄!也许在歌剧里,这奔腾咆哮的洪流可能是有道理的。对音乐剧来说,这也许是上演一些新东西的机会。因为我不认为,上演年轻意大利的现代歌剧,可使我们学到任何东西。这些意大利的现代歌剧,都是法国音乐作品的巧妙的或粗劣的仿制品,除非是相反。这种误会我已经谈过了,再强调也许就无聊了。
理查·施特劳斯先生既没有那绺折腾来折腾去的头发,也没有癫痫病人的手势。他身材高大,并且有那些大探险家豪迈、坚定的气度:嘴上挂着微笑,穿过野蛮部落。也许应该有点儿这种震撼公众文明的气概吧?他的面孔还是音乐家的面孔,但眼神和姿态却是一位尼采所说的那种“超人”的眼神和姿态;尼采应当是他的老师,使他精力充沛……他对那种愚蠢的多愁善感的蔑视,一定也是跟这位老师学到的。而且他所要的,是音乐不要继续没完没了地、勉勉强强地照亮我们的黑夜,而是音乐要取代太阳。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中确有太阳。但我们也能看到,大部分听众不喜欢这种太阳,因为,音乐行家们,而且是著名的音乐行家们,毫不含糊地发出了不耐烦的信号。不过,这并不能阻止听众热烈鼓掌,向理查·施特劳斯致敬!
* * *
这是一场很精彩的音乐会:法国音乐和波兰音乐友好携手,同台演出(先生,波兰万岁!)。当然我不跟你们谈法国音乐。代表法国音乐的是拉罗、马斯奈
 、布吕诺。我列举的这些名字,就可不用赘述了。至于波兰音乐,我至今为止没有什么特别的偏爱!在所有波兰作曲家当中(我们并不想个个都认识),斯托约夫斯基
、布吕诺。我列举的这些名字,就可不用赘述了。至于波兰音乐,我至今为止没有什么特别的偏爱!在所有波兰作曲家当中(我们并不想个个都认识),斯托约夫斯基
 的D小调交响曲获得过帕德雷夫斯基
的D小调交响曲获得过帕德雷夫斯基
 奖。人家告诉我们,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受到欢迎和承认。如果大家愿意,我也遵循节目单上给我提供的这个评价。至于其他曲目,我很想说,诺斯考夫斯基的《大草原》有动感:哥萨克人纵马腾跃,旋转,发出呼叫,像凶悍、好战的阿帕奇印第安人。博斯卡太太唱得非常好,波兰乐队指挥姆利纳斯基先生,理所当然,汗湿了衬衫的领子。
奖。人家告诉我们,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受到欢迎和承认。如果大家愿意,我也遵循节目单上给我提供的这个评价。至于其他曲目,我很想说,诺斯考夫斯基的《大草原》有动感:哥萨克人纵马腾跃,旋转,发出呼叫,像凶悍、好战的阿帕奇印第安人。博斯卡太太唱得非常好,波兰乐队指挥姆利纳斯基先生,理所当然,汗湿了衬衫的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