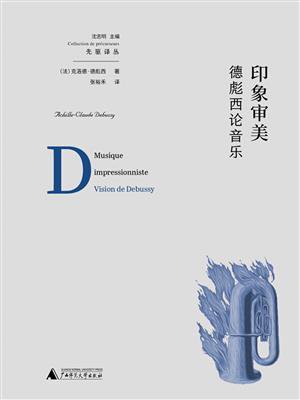爱德华·格里格

爱德华·格里格
 是那位在“……事件”
是那位在“……事件”
 期间对法国很不友好的斯堪的纳维亚作曲家。他在一封回答科洛纳先生邀请他来指挥乐队的信中,气呼呼地声明他不再愿意踏上一个如此不懂自由的国家的领土……于是法国只好放弃格里格先生而另请他人。可是好像格里格先生少不了法国,既然今天他愿意……既往不咎,越过国界来指挥过去被这位斯堪的纳维亚人瞧不起的法国乐队……再说,事件已经平息,格里格先生也快60岁了!上了年纪的人,怒火必然平息,变得心平气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事态的变化,权衡事态变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其次,尽管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毕竟是人嘛……巴黎人对待外国人是如此的友好热情,要想拒绝巴黎人的这种热情是很难的。甚至有的人没有格里格先生那样响亮的名声,也一样受到友好热情的接待。
期间对法国很不友好的斯堪的纳维亚作曲家。他在一封回答科洛纳先生邀请他来指挥乐队的信中,气呼呼地声明他不再愿意踏上一个如此不懂自由的国家的领土……于是法国只好放弃格里格先生而另请他人。可是好像格里格先生少不了法国,既然今天他愿意……既往不咎,越过国界来指挥过去被这位斯堪的纳维亚人瞧不起的法国乐队……再说,事件已经平息,格里格先生也快60岁了!上了年纪的人,怒火必然平息,变得心平气和,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事态的变化,权衡事态变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其次,尽管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毕竟是人嘛……巴黎人对待外国人是如此的友好热情,要想拒绝巴黎人的这种热情是很难的。甚至有的人没有格里格先生那样响亮的名声,也一样受到友好热情的接待。
有一阵子,我确实以为,我能够告诉大家的只是一些关于格里格音乐的色彩印象!……首先,经常光顾科洛纳音乐会的挪威人增加了三倍。我们从来不曾有机会看到这么多的红头发和怪模怪样的大礼帽(克里斯蒂安纳
 的时装看来有点落伍了)。其次,音乐会开始的第一个节目是一首题为《秋》的序曲。与此同时,一群格里格的欣赏者由于过分热情而大声喧哗,结果被一位与其说是爱好音乐不如说是勤奋负责的警务长赶到塞纳河的堤岸马路上去乘风凉了。现在人们害怕矛盾的态度吗?
的时装看来有点落伍了)。其次,音乐会开始的第一个节目是一首题为《秋》的序曲。与此同时,一群格里格的欣赏者由于过分热情而大声喧哗,结果被一位与其说是爱好音乐不如说是勤奋负责的警务长赶到塞纳河的堤岸马路上去乘风凉了。现在人们害怕矛盾的态度吗?
问题不该由我来回答,但是格里格有一阵子招来了一些最令人不快的形容词,而我当时正忙着跟巴黎市的显赫而威严的保安警察谈判,没能听到这首曲子。
我终于见到了格里格先生!……从正面看上去,他的样子像天才的摄影师。从背面看,他的发型使他很像那种叫作向日葵的植物。鹦鹉很喜欢这种植物,外省小车站上作为点缀的花圃里也常长着这种植物。格里格先生虽然上了年纪,但行动敏捷、利索;他指挥乐队兢兢业业,精雕细琢,把所有的抑扬顿挫都指挥得很清楚,感情的运用都恰到好处。
序曲(我在过道里忙着跟警察谈判没有听到)之后,是由(拜罗伊特剧院的)古布兰森太太唱的三首歌曲。第一、第二首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那是格里格模仿舒曼的作品。第三首,《天鹅》,花招比较多(而且在沙龙里很知名)。经过乐队的烹调,在竖琴的香味里掺进双簧管的柠檬汁,整个曲子浸在弦乐的汤汁里,再加上令听众情绪起伏的休止符,曲子便具有了最可靠的、让听众叫喊“再来一遍!”的配方。这是一些非常轻柔悦耳、朴实无华的歌曲,是富人区里给养病的女人唱的催眠曲……总有一个音符拖在和弦上,就好似湖面上的一朵睡莲,被月光照得厌倦了,或者是……天空中的一个小气球,被乌云挡住了去路。
 这首曲子美得无法言喻,听众不禁为之动情。法国人传统的感受力总是万无一失的,热情地要求再唱一遍。古布兰森太太唱这三首曲子时,时而轻柔,时而深沉,声音带有“大峡谷”的冷峻而崇高的忧伤,而大峡谷赋予了挪威最纯净的魅力。
这首曲子美得无法言喻,听众不禁为之动情。法国人传统的感受力总是万无一失的,热情地要求再唱一遍。古布兰森太太唱这三首曲子时,时而轻柔,时而深沉,声音带有“大峡谷”的冷峻而崇高的忧伤,而大峡谷赋予了挪威最纯净的魅力。

可是叫好声响了起来……太太们改变了她们微笑的对象……有一双妙手的普诺
 出场了。
出场了。
你们知道,听众见到普诺,就知道快要举行格里格的音乐会了……确实是这样,谁也不能像普诺那样将格里格的作品奏出那么好的效果。他凭借叫人难以置信的灵巧,挽救了乐曲中那些耍弄“花招”和“骗术”的部分。听众看到的仅仅是,这首协奏曲以舒曼的风格开始,以最佳的状态结束,堪称绝妙,但并不是一首具有个性的艺术作品。作品中处理钢琴的方式完全是传统的。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乐曲中不时出现军号的响声。一般来说,军号的响声预示一段让人如醉如痴的抒情慢板就要开始了。(军号声!……人家滥用了你的天真。)普诺总是一如既往,令人赞叹。应该看一看他回到台上来向发狂的听众致敬的样子:他用疲乏的左手挥动着手绢,用温和的、否定的手势,回答那不合人情的“再来一遍”的请求。
两首为弦乐器写的哀歌多么动人啊!特别是第二首,我们感到马斯奈的影响……(但没有马斯奈作品给人在感官上获得享受的冲动,这是马斯奈作品的特点,也是马斯奈作品让人喜爱,几乎欲罢不能的原因。)
格里格的乐曲像集市上小铺子卖的麦芽糖那样,稍稍拉长了一点儿,也许麦芽糖是粘在铺子老板的手上的,看来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吧?这两首曲子再一次重复了过去使格里格成功发迹的手法:曲子以一个不起眼的小乐句开始,然后乐句顺利地展开;半路上乐句遇着和弦的花朵,并用其装饰自己不很出众的美丽。整个曲子转调上了一层,同时运用必不可少的弱音器,然后又降回原调。接着,出现一系列原先故意“避开”的华彩乐段,乐曲渐渐减慢速度直至最终结束。听众再次如痴如狂……大家嘴里有一种玫瑰糖的既古怪又讨喜的味道,糖里可能裹着毒品啊。
实际上,这天下午最愉快的时刻是听《培尔·金特》,这是格里格为易卜生的同名诗剧写的交响组曲。交响组曲的乐思优美,节奏巧妙,感情是地地道道的挪威感情。配器的安排也比较平衡。创造性的新发现取代了对过于简单的效果的追求。这场专门演奏格里格作品的音乐会最后由古布兰森太太演唱《诸神的黄昏》的终曲来结束,简直无法解释。我白费力气寻找,也没找到把德国的艺术丰碑跟格里格的挪威伤感放在一起的理由。我没有听完就走了……吃了花色糕点之后就不吃烤牛排啦。
言归正传,还是应该以格里格来结束此文。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这次来巴黎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艺术上的新成就。他仍旧是一个把本国民间音乐运用得很巧妙的音乐家,虽然远不及巴拉基列夫
 先生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先生运用俄国民间音乐所取得的成就大。除了这一点,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比较注重效果、不大注意真正艺术的灵巧的音乐家。他在音乐上真正的启蒙老师好像是一位跟他同龄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理查·诺尔德鲁克,生来就是一个天才。当他在20岁上夭折时,已经有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了。他死得这样早十分可惜,因为一则挪威失去了一份荣誉,二则格里格失去了一个可能阻止他误入歧途的朋友的影响……此外,格里格抱有一个类似《大建筑师》(易卜生的最新剧作之一)的目的,“为孩子们建造一所房子,让他们住在里面如同住在家里一样幸福”。
先生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先生运用俄国民间音乐所取得的成就大。除了这一点,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比较注重效果、不大注意真正艺术的灵巧的音乐家。他在音乐上真正的启蒙老师好像是一位跟他同龄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理查·诺尔德鲁克,生来就是一个天才。当他在20岁上夭折时,已经有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了。他死得这样早十分可惜,因为一则挪威失去了一份荣誉,二则格里格失去了一个可能阻止他误入歧途的朋友的影响……此外,格里格抱有一个类似《大建筑师》(易卜生的最新剧作之一)的目的,“为孩子们建造一所房子,让他们住在里面如同住在家里一样幸福”。
在他昨天让我们听到的作品里,我没有感受到这个美丽形象的任何痕迹。现在我们对他的新作还一无所知,不是吗?也许他的新作就是易卜生所说的“幸福的住所”!反正格里格先生没有给我们进入幸福住所的快乐。他不辞劳苦来到法国,昨天对他的热情接待可以报答他了。我们最强烈的愿望是,将来在他用音乐建筑的房子里,我们被他认为是有资格住进去的人,即使不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适意,至少是幸福的。
* * *
终于!……美国音乐之王到了巴黎!这意味着,下星期整整一周,索萨
 先生和他的“一班人马”,将向我们展示美丽的美国音乐,以及美国上流社会消费音乐的方式。说真的,要指挥这支乐队,非得具有特殊的天赋不可。因为,索萨先生是转着身子指挥乐队的:他或者像是摇着刚洗过的生菜沥沥水,或者像是挥着扫帚扫灰尘,或者像是拍打从低音大号口飞出的蝴蝶。
先生和他的“一班人马”,将向我们展示美丽的美国音乐,以及美国上流社会消费音乐的方式。说真的,要指挥这支乐队,非得具有特殊的天赋不可。因为,索萨先生是转着身子指挥乐队的:他或者像是摇着刚洗过的生菜沥沥水,或者像是挥着扫帚扫灰尘,或者像是拍打从低音大号口飞出的蝴蝶。
如果美国音乐是唯一给难以言喻的“步态舞”伴奏的音乐,我承认,目前看来,这是美国音乐超过其他音乐的唯一优点,而索萨先生是无可争议的美国音乐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