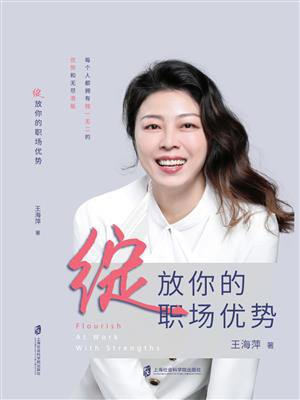二、我们为自己的独特优势而生
有机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是幸福的,人生是丰盛的。然而,现实中大部分人可能仍走在探寻自己优势的路上。不仅今天的人们如此,历史上的先人们也曾一样地努力自我探索。例如,在希腊德尔菲的太阳神庙上就镌刻着三条箴言,其第一条就是“认识你自己”。这说明认识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苏格拉底则把它上升为哲学层面的议题;中国人也说“四十不惑”,暗示认识自我是每个人40岁以前的人生课题。
所以我相信你也一定曾经问过自己:我到底是谁?我应该怎样度过一生?
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可能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很多人甚至在中年之后,对世事已经“不惑”,却对自我仍感到困惑。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持续地自我探索?这其实是有心理学渊源的。心理学家认为,自我探索根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
“自我实现倾向”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来访者中心”理论的基本假设。罗杰斯认为,个体还在母亲子宫里的时候,就已经生成了自我实现的追求倾向,这个“自我实现倾向”如同一粒种子,在个体离开母亲的子宫后,引领一个人继续自我探索之路。
根据罗杰斯的理论,个体在离开母体后,会向着最具天赋(或称才干)的方向发展,直到长成每个人最理想的样子,也即“天生我材”所应该的样子,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干,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罗杰斯把这种完全发挥自我才干的状态称为人的“理想自我”。
然而,理想自我通常难以完全实现。个体在出生后,一方面会接收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爱,另一方面则会受到家庭和社会寄予的各种期望的制约。如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所解释的一样,幼年时的个体处在类似“本我”的阶段,一切要求父母均无条件的满足,给予孩子足够的爱。稍稍长大一些,进入童年阶段,父母和亲族开始对孩子实行爱的管束,要孩子向着家族和社会所期许的方向成长。于是,当孩子再想如幼年一样得到任何想得到的东西时,都必须先要满足他人的期望才能获得。比如,如果想获得某个玩具,就需要在期末考试中得到某种级别的成绩。
他人的期望就如同“超我”,是一种符合社会期许而可能与“本我”愿望相违背的要求。在“超我”的约束下,个体不得不努力让自己的“本我”愿望向“超我”要求妥协,从而既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本我的愿望,又能让“超我”感到满意。这种妥协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在“本我”趋向和“超我”期望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的“自我”。
这种妥协最为经典的案例体现在我们对专业和职业的选择上。一个人可能本来热爱的是艺术,但因某些原因,他不能选择这个专业,而转学了其他更能赚钱的专业。当个体因为他人的期望或某种现实的限制而背离了内心向往的方向,转而走上一条妥协路径的时候,他/她就会在这条路径上成长为罗杰斯理论中的“现实自我”。
经过努力,现实自我也会取得成就,并看起来很成功。然而,由于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的存在,会令人们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思索自我的现状以及自我到底是谁这个困扰人类的终极问题。“自我实现倾向”就如同一朵开放在内心深处、营养不良的小花,在你为现实所困顿而陷入思索或者为表面的成功庆祝后遁入沉思时,那朵小花就会摇曳在眼前,提醒你它需要照料,你的“自我实现倾向”需要更好的营养。
分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人会发生“中年危机”,即当按照他人和社会的期许在“现实自我”中努力拼搏多年后,你会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存在的意义,会希望用余生的时间去寻找真正的自我。也即罗杰斯的“自我实现倾向”通常会在中年时更猛烈地向你发出呼求,推动你去向着“理想自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