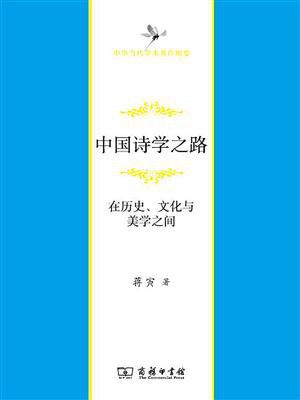三、游览诗:精神超越之场
按王国璎先生的理解,山水诗中未受诗人知性介入或情绪干扰,呈现其本来面目的山水描写,与道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诗人“在‘虚静’、‘忘我’的心理状态之下待物,则能物我两忘、主客合一,使物我之间不再有任何隔阂。由此可以直接循耳目所及去感应自然的万物万象,而把握自然物象的本质。这种以虚静、忘我之心境去直接感应物象的活动,即是一种审美性的观照,是一种美感经验的精神状态”
 。如此解释,足以说明自然山水以非主观色彩呈现的原因,但其间玄学观照方式如何转化为审美观照方式,质言之,即以虚静的心境直接感应物象是否就一定是审美观照,似乎还值得讨论。具体到谢灵运,他对山水的观照是否出以虚静的心境,也还有待斟酌。我觉得谢灵运的诗歌并没有显示出他写山水是出于对自然美的赏爱,他反复提到的“心赏”不过是“神超理得”的另一种表达。表面上看,他笔下的山水和前辈玄言诗中的山水没有多大区别,就像葛晓音先生说的“他的山水诗与玄言诗旨趣相同”,虽“已从玄言中脱胎而出,但还保留了大量的玄言成分”
。如此解释,足以说明自然山水以非主观色彩呈现的原因,但其间玄学观照方式如何转化为审美观照方式,质言之,即以虚静的心境直接感应物象是否就一定是审美观照,似乎还值得讨论。具体到谢灵运,他对山水的观照是否出以虚静的心境,也还有待斟酌。我觉得谢灵运的诗歌并没有显示出他写山水是出于对自然美的赏爱,他反复提到的“心赏”不过是“神超理得”的另一种表达。表面上看,他笔下的山水和前辈玄言诗中的山水没有多大区别,就像葛晓音先生说的“他的山水诗与玄言诗旨趣相同”,虽“已从玄言中脱胎而出,但还保留了大量的玄言成分”
 ,或詹福瑞先生说的,谢灵运“摆脱了纯玄言诗抽象演绎玄理的创作模式,发展了从山水这些感性入手体悟玄道的创作路子”
,或詹福瑞先生说的,谢灵运“摆脱了纯玄言诗抽象演绎玄理的创作模式,发展了从山水这些感性入手体悟玄道的创作路子”
 ,胡明先生曾用大量例证细致分析这类“披了山水外衣的玄言诗,即用山水岩泉、林濑云溪彩绘涂抹的玄言诗”
,胡明先生曾用大量例证细致分析这类“披了山水外衣的玄言诗,即用山水岩泉、林濑云溪彩绘涂抹的玄言诗”
 的基本特征。我想进一步指出,谢灵运诗歌中的玄理从表达到意义实质上已不同于玄言诗。这关系到我们对谢灵运诗歌结构与成因的理解,当然也涉及山水对于谢灵运的意义及在诗歌中负荷的结构功能。
的基本特征。我想进一步指出,谢灵运诗歌中的玄理从表达到意义实质上已不同于玄言诗。这关系到我们对谢灵运诗歌结构与成因的理解,当然也涉及山水对于谢灵运的意义及在诗歌中负荷的结构功能。
要理解谢灵运的自然观首先必须理解他的家世背景和生活处境。谢灵运出生在世崇道教的世族,自“弱龄而涉道”(《山居赋》),终生都沉浸于道家和道教思想中,向往神仙世界,修炼长生之术。道家抱朴处顺、守道适性的生活宗旨和率意自然的生活作风始终贯穿于他平生行事和诗文创作中。据卢盛江先生研究,玄学从魏正始时期开始,通过士人心态、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三个途径对文学思想产生影响
 。如果说这种影响在魏晋之际更多的是发生在士人心态和审美意识的层面,到晋宋之际就主要集中在士人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层面,直到齐梁之际才逐渐淡化,只在士人心态层面还有一点残余。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也显示出他主要是在心态和思维两方面受到玄学的影响。
。如果说这种影响在魏晋之际更多的是发生在士人心态和审美意识的层面,到晋宋之际就主要集中在士人心态和思维方式的层面,直到齐梁之际才逐渐淡化,只在士人心态层面还有一点残余。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也显示出他主要是在心态和思维两方面受到玄学的影响。
刘裕篡晋之后,虽颇优待世族,但鉴于晋室掣肘于世族的教训,不任世族子弟以实权
 。谢灵运虽出身名门,“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结果是大肆游衍,纵情山水。他出任永嘉太守时,常废弃公务,“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期年辞去,归始宁故宅营别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中间一任侍中,也“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免官回乡后,更是“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甚至“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后任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
。谢灵运虽出身名门,“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结果是大肆游衍,纵情山水。他出任永嘉太守时,常废弃公务,“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期年辞去,归始宁故宅营别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中间一任侍中,也“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免官回乡后,更是“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甚至“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后任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
 。他人游览山林,都为躲避世间的喧闹,取其幽深宁静,而谢灵运的这些游览活动却放纵无度,惊扰乡邻,一副暴发户大摆排场的铺张劲头,仿佛有意用一种桀骜放肆的姿态向朝廷,向官府,向乡里发泄内心的不满。而他的放浪行为也确实不止一次地招致有司的纠劾、地方官府的不满。想象一下他那种游览的情形,我们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狂躁的、骄逸放纵的、祸害乡里的贵族形象,无法与他诗歌留给我们的清雅的美感联系起来。我们不禁要追问:他的游览山水,究竟是要从山水中体悟道理,还是要到山水中去发泄烦闷?
。他人游览山林,都为躲避世间的喧闹,取其幽深宁静,而谢灵运的这些游览活动却放纵无度,惊扰乡邻,一副暴发户大摆排场的铺张劲头,仿佛有意用一种桀骜放肆的姿态向朝廷,向官府,向乡里发泄内心的不满。而他的放浪行为也确实不止一次地招致有司的纠劾、地方官府的不满。想象一下他那种游览的情形,我们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狂躁的、骄逸放纵的、祸害乡里的贵族形象,无法与他诗歌留给我们的清雅的美感联系起来。我们不禁要追问:他的游览山水,究竟是要从山水中体悟道理,还是要到山水中去发泄烦闷?
其实,我们只要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平心静气地去看谢灵运诗,就会理解,谢灵运遁迹山林的游览只不过是排遣世俗功名的焦虑、获得内心平衡的一种调节手段。正像《游名山志》所自陈的,“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游览既以适性为目的,则所有行为都以一种心理满足为归宿,而诗歌就成了达成这一境界后平静而愉悦的记录。《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写道: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蘋萍泛深沉,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诗在自然风光和游历路途的交叉铺叙后引入山鬼形象,再以神话恍惚、莫可究诘的结果隐喻世间一切追求都不可执着期待,由此达到消解世俗执念的彻悟境界。表面上看,物虑是由观而悟而遣,实则山鬼的情节本身不就是一种“安排徒空言”(《晚出西射堂》)么?精通释道二教之理的谢灵运,岂待因此才明白这简单的道理?我想玄理他是早就明白的,诗的表达不妨看作是重新确认。为什么要重新确认?因为这是内心从烦躁达到平和的情理交战的结果。诗作为战果的记录,已省略了交战的过程,仿佛诗人自始就是在欣然忘机的平和心境中进入山水胜境的,然而一部分作品还是留下了作者以理克胜的痕迹。《郡东山望溟海》写道: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白花皓阳林,紫虈晔春流。非徒不弭忘,览物情弥遒。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
诗作于永嘉,第二联点明出游动机是眺海以消忧,结果非但原先的忧愁未曾忘却,览物反而使情绪更加强烈,连传说使人忘忧的萱草也无法化解。由于“萱苏”一句继续强化了情的力量,结句的自解不免苍白无力。在这里,“情”不仅明显是负面的因素,而且有着难以克制的顽强力量,玄理显得定力不足。类似的例子还有《登上戍石鼓山》,开篇云“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落句云“佳期缅无像,骋望谁云惬?”这也是理不胜情的例子。当然,更多的作品还是“理来情无存”(《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的完胜记录,如《过白岸亭》的“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游赤石进帆海》的“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游南亭》的“乐饵情所止,衰疾忽在兹。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等,不一而足。在这些诗中,忧愁、烦闷、倦怠乃至享乐的欲望,总之属于“情”的精神郁积,都被理所化解、涤荡。诗人就这样在游赏观览中,重复、玩味、验证、肯定来自“三玄”的理趣,获得“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的恬适心境,从而消释人世间的烦恼。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心理满足是可以从自然的感性之美中获得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两句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我们既已知道谢灵运游览的动机主要是为化解自己的精神焦虑,而这种化解又是通过以理克情的方式实现时,那么玄学的观照方式是“得意忘象”这一点就不能忽视了。谢灵运的自然观正属于典型的玄学方式,就像《山居赋》开篇所说的:“大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夫能重道则轻物,存理则忘事。”事物和道理既然是外和内、表和里的表现关系,两者的价值轻重和取舍也就不言而喻。因此不妨说,在谢灵运的山水游览中,自然景观其实是应该被理性超越的对象,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可以忽略的东西。事实上,他的大多数作品都表明,他游览时关注的根本不是作为客观现象的山水,而主要是自我行为和自我意识,它们都和他满脑子的玄理随时产生互动。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的一则轶事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山水对于谢灵运的意义,进而理解其诗中山水的存在属性:
殷、谢诸人共集,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
谢安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对视觉形成原理的科学追问,也可以看作是对意识产生方式的哲学探讨。如果从主客体关系着眼,他不就是在问:我们的眼睛在看着风景,可是风景有没有被我们看到即进入我们意识中呢?正像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如何看见它,这是依影响我们的艺术而决定的。”
 艺术史家沃尔夫林(H.Wolfflin)也说过:“人们看见的总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而且这要求有一个长期的教育(这在一个艺术多产的时代也许是不可能的)来克服天真的知觉,因为它与客体在视网膜上的反映毫无关系。”
艺术史家沃尔夫林(H.Wolfflin)也说过:“人们看见的总是他们所寻找的东西,而且这要求有一个长期的教育(这在一个艺术多产的时代也许是不可能的)来克服天真的知觉,因为它与客体在视网膜上的反映毫无关系。”

从谢灵运诗的写法来看,要说他没有看到山水之美可能太绝对,也许应该说他诗中存在着“玄思与审美的二元山水观”
 ,但山水肯定不是他关注的中心,却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笔墨之所以触及山水景观,是因为不由表象无法企及内蕴,也就是《登江中孤屿》所说的“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在很多情况下,他根本无需什么体悟,只消默诵“三玄”那些名言,吟味那些理趣,就足以为他直观山水景物的某些朦胧感觉命名,或引发若干相应的感喟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正流行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宗炳《画山水序》)的观念,一方面也是源于他自幼习染道家学说养成的兴趣。
,但山水肯定不是他关注的中心,却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笔墨之所以触及山水景观,是因为不由表象无法企及内蕴,也就是《登江中孤屿》所说的“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在很多情况下,他根本无需什么体悟,只消默诵“三玄”那些名言,吟味那些理趣,就足以为他直观山水景物的某些朦胧感觉命名,或引发若干相应的感喟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正流行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宗炳《画山水序》)的观念,一方面也是源于他自幼习染道家学说养成的兴趣。
正如前文所说,玄学的抽象名理只可意会不可言说,而游览和观赏的瞬间直觉和自性经验更是难以明言,于是诗歌所能表现的,只能是被传统经典概念化了的老生常谈。黄节先生曾指出:“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以成之。其所寄怀,每寓本事;说山水则苞名理。”
 确实,谢灵运的山水游览之作大多是发挥“三玄”的旨趣。王国璎先生曾举出以下这些例句:
确实,谢灵运的山水游览之作大多是发挥“三玄”的旨趣。王国璎先生曾举出以下这些例句:
《富春渚》:怀抱即昭旷(庄),外物徒龙蠖(易)。
《晚出西射堂》: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庄)。
《登池上楼》:持操岂独古(庄),无闷征在今(易)。
《游南亭》: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庄)。
《过白岸亭》:未若长疏散(庄),万事恒抱朴(老)。
《登江中孤屿》:如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庄)。
《登永嘉绿嶂山》: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老)。恬知既已交,缮性自此出(庄)。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淮)。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老)。
《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庄)。
《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顷用,岂为古今然(庄)。
《七里濑》: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庄)。

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不少,如《登永嘉绿嶂山》“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四句用《易》,《赠从弟弘元》“视听易狎,冲用难本”用《老》,《初往新安至桐庐口》“既及泠风善,又即秋水驶”,《斋中读书》“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游岭门山》“早莅建德乡,民怀虞芮意”用《庄》,不一而足;而辞赋中发挥《庄》义之处亦复不少
 ,诚如前人所说,“读《庄子》熟,则知康乐所发,全是《庄》理”
,诚如前人所说,“读《庄子》熟,则知康乐所发,全是《庄》理”
 。但谢灵运相比前代玄言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诗中引入了佛教名理。《过瞿溪山饭僧》云:“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石壁立招提精舍》云:“四城有顿踬,三世无极已。浮欢昧眼前,沉照贯终始。”如此频繁出现的玄言和佛教名理,只能说明谢灵运的游览活动有一个固执的心理指向,同时也暗示了山水并不是他关注的中心或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缺席的可能性吧?
。但谢灵运相比前代玄言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诗中引入了佛教名理。《过瞿溪山饭僧》云:“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石壁立招提精舍》云:“四城有顿踬,三世无极已。浮欢昧眼前,沉照贯终始。”如此频繁出现的玄言和佛教名理,只能说明谢灵运的游览活动有一个固执的心理指向,同时也暗示了山水并不是他关注的中心或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缺席的可能性吧?
我们在前文已看到,由于名理的抽象玄远、不可言说,玄言的清谈都表现为简约隽永的感叹。诗歌也是如此,只宜片言只语,点到为止,若刺刺铺陈势必南辕北辙,背离本旨。这就决定了基于玄学观照方式的山水游赏之作,只能停留在展示超越的过程,而不是陈说其结果上。谢灵运诗歌的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谢诗结构雷同的问题,如黄节先生曾指出:
大抵康乐之诗,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故末语多感伤。然亦时有例外,如《登池上楼》首四句“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则以理语起矣;至如《南楼中望所迟客》之“杳杳日西颓,漫漫长路迫”,《游赤石进帆海》之“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游南亭》之“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则又以景语起矣。然于写景说理之后,必紧接以叙事,则几成康乐诗之惯例矣。

谢灵运诗结构上的这种模式化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并作出自己的解释
 ,主要是归结于钟嵘所谓“寓目辄书”(《诗品》卷上)的表现方式的局限,或“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的对自然观照的浓厚兴趣
,主要是归结于钟嵘所谓“寓目辄书”(《诗品》卷上)的表现方式的局限,或“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的对自然观照的浓厚兴趣
 ,但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谢灵运诗歌的结构特点。因为从根本说,这并不是艺术思维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活动模式的问题。
,但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谢灵运诗歌的结构特点。因为从根本说,这并不是艺术思维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活动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