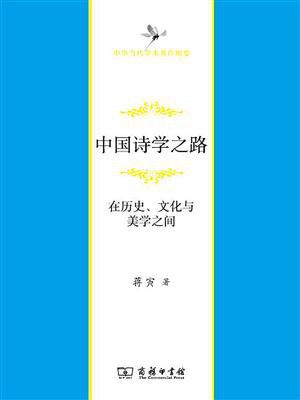一、三首诗中的时间感觉
在讨论三大诗人的时间意识之前,我们首先该知道他们对时间的感觉。时间感是全部时间意识内容的基点。请看下面三首诗:
古风其二十八 李白
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古来贤圣人,一一谁成功?君子变猿鹤,小人为沙虫。不及广成子,乘云驾轻鸿。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仅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苏轼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来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李白诗里的时间具有被极度夸张的急遽飞逝感:容貌的鲜艳就像闪电般短促,时光则像风一样倏地飘逝。起首两句极写时光飞逝之迅疾。“草绿”二句以具体的季节、日夜更替之急促来充实次句的内涵,而“华鬓”两句也以青春难驻、人生易老的具体描写来发挥首句的意蕴,一如杜甫“孔丘盗跖俱尘埃”之意。人生在世的日子是那么有限,而青春更是那么短暂,至于一切古人,无论贤愚一概化为虫鸟,没有任何东西能长存于世!全诗不仅以极度的夸张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间飞逝的感觉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虚无感,最后也暗示了作者消解这种精神困扰的方式——游仙。
杜甫诗没有这种感觉,萧萧落木和滚滚长江是两个运动的持续过程,“无边”“不仅”这意味着空间、时间上都无间隔的定语修饰赋予这两个意象以漫长乃至永恒的持续感,而诗人自身的“长作客”同样表现出生涯的持续性,这都是很概括却也很平实的叙述,说明诗人意识中的时间是一种正常的流逝感。此外,古人视“百年”为常人寿命的限度,杜甫爱用“百年”两字表示毕生,又从某种意义上显示出他对生命限度的冷静而客观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杜甫的时间感是比较正常、比较现实的。
苏东坡诗则又不同,时间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了。诗人虽说“走马来寻去岁村”,但诗中并没有表现出“去岁村”的今昔差异,也就是说没有表现出知觉的差异,因此时间过程就没有被一年的间隔突出,反而被“春梦”的比喻淡化了。在这里突出的是人的重来,而往事则被淡化到“无痕”的地步,仿佛一场恍似有又恍似无的春梦。这一比喻并不是偶然闪现的诗意表现,下文我们将看到,它与东坡对人生、对时间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联系在一起。三首诗体现了三位诗人不同的时间感,这不同的时间感基于他们各自对生活的感受,分别代表着反抗时间、顺从时间和超越时间三种透过时间观念表现出的人生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