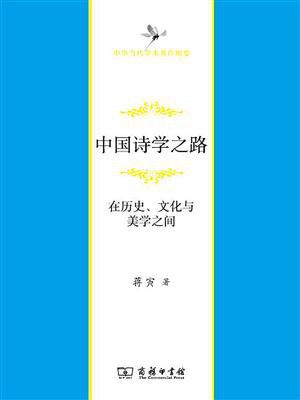四、超越“出处”的文化选择
执“分谊”而尽守节的义务,已明显是用公事公办的态度事君。而陆世仪言“分谊”,还将不可选择的事亲之孝划出界限,以比况报君的限度,更显出他在君臣关系上持通达的态度。除了重视“分谊”,他还着眼于动机的诚伪,联系到天下民生之苦来判断出处的宜忌,而不是抽象地谈论出处是非。这说明,时人看待出处问题,主要不是着眼于行为本身,而更关注动机如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曰:“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陆世仪激励徐次桓济世泽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由于清初社会对士人出仕普遍持宽容态度,亲友的出处,大家都不是很在意。顾炎武虽然很反感李因笃劝李二曲应征,但他同徐乾学兄弟的甥舅关系并未因他们仕清显达而断绝,只是嫌进京住在徐家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而已
 。顾炎武本人在66岁时拒绝博学鸿儒之征,固然举世钦佩;但这一年施闰章、汤斌、彭孙遹、汪琬、李因笃、朱彝尊、毛奇龄、孙枝蔚、尤侗、陈维崧、傅山、严绳孙、李来泰等186位名士应召之京,也没给这些人的生平带来污点,相反此科倒是有清一代为人乐道的盛事,“抡才之典于斯为盛!”
。顾炎武本人在66岁时拒绝博学鸿儒之征,固然举世钦佩;但这一年施闰章、汤斌、彭孙遹、汪琬、李因笃、朱彝尊、毛奇龄、孙枝蔚、尤侗、陈维崧、傅山、严绳孙、李来泰等186位名士应召之京,也没给这些人的生平带来污点,相反此科倒是有清一代为人乐道的盛事,“抡才之典于斯为盛!”
 如果说侯朝宗名列明季“四公子”之一,就该奉明正朔,不食清粟,那不就成了黄宗羲所鄙视的“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了吗?
如果说侯朝宗名列明季“四公子”之一,就该奉明正朔,不食清粟,那不就成了黄宗羲所鄙视的“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了吗?
 于情于理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于情于理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更何况,出处问题虽然关乎气节,但明哲保身也夙为儒者处世的原则。仕清一事,褒贬存乎其人之所行而已,并没有什么必不可的理由。且看陈瑚《报李映碧廷尉书》是怎么说的:
夫子曰“危行言孙”,诗曰“明哲保身”,圣贤之学,蠖屈龙蛰,以全其用。今吾党之爱阁下者,非虑回面易行而丧其所守也,但恐制行太高,立身太洁,触要人之忌,成周章之局耳。谓宜相机观变,稍示委蛇。当事固请,不妨一见谢之,不必逾垣闭门,为已甚之行。此在阁下未为屈节也。

当时有人举荐李映碧,映碧闭门坚拒,陈瑚担心他由此贾祸,因示以权宜之计。宋征舆《钱先生寿序》载,钱谷工制举业,为有司所招,乃父语之曰:“与汝约,不十年不可以出。十年者,天道之周也。《易·象》曰:十年乃字,反常也,礼故国者如是而足也。”
 谷不敢违命,十年后方出应试。凡此种种,后人应该体谅当事人的选择,而不应以正统的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正像对古代的“节妇”不必去赞美,对追求爱情的“淫奔”也不必去谴责一样。为什么我们在男女情爱方面能以现代人的眼光体谅古人,在出处问题上就不能了呢?说到底还是意识深处的夷夏之辨在作祟。
谷不敢违命,十年后方出应试。凡此种种,后人应该体谅当事人的选择,而不应以正统的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正像对古代的“节妇”不必去赞美,对追求爱情的“淫奔”也不必去谴责一样。为什么我们在男女情爱方面能以现代人的眼光体谅古人,在出处问题上就不能了呢?说到底还是意识深处的夷夏之辨在作祟。
历史地看,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度,遭到异族侵略,为异族所统治,国民都会有屈辱感,尤其是意识到统治者的文化品位低于本民族时。可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汤因比(A.J.Toynbee)已用大量史实证明,“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边界稳定下来,时间永远是对蛮族有利的”。而且,任何一个蛮族入侵者如果未先受过任何其他文化的影响,就很可以成功
 。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时代的女真人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们的确也成功了。这严酷的事实在当时所激起的并不只是对异族的仇视,更多的倒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一代人的悲哀心境也不只是对朱家王朝的眷恋,更多的不如说是对汉民族文化的哀挽。史学家章学诚曾说:“亡国之音,哀而不怨。家亡国破,必有所以失之之由。先事必思所以救之,事后则哀之矣。不哀己之所失,而但怨兴朝之得,是犹痛亲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遗民故老没齿无言,或有所著诗文,必忠厚而悱恻。其有谩骂讥谤为能事者,必非真遗民也。”
。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时代的女真人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们的确也成功了。这严酷的事实在当时所激起的并不只是对异族的仇视,更多的倒是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一代人的悲哀心境也不只是对朱家王朝的眷恋,更多的不如说是对汉民族文化的哀挽。史学家章学诚曾说:“亡国之音,哀而不怨。家亡国破,必有所以失之之由。先事必思所以救之,事后则哀之矣。不哀己之所失,而但怨兴朝之得,是犹痛亲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遗民故老没齿无言,或有所著诗文,必忠厚而悱恻。其有谩骂讥谤为能事者,必非真遗民也。”
 姑不论末句对遗民的论断是否有道理,他对亡国遗民的反思意识的强调是符合清初历史状况的。
姑不论末句对遗民的论断是否有道理,他对亡国遗民的反思意识的强调是符合清初历史状况的。
梁启超在《无聊消遣》中引顾炎武的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自近代以来成为最脍炙人口的名言、最激动人心的口号,然而它却并不是顾炎武的原话。顾炎武本来是这么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或许可视为当时文化救亡意识的觉醒。在对历史的冷静审视中,顾炎武看到了历史模态的循环,历史悲剧的重演,感到汉民族的礼乐文明正走向沦亡,将被异族的野蛮文明所取代。为此他向民族的每一分子(其实主要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发出了拯天下沉溺,挽救民族文化于危亡的呐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国家和天下这两个素来混为一谈的概念作了区分:国家指王朝,是一个政治概念;天下则意味着中原大地和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众、文明,是一个文化概念
 ——黄宗羲《原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宣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王朝的存亡,自有食其爵禄者为之负责;而民族和文化的存亡,则与民族的每一分子相关,作为文化承载者的知识人更应理智地审度自己的命运和选择。因为这时个体的命运已同民族、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个体的选择将成为民族、文化的选择,并决定其未来的前途。
——黄宗羲《原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宣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的。王朝的存亡,自有食其爵禄者为之负责;而民族和文化的存亡,则与民族的每一分子相关,作为文化承载者的知识人更应理智地审度自己的命运和选择。因为这时个体的命运已同民族、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个体的选择将成为民族、文化的选择,并决定其未来的前途。
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兴灭继绝,拯救汉文化的沉沦;个人的出处穷通,相比之下根本无关紧要。因此,陆世仪《与张受业先生论出处书》说:
大约当今时事,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可为……窃谓士君子处末世,时可为,道可行,则委身致命以赴之,虽死生利害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吾一身之所系者小也。若时不可为,道不可行,则洁身去国,隐居谈道,以淑后学,以惠来兹,虽高爵厚禄有所不顾。盖天下之所系者大,而万世之所系者尤大也。

的确,在民族文化的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这样的大问题面前,个人的出处还有多少可掂量计较的分量呢?说到底不过是个人良心是否说得过去的问题罢了。所以答复徐次桓问出试时,陆世仪说“此亦非大关系所在”。那么,什么是大关系所在呢?首先当然是抗清。顾炎武、阎尔梅、王夫之、毛奇龄、屈大均、吕留良、黄宗羲、归庄、朱彝尊,这一批名士无不参加过抵抗运动,然而形势已无可挽回。用武力已难与清朝抗争的现实,迫使他们为汉民族及文化的前途另选择一条道路,一条切实可行的真正的自救之道。
在对亲身经历的亡国史和明代兴衰史进行深刻反思后,他们达成共同认识,救治汉文化的虚脱和积弱,首先要从改造学风开始。于是他们选择了崇尚实学的道路,希望由此改变汉文化风雅有余而经济不足的根本弊病。当时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诸如顾炎武的地理学、音韵学,朱彝尊的经学史整理,王夫之、颜元的哲学,李二曲的性理之学、黄宗羲的政治学、思想史研究,无不是这一信念的具体实践。顾炎武致黄宗羲书,清楚地说明了他们那一代人学风的转变:
某自中年以前,不过从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

这里的“积以岁月”正是明亡清立的那段时间,他们都在此期间完成了学风的转变。顾炎武《与潘次耕札》说“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扼要地阐明了一代学人崇尚学问的动机和宗旨。正因为抱有如此崇高的目的,他们才能很自负地宣言:“天下有道之士不可多得。吾辈学问进一分,则世界人心有一分受用;吾辈学问减一分,则世界人心有一分陷溺,其所关系诚有非浅鲜者”
 。志士仁人生当末世,无以自达,无以达人,作为文化传统的承传者,只能读书明理,探究传统文化尤其是离自己最近、与自身关系最密切的传统(对清人来说就是明代)的得失,及于现实生活的适应性,从而加以改造和新的诠释。这是知识人在时不可为之后惟一能做的事,也是他们的责任。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正是这么做的。在抗清失败后,他们就走上了改造学风进而改造民族文化的道路,期望“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即使此生看不到理想的实现,也要“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
。志士仁人生当末世,无以自达,无以达人,作为文化传统的承传者,只能读书明理,探究传统文化尤其是离自己最近、与自身关系最密切的传统(对清人来说就是明代)的得失,及于现实生活的适应性,从而加以改造和新的诠释。这是知识人在时不可为之后惟一能做的事,也是他们的责任。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正是这么做的。在抗清失败后,他们就走上了改造学风进而改造民族文化的道路,期望“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即使此生看不到理想的实现,也要“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
 ,为日后“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为日后“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做好理论和知识的准备。
,做好理论和知识的准备。
他们的选择至今看来仍是值得赞赏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
 。在当时,改造学风首先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思想工具进行改造,其直接的结果就是走出汉文化中心主义封闭自足的方阵,去应对历史的挑战——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地面对挑战并成功地应战,才能保持它机体的活力。更进一步,崇尚实学,由风雅之学转向经济之学,必将赋予汉文化一种经济的实践性格,而求实的科学作风最终也会培养成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已为西方思想史所证明)。这种学术趋向不仅与明代以来汉文化的空疏、虚矫、愚妄相对立,从根本上说,也是与封建体制的意识形态专制相对抗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景观。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思路没有逃过满清统治者警觉的目光。玄烨分明已感觉到这股学术思潮的力量,预见到它鲜明的经济倾向必将给汉文化带来空前的活力,于是他坚决地通过意识形态干预压制了这股思潮,并以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为发轫,大力提倡文治风雅,与文字狱的威慑相结合,最终将清代学术和文化扭曲为思想贫瘠的乾嘉学风。
。在当时,改造学风首先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思想工具进行改造,其直接的结果就是走出汉文化中心主义封闭自足的方阵,去应对历史的挑战——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地面对挑战并成功地应战,才能保持它机体的活力。更进一步,崇尚实学,由风雅之学转向经济之学,必将赋予汉文化一种经济的实践性格,而求实的科学作风最终也会培养成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已为西方思想史所证明)。这种学术趋向不仅与明代以来汉文化的空疏、虚矫、愚妄相对立,从根本上说,也是与封建体制的意识形态专制相对抗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景观。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思路没有逃过满清统治者警觉的目光。玄烨分明已感觉到这股学术思潮的力量,预见到它鲜明的经济倾向必将给汉文化带来空前的活力,于是他坚决地通过意识形态干预压制了这股思潮,并以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为发轫,大力提倡文治风雅,与文字狱的威慑相结合,最终将清代学术和文化扭曲为思想贫瘠的乾嘉学风。
清代前期学术史的这一趋势,早已是文史研究者熟知的常识。我想借此说明的是,在明清之交,知识阶层最关切的是汉民族汉文化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斯文斯民存亡未卜之际,个人的出处实在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我不想否认,处在钱谦益和吴梅村的位置,当然无法以拯救文化沉沦这样的宏大理由来自辩和自解,也难以摆脱“名节”观念的沉重负担,更不能抑制沧桑变幻中个人命运难以自主的悲哀。但在个人与国家的一体化关系早已解除,并且能将君主视为异己的东西加以排斥,认识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明清之际,我们还能以是否出仕来评判这些所谓“贰臣”的大节吗?读一读《明夷待访录》:“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当时人对君臣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已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今天还根据出处来评判他们的节操,就不仅显得观念太陈旧,眼界也显得太狭窄了。当时人早已超越了出处问题的道德取向,三百年后我们还拘泥于此,不是见识远不及古人么?
当时人对君臣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已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今天还根据出处来评判他们的节操,就不仅显得观念太陈旧,眼界也显得太狭窄了。当时人早已超越了出处问题的道德取向,三百年后我们还拘泥于此,不是见识远不及古人么?
凡是不平常的时代都有不平常的课题。每个历史关头,人们思考的是什么,要做的是什么,这是后人必须了解的,否则历史研究就会成为一通歪批《三国》。就侯方域来说,不要说应试,就是真的出仕,在今天也不必作为操行污洁的问题来讨论。他之所以比不上顾炎武等人,决不在于他应试而顾炎武拒绝。根本的问题是他缺乏顾炎武那种责任感,那种对明代文化的反思,缺乏改造学风的决心和勇气。他一直是个公子,入清后仍然是一副名士作派。黄宗羲《思旧录》载:“朝宗侑酒,必以红裙,余谓尔公(张自烈字)曰:‘朝宗之大人方在狱,岂宜有此?’尔公曰:‘朝宗素性不耐寂寞。’余曰:‘夫人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吾辈不言,终为损友。’”
 如此不耐寂寞的名士,应不应举,出不出仕,有没有气节,于人于己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倒是应该警惕,像侯方域这样的个人出处问题,一旦与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及对祖国的忠贞不渝联系起来,是否就改变了这些概念的内涵,使忠于王朝、爱君主、爱现政权的实质性要求披上了美丽的光晕?
如此不耐寂寞的名士,应不应举,出不出仕,有没有气节,于人于己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倒是应该警惕,像侯方域这样的个人出处问题,一旦与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及对祖国的忠贞不渝联系起来,是否就改变了这些概念的内涵,使忠于王朝、爱君主、爱现政权的实质性要求披上了美丽的光晕?
在日常语境中,祖国与王朝或国家一向混用不分。然而“祖国”其实是不适合用来讨论问题的名词,因为它缺乏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具体限定。一般意义上,祖国泛指国土与生息其间的民族和文化,故比喻为母亲。如果人和祖国真是亲子般的关系,那就是不可选择的,而且原则上必是互爱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祖国的意义体现于现政权及其建构的生活环境时,人们常感觉不到亲子式的互爱。当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凄绝地呼吁:“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当老舍《茶馆》里的人物哀惋地长叹:“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呢?”当美国影片《第一滴血》续集的结尾主人公悲愤地嘶喊:“美国,我们是爱你的,可是你爱我们吗?”(大意)这里的祖国、咱们的国、美国,既不是亲爱的母亲,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文化区域,而只指具体的政权控制的行政区域,分别为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或约翰逊政府主宰的美国。事实上,祖国的意义总是通过国家,更具体地说是现政权、政体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总和体现出来的。如此说来,就绝不存在什么抽象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所谓爱国,首先是指爱现行国体和社会生活,在封建社会就表现为爱现政权也就是世袭的某姓王朝。这虽然与乡土人情意义上的爱国有根本的不同,但历来总是将两者混为一谈,而近代以来的执政者更是竭力模糊两者的差别,让人误以为爱国就是爱现政权,或将对现政权的拥护视为爱国行为。
梁启超将顾炎武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对照,缩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句,已使天下的内涵因失去参照系而变得模糊;今人援引时又改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有意无意的改篡,或许暗示了个体的某种趋同性或依附性倾向吧?这不是个简单的语义学问题,也许关系到本文论述的士人在易代之际的命运和选择问题。对此若无清醒的认识,不仅会妨碍我们合理地看待古代士人的命运与选择,甚至还容易纠缠于无关大局的细节,忽略真正重要的时代精神问题,以致丧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自居。
(本文原题“易代之际的生存伦理——历史的相似
情境及其诠释”,刊于《中国文化》2011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