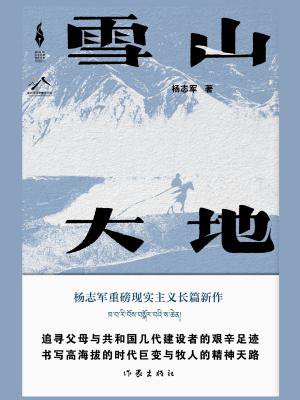2
水一直不退,低洼地变成了一片汪洋。但父亲和桑杰都知道,不管水退不退,赛毛和父亲的马都已经不在了。桑杰没有哭,也不让孩子们哭。父亲知道,这是因为活人的眼泪会滞留灵魂远去的脚步,就像被酥油粘住了羊毛,被水打湿了翅膀。孩子们是懂事的,除了索南会带着妹妹梅朵时不时高声念诵起祈福真言外,没有什么异样。沉默的才让则愈加沉默,他伫立在高地上,望着低洼地和大水的眼睛晶亮而明澈,如同冰雪的精灵在无边的寂静里放光。父亲感觉到,才让的眼光有声音,有一种悲沉的能够穿透人心的声音。梅朵黑和梅朵红一早一晚都会走向低洼地,蹲踞在汪洋的边缘,吠叫几声,沉默一会儿,是守望,还是送别?桑杰里里外外忙碌着,尽量不让一个突然失去了阿妈的家庭陷入混乱。他让索南和才让去放牧,自己挤奶,背水,拾掇牛粪羊粪,生火烧茶,打酥油。父亲说:“还是你去放牧吧,两个孩子整天在外头,遇到狼豹怎么办?家里有我呢。”桑杰说:“噢呀。”但只去了一天,他就又把孩子换去放牧了,因为他发现父亲烧的茶里奶子和盐巴放得多了些,父亲的挤奶留给小牛犊的少了些。盐巴是金贵的,奶子能少喝就少喝,因为更多的奶子要打成酥油交给公社,公社要交给县上,交不够的话角巴主任会不高兴的。但又不能克扣小牛犊的,它还不会吃草,它要长大。父亲说:“我知道啦,你去吧,放牧要紧,孩子的安全更要紧。”桑杰说:“怕没有,有梅朵黑和梅朵红哩。”
一个星期后水退了,低洼地裸露而出。桑杰和父亲走过去,来到赛毛救了父亲的那座荒丘前,绕着荒丘转了又转,是念着祈福真言的顺时针绕转。父亲的祈福真言湿漉漉的,他像桑杰一样忍着,把眼泪流到了嘴里,又从嘴里流进了祈福真言。然后他们又来到野马河汇入黄河的地方,念了一会儿祈福真言,平静地回到高地。放牧归来的索南和才让带着梅朵也去走了一遍,走到半夜才回来。两只藏獒却对消失了大水的低洼地毫无兴趣,它们知道那儿什么也没有,连赛毛和父亲的马划过地面的擦痕都没有。
又过了一天,角巴主任出现了,跟他在一起的还有野马滩的大队长囊隆和几个牧人。他在帐房前一见桑杰就说:“知道啦,知道啦,我一个耳朵进的是天上的鹰叫,一个耳朵进的是牧人的传言,你把家里的人丢掉了吗?可惜啦,可惜啦。超度的人请了没有?”桑杰弯下腰去,正要回答,角巴又说:“你这样好的人也会吃鞭子,沁多的规矩没有变是真的,但是我变啦,难道大家不知道?”他晃晃头转向父亲:“我把我当主任,牧人把我当头人;我把沁多当公社,牧人把沁多当部落。强巴科长啦,你说怎么办?世事变啦,他们的想法一点点都没变,这些老牧民(死脑筋),你就是把一桶雪水泼到头上他们也不会清醒。我说过多少回,过去和现如今不一样啦,天不一样,地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啦。怎么我越说不一样,牧人就越觉得一样呢?”父亲悲伤地沉默着。角巴叹口气说:“桑杰你吃了几鞭子记不记得?不记得的话那我就说了算,用指头数是两巴掌(十鞭子)不是一巴掌,今天当着我的面你还给他们。”桑杰说:“主任啦,我从来没打过人。”“也没打过马?”“打过,马不打不跑,主任是知道的。”“这就对了嘛,你怎么打马就怎么打他。”角巴指了指囊隆,把自己手里的马鞭塞给了桑杰,“囊隆你把马还给桑杰,再请一个阿卡(修行的人)来这里,酥油不热不化,亡魂不度不走。”桑杰说:“要请就请官却嘉阿尼,他法力大大的有哩。”囊隆“噢呀噢呀”着,把手里的马缰绳还给了桑杰。角巴主任又朝桑杰瞪起眼睛:“打呀,为什么不打?”忽又哼哼一声,“不想打就算啦,聪明的人不结仇,能饶就饶过,现如今人家是大队长,只有他打你的,没有你打他的,天可以变,尊卑不能变,大人小人不能变,牛犊子不能给牦母牛喂奶,下跪的总是羊羔子,没见过马驹子踢坏儿马子的。你丢了女人,家里谁烧茶?我,沁多草原的角巴德吉,嘴皮子干得就要冒出火来啦,快快快,公社的奶子不要给主任舍不得,多多的酥油放给的要哩。”桑杰赶紧弯腰,手掌向上,指向了敞开的帐房门。角巴说:“强巴科长啦,才让县长从州上托人带话,让你马上回县上,你今天就跟我走。”父亲问:“没说是什么事?”角巴嘿嘿了一声:“人家的事怎么能给我说?”
角巴是个说话办事嘁里喀嚓、讲究时效的人,喝酥油茶吃糌粑也一样,不浪费一点点时间,很快他就走出帐房打算离开了。“强巴科长啦,我们走,你没有马了吗?先在野马滩借上一匹,到了‘一间房’,我送你一匹好马。”囊隆说:“我这就去找马。”父亲虎头蛇尾的蹲点就这样结束了。他走向高地的边沿眺望低洼地,想着为自己而死的赛毛,忍不住抽泣了一声,泪光闪闪地蒙住了眼睛。桑杰来到他身后:“强巴科长啦,你哭啦。”父亲赶紧用手背擦了擦:“对不起啦,胸腔里的酸水水,不由得要往外冒啦。”桑杰说:“赛毛已经远远地转世去了吧?没走的话也不要紧,官却嘉阿尼就要来啦。阿尼的祈愿,亡魂的马,是往天上去的快马,善人有福气,赛毛的福气大大的有哩。”说着也忍不住哭起来,边哭边招手,“孩子们,你们也过来,想哭就哭吧,你们的阿妈走啦。”才让第一个跑来,接着是索南,他们朝着低洼地扑通一声跪下了。梅朵慢慢地走着,还没到阿爸跟前,就已经成了泪人儿。全家人包括父亲,再也不克制不隐忍了,呜呜地哭声爆响而起,梅朵黑和梅朵红也跟着轰轰轰地叫。才让趴到地上,没有声音,只有如溪如河的眼泪,比所有人都多的眼泪,流淌在草丛里。
角巴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看他们哭一天也哭不够的样子,大声说:“要哭的话,藏族人的眼泪多得没有升量,野马河算什么?黄河算什么?人活着,没有不可怜的下场,今天这个死,明天那个死,一辈子不够哭的。那么多事情还要做,走吧,强巴科长啦。”父亲用衣袖擦掉眼泪,拉起梅朵,摸摸她干净的脸蛋,拉起索南,摸摸他的头,又摸摸梅朵红的鼻子、梅朵黑的鬣毛,然后来到桑杰跟前:“桑杰啦,没忘了赛毛的心愿吧?”桑杰愣愣的,见父亲望着才让,自己便也望着才让。父亲说:“我想把才让带走,去找曼巴给他治病。赛毛天天都在祈祷,‘才让会说话,将来骑大马,穿金纱’。”桑杰吃惊地啊了一声,没说话。父亲拉起依然趴着的才让,牵在手里说:“你放心,你们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角巴说:“桑杰你碰上好人啦,听我的,把哑巴儿子交给强巴科长。我看出来啦,他前世是雪山大地保佑过的善良人。”父亲觉得承认的话桑杰就会信任自己,便“噢呀噢呀”起来。
上路了。草原上昨天新开了许多蓝色的绒蒿花,今天又新开了许多粉色的早菊,遍地的花骨朵一个时辰跟一个时辰不一样。这是夏天走向盛典的标志,很快就要凉了。角巴牵着马,陪伴父亲和才让步行了一会儿,就见囊隆拉马走来。父亲迎过去,说着谢谢,接过了缰绳。他检查了一下马鞍,先扶才让上去,然后踩镫而上。接下来的行走格外轻松,不用父亲操一点心。角巴是沁多公社的当家人,他选择的路线便捷而平坦,还总能碰到牧家,酥油茶是不断的,糌粑是管饱的,想过夜的时候,就能看到被夕阳染红的帐房。第二天下午,他们到达了“一间房”。角巴说:“强巴科长啦,去我家过夜吧,家里条件好些。”父亲不客气,带着才让跟了去。他们先是看到了一座白色的方塔,走不多远又有一座高大的祈福真言石经堆,堆上插满了带着旗幡的木箭,又走了一会儿,就看到一座帐房从地平线上遥遥而来。
角巴家住的是十几块牛毛褐子组成的大帐房。这个季节,儿子一家赶着牛羊带着藏獒去了山上的夏窝子,家里只有妻子和两个女儿。妻子姜毛黑黑胖胖,一看就是个不缺吃喝的富家女人。两个女儿一个十六,一个十二,见了客人都过来笑嘻嘻问候。父亲说:“才让,这两个姐姐漂亮不?”才让胆怯地低下头。父亲问她们叫什么,大的说:“卓玛。”小的说:“央金。”“卓玛央金你们好?这个哑巴弟弟就交给你们啦,让他吃好喝好睡好,就像到了他自己的家里。”卓玛和央金齐刷刷地说:“噢呀。”角巴说:“她们有哥哥没有弟弟,见个男孩子喜欢得很。”父亲坐下来,打量着主任家的陈设,锅灶右边铺了两层毛毡,毛毡上还有卡垫,沿帐壁摆着一溜儿叠成长条的花被子,说明主人通常是穿着衬衣睡觉的,不像普通牧人,白天裹的是老羊皮袍,晚上盖的还是老羊皮袍。帐壁前摆着一盏长明的酥油灯,映照着里面雕刻的吉祥八宝图,不知是铜的还是金的。帐壁边放着一溜儿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家什,奶桶、酥油桶、酸奶桶、铜壶、铜锅什么的,还立着一杆被五彩旗幡装饰起来的叉叉枪。晚餐也比牧人家丰富好多,有糌粑和加了肉汤的糌粑糊糊,有风干的羊肋巴肉,有招待客人的酸奶和奶皮子。糌粑是拌了糖的,才让大概是第一次吃糖,吃饱了还想吃,肚子都鼓了起来。睡觉时最尊贵的右首里面自然要让给父亲,父亲叫才让跟他睡,却被两个姐姐夺了过去,她们睡在左首里面的毛毡上,那儿是帐房最深最低的地方,隐秘得就像闺房。
父亲一觉醒来,角巴已经不在了,说是去马群里拉马去了,这时候牧人会把马群从半山腰赶下来,去河边采食被水雾打湿的草。父亲和才让吃了甜糌粑和咸酥油茶的早饭,来到帐房外面等了一会儿,就见角巴粗声大气地唱着歌骑马走来,身后拉着一匹红亮红亮、精神昂扬的高头大马。“哈哈,强巴科长啦,你怎么感谢我哩,我给你带来了沁多草原最好的马。”说着抬腿下马。父亲快步来到枣红马跟前,朝马肚子下面瞅瞅:“还没骟掉?”又接过缰绳看了看牙齿,不禁惊叫起来,“门牙才出现,边牙还没有,岁口这么轻?”角巴说:“你也看出来啦?别看它高大,它还在长,再长就是世上第一啦。”父亲是搞畜牧的,自然懂马,看它头小,耳尖,鼻大,脸窄,脖直,胸阔,腿细,腰平,臀圆,蹄小,毛匀,皮亮,连声称赞:“好马好马,骟掉就可惜啦,有名字吗?”“我给你说过你忘啦?”“日尕?赛马会上的第一名?怪不得一见就喜欢。”“日尕”是见了喜欢的意思,父亲的喜欢就像牛羊见了牧草,河床见了雪水,星星见了黑夜,带着情不自禁的冲动。
父亲拉着日尕在帐房前的草地上走来走去,轻声细语地跟它说着话,好让它尽快熟悉自己。又把手插进鬃毛,摩挲着它弹性的肌肉,再次说:“好马好马。”父亲后来说,好马的标准不仅看外貌品相,还要看马肉、马精、马神、马心。所谓“马肉”,指的是正常情况下,好马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赘肉,也没有一丝缺少的肌肉,这不在于人给它喂多喂少,在于它自我控制的能力,它天生就知道自己是飞奔和行走的能手,吃进去多少能量,就必须挥发出多少能量,食量和挥发正好相等,所以总是在劲健的状态里保持着身段,不会饱满到臃肿,也不会峻峭到骨立。“马精”是指领悟主人意图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它应该果断、自信、顽强、勇敢而又收放自如,控制得当,好比体内有一台能够自动运转的发动机,平静、亢奋、行走、奔跑、跳跃、止步,甚至嘶鸣、咴叫,一切反应都来自本能和下意识,而又符合主人的需要,不需要一再调教。“马神”是指马对外界的感觉能力,它必须拥有非凡的听觉和嗅觉,来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以及凶吉的程度,很多情况下它会做出不服从主人的举动结果却证明它是对的,也就是说它会把对主人有利放在第一位,见机行事,灵活多变,而又一心一意。“马心”说的是它和主人的关系,它有人的感情,有对人的模仿,还有献身的勇气。它没有道德感,但它有超强的记忆,其中包括了对亲疏、敌友、是非、荣辱、对错、好恶的记忆。应该说人具备的它都具备,人不具备的它也具备。但是现在,对父亲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他只能感觉到日尕知道自己是匹好马,也知道他正在称赞它。马是喜欢称赞的,低头摆尾便是证明,但这并不能表示它也会称赞父亲。父亲觉得他跟日尕有缘分,日尕觉得呢?人人都知道人对马的挑剔,却不知道马也会挑剔人。马永远都会遵循马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人的高低,它们帮助主人的能力强弱,很多时候取决于主人本身的优劣以及它们喜欢主人的程度。
父亲拉着日尕溜达了几圈,就准备上路了。角巴又送给他一副看上去很不错的半新的包皮鞍鞯,他搭上去,绑好马肚带,示意才让上马。才让在卓玛和央金的护送下走了过来,他默然无话,话都在脸上:喜悦中带着一丝丝娇羞,好像他才是女孩儿。父亲望着才让腰带上的一把镶嵌了宝石的小藏刀问道:“哪个姐姐送你的?”才让仰头望了望央金。央金抿嘴一笑。父亲说:“谢谢啦。”角巴说:“强巴科长啦,什么时候再来蹲点?”父亲说:“这个说不准,后天或者后年都有可能。”“你不来沁多蹲点,我就去县上蹲点,反正我知道蹲点就是住上几天,到时候就住在你家里。”“我等着,有两样东西我说了你一定会来。”“什么东西?”“白馒头、甜米饭。”“噢呀,不去我就不是人啦。”角巴的妻子姜毛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布袋过来,父亲接了说:“是给才让的糖糌粑吗?谢谢啦。”又对卓玛和央金说,“跟我去县上吧?这么漂亮的姑娘县上没有。”姊妹两个笑着。
日尕走起路来快捷轻松,步幅能大能小,很快到了“一间房”。继续往前走,就是一片平坦的野苜蓿地,齐整的高度和均匀的翠绿让草浪失去了活泼的澜漪,像是在太阳底下昏昏欲睡了。风也是平和的,轻柔地抚过脸颊,留下一丝凉爽和酥痒。父亲取下嚼子,让日尕边走边吃。但它只吃了几口,就扬头加快了步子,似乎知道背上的主人想快点回到县上。父亲没有再给它套上嚼子,想试试它的领悟能力,顺便告诉它:他是信任它的。因为好马都反感强迫,很忌讳不被信任。他们走到黄昏就到了县上。父亲把日尕安顿到县政府的马厩,带才让来到他的宿舍,翻出几颗水果糖让他吃着,自己去了才让县长的办公室。
才让县长正在召集人开会,一见父亲就说:“回来了吗,这么快?”“你叫我马上回来,我能不快吗?”“你坐。”又对大家说,“散会,散会。”开会的人走了。父亲端起县长的茶缸,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坐到长条凳子上。才让县长说:“我也刚从州上回来,有人给州上反映,说沁多人民公社换汤不换药,还是部落制的老卡玛(规矩)。你蹲点的结果怎么样嘛?”父亲说:“说不定老卡玛就对啦。牧区跟农区不一样,农区是从土改到单干,再到互助组和合作社,最后成了人民公社,牧区没有进行过土改,也没有过互助组和合作社,从部落一下子变成了人民公社,部落的规矩自然就是公社的规矩。”才让县长说:“其他公社不要紧,领头人变了一切都会变。就是这个沁多公社,公社主任就是过去的部落头人,行的还是头人的办法,摆的还是头人的威风,我想把角巴换掉。”父亲说:“角巴能换吗?角巴换了谁当公社主任?”“既然公社跟部落没两样,不换是不行的。”“换掉的话牧人就什么遵循也没有啦,沁多公社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当主任。牧人对不服气的人理都不理,到时候牲畜交不上,奶子交不上,皮张交不上,你怎么办?骑着马去催?连人影子都找不到,草原这么大,等你好不容易见了人,牲畜上山啦,奶子吃掉啦,皮张做成袍子啦,命令也好,请求也罢,都成马后炮啦。”才让县长琢磨着说:“我也是藏族人,知道你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可要是不换,不就是走回头路了吗?”“稍微走一点,不要紧吧?”“要紧不要紧,你我说了不算,上级的眼睛大汪汪地瞪着呢,必须得换,而且要快,不然会犯错误的。”父亲固执地说:“我们不能说换就换,得讲一点策略。”才让县长立刻摆手打断了父亲:“这话就不要说啦,你我心里都明白。还有件事,也很急,上面已经给我谈啦,要我尽快去州上工作。县委王石书记高原反应严重,得在西宁住一阵医院,新县长是谁还不知道。王石书记的意见是,先由你代理副县长,行使县长职责。我也同意,已经报到州上去啦。”父亲愣住了,半晌才说:“啊嘘,这是怎么啦?赶着鸭子上架吗?”才让县长笑道:“鸭子是什么我没见过,你上不上架是你的事,我的事就是尽快去州上,督促州委把你的任命书下到沁多县。你代理副县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沁多公社的领导人。你先把人选好,报到州上来,无论你选谁,我都在州上支持你。”“那我就还是选角巴。”“你这个死脑筋,怎么就说不通呢。”“对了,我得声明一下,我改名字啦,以后你们就叫我强巴。”他没说这是角巴德吉给他起的。才让县长说:“这个名字好,从此你里里外外就都是个藏族人啦。”
县委和县政府合署办公,统称县政府,书记王石在西宁住院,县长才让升迁到了州上,作为代理副县长的父亲实际上成了一把手。但父亲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急急忙忙去沁多公社撤换角巴主任,而是骑着日尕去了阿尼琼贡。他早晨出发下午到达,在黄河滩的树林边找了家牧人的帐房住了一宿,然后去殿堂找曼巴给才让看病。两个曼巴两种说法,一个说是喉轮与耳轮旋转时离开了梵天线,一个说是觉悟脉遇到了黑死神的阻滞,但结论都一样:治疗是没办法啦,好好祈祷的要哩,雪山大地的眷顾下,奇迹是不会没有的。又见到一个戴眼镜的曼巴,他说西宁有大医院,公家人何必要占着食物到处寻吃的?热病和寒病打仗,身体的守护神受伤啦,伤口不能愈合时,就是这个样子。父亲说起才让聋哑的原因,提到了官却嘉阿尼和他的那一巴掌。眼镜曼巴突然大笑,走到门口说:“官却嘉你过来,公家人说你有疫病鬼的巴掌。”在不远处的空场上说话的几个阿卡推搡着一个年近三十的人走了过来。父亲吃惊地望着他:“你就是官却嘉阿尼?”“噢呀,有事吗?”“这么年轻就叫阿尼?”听到父亲说话的人都笑了。官却嘉阿尼瞪起眼睛说:“不像吗?我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大家都说像。”父亲知道,“阿尼”有祖父、外祖父、受人尊敬的老翁以及幸福博大的意思,官却嘉给自己起这么一个名字,而且别人也这么称呼,那就多少有点戏谑和嘲讽了。父亲笑道:“噢呀噢呀,像得很,可是你怎么还没走呢?”“我往哪里走?”父亲说起野马滩的桑杰希望他去超度亡妻的事,又说:“这个囊隆,光知道‘噢呀噢呀’答应,不知道落实照办。”官却嘉阿尼说:“我在阿尼琼贡是个身份显赫的人,一个牧人恐怕请不动吧?不信你问他们。”眼镜曼巴说:“对着哩,他比天上的黑老鸦显赫一点点,是喜鹊的阿尼。”官却嘉梗着脖子,认真地说:“让我去祈福?我的经是随便念的吗?那是大经,是狮子吼的经。”父亲说:“官却嘉阿尼请讲,你要什么才能去,钱还是物?”“什么也不要,就要一句话。”“一句什么话?”“阿尼啦,您好,贵体安康。”“阿尼啦,您好,贵体安康。”官却嘉呵呵一笑,抬脚就走。
父亲追上去问:“你去哪里?”“你不是让我去野马滩吗?”“这就要走?”“再不走就晚啦,亡灵变成孤魂野鬼啦,你早说我就早去啦。”“慢慢慢,还有一件事。”父亲把才让从身后拉到前面,“这个娃娃你认得吗?”“不认得。”父亲说:“你把人家一巴掌扇成了聋哑人,怎么能说不认得?”“哦?什么时候?”不等父亲细讲,官却嘉又说,“马咬的喝马血,牛啃的吃牛肉,我一巴掌扇坏的也能一巴掌扇好。”说着举起了巴掌,吓得才让赶紧往后窜,却被父亲摁住了。父亲也是心存侥幸:万一官却嘉真的能一巴掌扇好呢?“你扇,你扇。”官却嘉就扇了一巴掌,而且不轻,才让的半个脸顿时红了。父亲盯着才让看:“才让。”才让没反应。“你见没见过这个人?”才让还是没反应。父亲说:“阿尼啦,你怎么随便打人?”“是你叫我打的嘛。”“可你没有扇好他。”官却嘉诡谲地一笑:“我是有法力的,我扇坏的一定能扇好,扇不好就说明不是我扇坏的。”父亲生气地摆摆手:“话都由你说啦,赶紧去野马滩,桑杰还等着呢。”父亲看他大步走去,心说他无马可骑,得走到什么时候?又喊住他,摸出小本子,写了张纸条给他:“路过县上时往县政府拐一下,把这个交给里面的人。”官却嘉接过纸条看了看:“这是什么,公家人的经文吗?”父亲说:“是一匹马,借给你的。”“那我就知道啦,这是文书,你是个做官当老爷的,谢谢啦。”
求医无果让父亲有些郁闷,他一手拉着马一手领着才让走出了阿尼琼贡。已是中午,金灿灿的虎耳花盛开在黄河滩上,似乎既然是黄河,岸边就只能开黄花。阳光通过河水的吸收和折射变得柔软而稀疏,草色就像刻意讨好天空一样变成了湛蓝的汪洋,远远近近的山脉苍凉而超然。靠近阿尼琼贡的松林覆盖的山坡下,是一片依仗山形波荡起伏的白色旗阵,静谧而祥和。父亲拿出从县政府食堂打来的馒头给才让吃,自己也吃了几口。回去的路上,父亲给日尕上了嚼子,让它跑起来,生怕天黑前赶不到县上。日尕不停地后视着父亲,收住四蹄没有狂奔,而是用四腿交叉的大跑稳健而轻松地跑着,直到太阳落向山顶,目的地迎面而来。父亲摸摸日尕,连汗都没出,这耐力,啊啧啧,太厉害啦。这天晚上,父亲在日尕的马槽里多放了一抱草料,又喂了一块早晨从食堂打来的酥油。喂马的人不满意地说:“你对马比对人好。”“怎么这么说?”“我几天没吃酥油啦,为什么不给我?”
食堂供应的酥油都是定量的:县级干部一天二两,普通干部一天一两,其他人三天一两。定量供应的还有粮食和其他副食。父亲带着才让去食堂吃饭时,专门等着他的食堂管理员说:“县长啦,这娃娃恐怕不是你的吧?”听父亲解释了,管理员又说,“那怎么办呢?前几天你给他打饭我没说什么,原因是你下乡积攒了一些,打回去也是应该的。但是从今天这一顿开始,你只能打一份县长餐,也就是菜的话比别人多一勺,汤的话比别人多一口,馒头大家都一样,一顿二两,一天六两。”“我有个小客人就不能增加一点吗?”“每天多少粮都是按人头用秤称过的,给客人增加,就得把别人坑下,我没有这个权力。如果实在不够吃,我把我的那一份给你。”父亲笑道:“不需要。”管理员也笑笑:“还有一件事,上个月县上的供应粮迟来了一个星期,这个月一个星期都过啦,还没来,县长你看怎么办?”“你打电话催催,我也催催。”父亲把碗递向窗口,打了自己的菜说,“今天是星期六吗?”因为只有星期六才有炒菜。
父亲让才让端回宿舍吃,自己去了县政府小卖部,看有没有什么食物。小卖部里只有一种瓷噔噔的小月饼,很贵,一块钱一个。父亲一个月挣三十三块钱,交了伙食费,再给家寄些,也就剩不了多少。他一听价钱,转身就走,快到宿舍时又拐了回去,心说忘了月饼里头包着糖,应该给才让买两个。回到宿舍时,才让已经吃好,一个馒头只吃了一半,半碗白菜炒羊肉根本就没动。父亲把月饼放到菜碗旁边:“吃啊。”才让摇头,拍拍肚子。父亲说:“哪里是饱了,我知道牧人以为吃菜就是吃草,人不是牛羊为什么要吃草?你尝尝,尝尝就知道菜不是草。”说着父亲先吃了一口,又挖了一勺子送到才让嘴边,才让怯生生地张嘴吃了,感觉味道不错,便朝父亲笑了笑。父亲说:“好吃吧?拿着勺子自己吃。”这大概是才让第一次吃炒菜,香得他鼻子上都渗出了汗,快吃完时突然停下了,愣愣地望着父亲。父亲说:“我不饿,你都吃掉,还有月饼,是甜的。”才让继续吃起来。父亲说:“你跟着我肯定会想家,我有时顾不上你,但你要知道你是出来治病的,再想家也要忍着。”才让好像懂了,点点头。等才让吃完,父亲便带他去了办公室,他要打电话,想让才让看看电话是怎么打的。
“才让副州长啦,管理员反映,县上这个月的供应粮还没来,都迟了一个星期多啦。”“我知道,其他县的也没有来,我已经催过省上啦,再等等。”“还有件事,我得回一趟西宁。”“干什么去,想老婆了吗?不行。高原反应让很多外来的人待不住,牧区干部越来越不够用啦,你走了沁多县交给谁?有件事我已经快马加鞭把紧急通知下给了你,通信员连夜出发,你明天早晨就能收到。”“什么事,这么急?”“要往下边紧急调运一批牛羊肉,省上把任务压给了我们。”“你又压给了沁多?”“沁多草场最好,牲畜最多,我不压给你压给谁?”父亲说:“我真后悔给你打电话,悄悄地西宁走掉就好啦。”“你敢,我能变成老鹰把你抓回来,你信不信?”“我不信你是老鹰,但我信我是兔子,整天跑来跑去。才让副州长啦,我们是牧区,县政府机关吃个酥油怎么就这么困难?定什么量嘛,放开吃能吃多少?县级干部还好,一天二两,个人喝茶是够啦。普通干部一天一两,够干什么?家属怎么办?不是干部的三天一两,喂人呢还是喂猫呢?再说馒头,一天六两也可以,但肉和菜要供应上,要天天有炒菜,去年县政府食堂不就是这样的吗?今年怎么啦?”“你给我发什么牢骚?州上的食堂也好不到哪里去。办好食堂,全看县长。伙食差一点对你有好处,要是食堂天天都是八盘酒席,你还能增添什么?酥油也好,馒头也好,现在只要你给每人增加半两,全机关就都会说你是好县长。”
才让目不转睛地瞪着父亲,眼前的奇妙让他万难理解:父亲拿起一个黑乎乎的羊腿骨一样的东西,就能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那个人在哪里呢?父亲放下话筒说:“可惜野马滩没拉电话线,不然你就可以跟阿爸说话啦。”才让双手抚摸着话筒,抬头巴巴地望着父亲。父亲问:“你想打给谁?”才让望了望墙上的张贴画,上面有挺胸昂首的两男一女,有三面红旗和一句口号:人民公社好。他突然爬上椅子,用指头点住了中间的女人。父亲说:“哦,你是想阿妈啦,你阿妈已经远远地走啦,她这么好的人肯定在天上。跟天上的人说话,最好就是念祈福真言。”父亲带着才让离开办公室,又去马厩看了看日尕,回到宿舍后,让才让先睡下,自己趴到桌子上开始写信,信是写给家里的。写着,觉得有些饿,看桌上还有半个才让留给他的馒头,两口吞了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父亲的头一件事依然是操心才让吃喝。之后,叫来了县政府的通信员果果,让他立刻出发去一趟西宁,带着昨晚写好的信,也带着才让,又把提前打出来的自己今后两天的馒头都给了才让。才让不愿意跟父亲分手,父亲说了半天他必须去的理由,也不知他理解了没,当通信员把他抱上马背时,他哭了,没有声音,只有眼泪。父亲给他招手,他也给父亲招手,县政府大院门口,风中的告别里,一只是粗粝的大手,一只是正在粗粝的小手。果果拉马走去,他是藏族,始终保持着不在县政府门口和干部面前骑马的习惯。很快才让成了一个小小的不断回头顾望的背影,孤单而悲凉。父亲伤感地瞩望着,忽听一阵马蹄疾驰而来,州上的通信员边喊边下马:“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父亲接了通知,匆匆看了一眼,直奔办公室,一路上不断向人吆喝:“开会,开会。”有人提醒道:“今天是星期天。”父亲说:“没有啦,取消啦。”
这是父亲代理副县长而行使县长职责后,第一次召开的会,由县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决定:机关所有中层领导带人分赴各个公社,以最快速度督促完成向下边紧急调运牛羊肉的事,由于几乎所有地方既无路又无车,必须限定时间把活畜赶到县上来,由县上统一屠宰,然后联系省运输公司派车运走。另外,派人直接去省粮食厅催粮,去商业厅催副食,同时给小卖部进货,缺什么进什么,尤其是吃的,不能断了。最后父亲说了一个想法:“县上没有商店,牧民想吃点糖吃不上,想买个针头线脑买不着。县政府对面有一座土石墙木头顶的大房子,原先是头人储藏冻肉的仓库,现在里面空了,眼看就要塌掉,能不能从县财政拿出点钱,雇人修好,把机关小卖部搬到那里去?”在座的没有人说不好。财政科长旦增说:“县上的钱县长说了算,你说拿我就拿。”“那就一言为定,雇人的事总务科负责,不要忘了小卖部前平出一片场地来,方便牧民拴马扎帐房。”总务科长说:“噢呀。”
会议一完,父亲仰头喝光了茶缸里的茶,离开办公室,朝马厩走去。出发了。他知道尽管已经派人下去,但在草原上没有马到成功的事,何况正是牲畜育肥抓膘的季节,而不是冬宰的时候,公社主任也好,社员牧人也罢,都不可能你说上交多少就痛痛快快上交多少,拖拖拉拉甚至忘掉不办是很有可能的。草原人一向自由散淡,常常是你说什么都“噢呀”,回头风一吹就又忘掉啦。他作为现时唯一的县领导,必须亲自到场,一个公社一个公社说服督促。他先去了白唇鹿公社和雪豹岭公社,又去了其他五个公社,话说得嘴皮子都起皮了,还得使劲说,直到公社主任们一个个表态,用相同的思维说出了大致相同的话:“知道啦知道啦,给下边调肉和敬重雪山大地是一个样子的,亏待雪山大地就是亏待我们自己,难道草原上还有光顾自己吃肚子不管雪山大地挨饿的人?雪山大地在上,牧人辛苦放牧不就是为了上交吗?你说上交多少我们一心照办就是啦,放心吧强巴县长啦。”父亲说:“这样说就对啦,谁对雪山大地好,雪山大地就对谁好,你给人家牛羊,人家给你保佑,转经筒念祈福真言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唵嘛呢叭咪吽。”
多亏了日尕,把父亲在路上的耽搁至少减去了一半。似乎它原本就是为父亲而生,每一块肌肉都在按照父亲的意愿滚动伸缩,需要扬起四蹄时它会不遗余力,需要四腿交叉奔跑时它会把颠簸降低到最低而丝毫不减速度,有一次它居然连续奔跑了整整一下午,至少有两百五十公里。要不是天色将黑又看到了可以居住的牧家,还不知道它能跑到什么时候。父亲佩服它也佩服角巴,居然能把日尕调教得如此优秀。更庆幸角巴将日尕送给了他,他是跟马打交道的西北畜牧草原学校的学生,又在王石领导下的玛沁冈日牧马场搞过两年种马培育,后来又跟王石一起来到阿尼玛卿州,先是州畜牧兽医站站长,后是沁多县畜牧科科长,直到现在的代理副县长,可以说从来没有离开过马。日尕这样的好马他是头一次见,即便在牧马场那些一流马匹里面挑,也挑不出来,它不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它是万里、万万里挑一。人家把这样好的马给了他,他现在却要撤了人家。
十多天后,父亲走向了最后一个也是全县草场面积最大、牧户最多的沁多公社,一路走一路苦恼:怎么好意思张口呢?何况还要人家以最快速度上交牛羊肉,交得越多越好。但父亲明白,他虽然喜欢日尕,却不能拿它跟角巴的职务做交易,如果撤换角巴的结果是必须还回日尕,他只能忍疼割爱,徇私舞弊的事他绝对不做。问题是他不忍角巴下台的原因更在于角巴本人,在于他那些在草原上蜚声遐迩的经历,在于作为一个代表政府办事的人,自己不能昧着良心,硬把好人编派成坏人。当干部就得凭良心,代理副县长就是代理良心,不然要他干什么?
角巴德吉曾是沁多草原沁多部落的世袭头人,也是第一个跟马步芳对着干的人。“什么人头税、羊毛税、皮张税、酥油税,收了牧税,还收草税、牛税、羊税、马税、狗税,一头牛能剥几张牛皮?剥两张就已经连骨带肉啦,还想剥六张七张。再说草原祖祖辈辈都是部落的,你凭什么收税?”号称西北王的马步芳知道后,派麻团长前来镇压,三次血洗,杀了一百多牧人。逃过劫难的角巴来到阿尼琼贡,念叨着雪山大地,献了千盏酥油灯,然后跪地发誓:谁挡住马魔王,我就给谁当牛做马;谁赶走马家兵,我就是谁的人,要什么给什么;谁杀了麻团长,给沁多报仇雪恨,我就子子孙孙上香献贡。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他的期许就变成了现实:马魔王远走高飞,再也不来草原了,马家兵成了残兵败将,死的死,伤的伤,麻团长被新政府的剿匪部队一枪毙命。角巴一一兑现自己的誓言:拥护新政府,年年赠送一千只菜羊两百头菜牛,听说政府想成立国营牧马场,一时没有地方,就找到王石说:“我角巴可怜,金银财宝都叫马魔王刮削走啦,但祖先的草原是带不走的,一百年前有多少,现在还有多少。你们说,要哪一片,拿去就是啦。”王石说:“看着哪一片都好。”角巴说:“以我看,放马最好的草场在玛沁冈日,我把玛沁冈日献给公家怎么样?”这么着,那里的数百万亩草场便成了玛沁冈日牧马场。人民公社化时角巴又是整个阿尼玛卿州唯一一个主动把部落改成公社的头人。在公社成立大会上,王石给他披红戴花,说他是草原的雄鹰、牧人的榜样。这样一个由进步头人转变过来的公社主任,怎么能说换就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