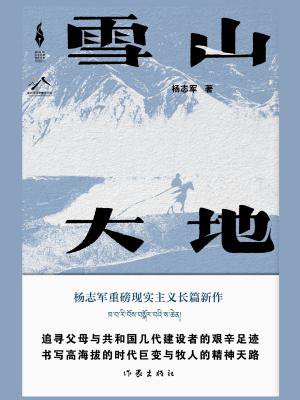1
草原疯狂地延伸着,用辽阔嘲笑着马蹄,似乎马永远走不出草原,马终究会累死在它的辽阔里。马蹄也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嘲笑着草原,似乎草原是不够踩踏的,踏着踏着就会踏没了。前往沁多公社的父亲路过“一间房”,来到前些日子到过的那片草原,看到了那座白色方塔和那座旗幡猎猎的祈福真言石经堆,却没看到角巴家的大帐房,只有扎营的痕迹固执地定位在草原上,就像残留的梦,依稀闪现着过往的日子。他前后左右转转,凭常识走向了有山的地方,这个时节的牧人大都在山上,在夏窝子里。他走过了一山又一山,看到牧草都是断了头的,黑土连片起伏,说明牛羊不久前采食过这里。可是现在呢,牧人和牲畜去了哪里?黄昏不期而至,彤云密布的西天如同新添了牛粪的火炉,草原在凄艳中静谧到死去。他正在疑惑,心说要不要原路返回,就见远处狼烟冒起,直直地如同顶天的柱子。他打马跑去,忽听一声枪响,又一声枪响。日尕戛然止步,本能地后退了几步。父亲双腿一夹说:“过去,看看是谁在打枪。”日尕看主人不怕,自己也就释然了,因为在它闻到的气息里此时并不存在什么危险。它和山风一起吹过一道缓慢的山梁,直奔高旷的风毛菊连片成海的草场。
角巴在那里,许多牧人都在那里。父亲跳下马背的同时,随手把缰绳一丢。日尕吃草去了,对它来说抓紧时间补充能量比什么都重要。父亲大步走向角巴。角巴说:“强巴县长啦,是多嘴多舌的百灵鸟把话传到你耳朵里了吗?你来得不是时候,糌粑吃不上,酥油茶没的喝。”父亲没好气地说:“你把公家人看成什么啦,酒囊饭袋吗,整天跑来跑去就为了吃喝?”“客人不吃喝,牧人不答应,你不吃喝哪来骑马走路的力气?你来了也好,看看我们牧人的伤心事吧,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哭都哭不出来啦。”说着指了指面前的山谷。山谷三面峭壁,谷底有一群牦牛,大都有气无力地卧着,有两头死在通往原野的路口,身上有血,显然是被打死的。父亲疑惑地看看山谷,又看看角巴手里的叉叉枪。角巴说:“这两头牛还有点力气,不打死就会走到外头去。”父亲更加莫名其妙:“怎么啦?”角巴长叹一声:“雪山大地保佑,让牛尸林快快过去,越快越好。”父亲吃了一惊:“什么时候发现的?为什么不上报?”“这种事怎么还能张扬?自己的疮疤自己烂,地上的泥巴地上沾,声音靠喊,瘟疫靠传,本来是碗大的,传出去就是天大的。人家会说,是沁多传过来的,连雪山大地都会怪罪。”“糊涂,你不上报,不及时采取措施,那就真是天大的灾难啦。”话虽这么说,但父亲知道角巴是对的,报告上去又能怎么样?牛尸林就是牛瘟,传染起来很快,无药可治,能做的只有封锁、隔离和扑杀病畜。父亲问起瘟疫的范围,角巴说已有三个大队发现了病畜,野马滩是最严重的,昨天在另一处深谷已经扑杀了一批。父亲这才意识到已经来到野马滩的界线上,看到大队长囊隆正带着一些人把山上的土石滚向山谷,官却嘉阿尼站在悬崖上,高声念诵着度亡的经。他问:“怎么没见桑杰?他的牲畜怎么样啦?”角巴说:“牲畜嘛,好着哩。他在野马滩住不惯,托了官却嘉阿尼给我说,还是想回野牛沟。我说回来也可以,但要是强巴县长再去野马滩蹲点,你还得搬一次家。”“搬家的不要,我也可以在野牛沟蹲点。”父亲明白,就算没有角巴的提醒,他也不会选择别人家做房东。桑杰一家是他的恩人,恩人便是一辈子的亲人。
父亲看了一会儿用土石砸死并掩埋病牛的悲惨境况,说起向下边紧急调运牛羊肉的事,角巴惊叫一声:“啊嘘,这个时候吗?”然后就呆愣着不说话。父亲说:“不好办是不是?一是不到屠宰季节,一是牛尸林蔓延。”“你说个数字我听听。”“整个沁多至少也得三千只羊、四百头牛。”“别的公社呢?”“也是这个数,起码的。”角巴喊起来:“不成不成,绝对不成。”“怎么了嘛不成?说说理由。”“我,沁多草原的角巴德吉,是跟别人一样的人吗?”父亲摇摇头。角巴说:“你说出来嘛,是风吹得头摇还是脖子软了头摇,我弄不明白。”父亲说:“你怎么能跟别人一样?你是进步头人转变成的公社主任,这样的主任草原上有几个?”“强巴县长啦,你说说肚子里的话,我这个主任州上可知道?”“当然知道。”“省上可知道?”“也知道。”“再往上就是北京啦,北京可知道?”“应该知道。”角巴望着天思考着:“这么说远远近近的公家人都知道我啦?这样的话我出的只能比别人多不能比别人少。”父亲松了一口气:“我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就直接说嘛,到底出多少才配得上我的名声?”“三千五百只羊,五百头牛。”角巴闭着眼睛咬住了牙,半晌才说:“噢呀。”父亲建议迅速召集各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开会,把上交的牛羊分摊下去。角巴说病畜最多的野马滩可以多出些力气少出些牲畜,立刻把囊隆喊到跟前,吩咐他派些牧人,连夜去通知其他大队的大队长,速来野牛沟的桑杰家开会。囊隆弯腰答应着走了。父亲问:“为什么要在桑杰家开会?”角巴说:“他家离这里比较近,又没有病畜,能喝上酥油茶。”“桑杰家没有女人,那么多人集中到一起,谁来烧茶?”“放心吧,我会带烧茶的人过去。”天就要黑了,向山谷滚够了土石的牧人纷纷离去。角巴带着官却嘉阿尼和父亲走向了野牛沟的沟垴,那儿地势高峻,风大寒冷,是瘟疫不易到达的地方,角巴家的大帐房就扎在这里。角巴说,顺沟往下走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是桑杰家的驻牧地。
父亲再次见到角巴的妻子姜毛和两个女儿,第一次见到角巴的儿子一家:夫妻两个带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女孩。他们已经睡了,听到藏獒的叫声后都爬了起来。又是一番招待,看大家都不能休息,父亲便埋头快快吃快快喝。角巴说:“不要急嘛,烫坏了嗓子怎么办?”父亲说:“饱啦。”“第一次见面的人,如果你不问清楚名字,就永远是第一次见。”他的意思是你可以边聊边吃,不着急。父亲便问起来,记住了角巴的儿子叫尼玛,儿媳叫旺姆,女孩叫普赤,大藏獒叫当周。吃完了要睡,角巴显得有些为难:最尊贵的右首里面只有一处,是让给父亲呢还是让给官却嘉阿尼?父亲挪过去,仰身躺到门边:“这个地方睡着舒服,一定能做个好梦。”这就等于把官却嘉阿尼当作了主客。角巴松了口气,望着官却嘉阿尼笑了笑。官却嘉阿尼说:“我是有法力的,身上带火,不是冬天不进帐房睡觉。”起身出去了。角巴就又把父亲请到了尊位上。父亲不再客气,睡了。他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被藏獒当周吵醒后,走出帐房一看,角巴正拿着熊皮刷子在给日尕刷毛,虽然是送出去的马,他还是放不下。姜毛和大女儿卓玛去雪线上背冰块,已在回来的路上,快到家了。尼玛收拢着昨晚的新鲜牛粪,冻成块的牛粪就像一朵朵怒放的黑牡丹。旺姆正在挤奶,边挤边小声唱着《挤奶歌》:
请问亲爱的牦母牛,
洁白的奶子哪里来?
牦母牛张嘴笑哈哈,
洁白的奶子草原来。
央金跑过去,抱住了冲父亲瞪眼吼叫的当周。父亲喜欢地摸摸央金的脸蛋,又摸摸当周的头,当周顿时安静下来。官却嘉阿尼在练习辩经,做出种种攻击对方的姿势,口中念念有词,巴掌拍得啪啪响。天亮以后还在睡觉的,只有父亲和普赤。父亲心说牧人真是辛苦,就算过去的头人现在的主任,也得勤快劳作,游手好闲和不劳而获是会受到牧人鄙视的。他走向角巴:“不好意思啦,让你伺候日尕。”角巴说:“日尕的毛没有以前亮啦,多喂些酥油的要哩,刷一刷它舒服些,它也会让人舒服些。”说着把粗糙的手伸进浓密绵长的鬃毛里,柔情地摩挲着。当周叫了一声,提醒主人注意,有人来啦。是野马滩的大队长囊隆。囊隆远远地下马,快快地走来:“主任啦,各个大队的大队长已经去了桑杰家。”角巴喊起来:“快快快,上路,早饭到桑杰家去吃,谁跟我烧茶去?”旺姆提着奶桶过来:“阿爸是叫我去吗?”角巴想了想说:“你算啦,让卓玛去。”卓玛半躺着把背上的冰块卸下来,又抱进帐房,一会儿出来说:“阿爸啦,为什么让我去?”角巴说:“少问,让你去你就去,把铜壶带上,再带些好糌粑,桑杰家的肯定不够。”央金说:“我也要去。”父亲代替角巴说:“噢呀。”角巴说:“你们两个今天穿漂亮些的要哩。”官却嘉阿尼说:“角巴啦,兔子再机灵,也躲不过鹰的眼睛。我已经看到啦。”
各大队的大队长来桑杰家开会,桑杰荣幸极了,朝人人弯腰,又做出献哈达的样子。客人也都做出了戴哈达的手势,等于说:虽然你人穷得没有哈达,但你如此殷勤,跟献了哈达是一个样子的。之后他又把腰弯向来人的坐骑,并在马脸上抹了一点酥油:贵人的坐骑自然也是尊贵的,祝福吉祥啊。卓玛和央金放下带来的一布袋糌粑,开始忙着烧茶。除了父亲,其他客人都没有进帐房。桑杰家的帐房其实只是一个众人集合的坐标,会场并不在帐房里,而是在不远处的草滩上。还没有形成河的溪流拉网一样窜来窜去,短浅的牧草以最丰富的营养显出妖媚的油绿,花有点奇怪,大大小小都带着一滴永不消失的露珠。大家席地而坐,抬眼望着高耸的雪峰和蓝到发紫的蓝天,迷恋地享受着夏天最后的晴热。角巴说:“风已经不一样啦,冷天就要来啦。”大家说:“今年好像冷得快些,牲畜要遭殃啦。”卓玛和央金很快拿来了盛满酥油茶的铜壶和糌粑匣子。桑杰在一边瞅着,不敢过来伺候。角巴招招手:“到你家里来啦,你不让茶谁让茶?”桑杰立刻过来,一一接过客人自带的木碗,从卓玛提着的铜壶里接上酥油茶,再双手递过去。这等于提高了他的身份,他满脸都是笑,像周围的花。在他给角巴端茶时,手不禁颤了一下,酥油茶洒在了角巴的袖子上,身后的卓玛习惯性地叫了声“下人”:“怎么搞的嘛。”角巴瞪了女儿一眼,翘起无名指,蘸着酥油茶弹了三下——敬天敬地敬神后,又双手捧还给了桑杰:“桑杰啦,这碗茶你喝。”桑杰惊得浑身抖起来,不仅主任给他让茶是头一次,加上敬语叫他“桑杰啦”也是头一次。同样惊讶的还有卓玛,瞪大眼睛望着角巴:阿爸啦,你这是怎么啦?桑杰接过茶碗,也是敬天敬地敬神,然后假意喝一口,再次捧到角巴面前。角巴正要伸手,官却嘉阿尼说:“你不喝我喝,我是个穷阿尼,没有自己的木碗,到哪里都是用别人的木碗。”端过去大大地咕了一口。角巴说:“卓玛你要记住,你不是头人的女儿,你是公社主任的女儿。在座的呢,不是你的叔叔,就是你的哥哥。”卓玛红着脸说:“拉索(遵命)。”官却嘉阿尼说:“那你说说,桑杰是你的叔叔呢还是哥哥?”卓玛看看比自己差不多大十岁的桑杰,一时语塞。官却嘉说:“是哥哥。”角巴说:“对着哩,哥哥。”卓玛便大大方方地说:“哥哥啦。”桑杰连叫几声“姐姐啦”,一脸惊慌地望望天空:雪山大地啊,这是怎么啦,我变得跟贵人平起平坐啦?
喝了茶,吃了糌粑,便开始议事。议事很简单,角巴熟悉沁多就像鼢鼠熟悉自己的洞,基本就是他说了算。父亲没有参加,他相信角巴会把事情办得更好,自己在场反倒多了一个障碍,角巴会不断地问:“强巴县长啦,这样行不行?”“强巴县长啦,你看怎么样?”他在帐房里跟梅朵说话:“索南和梅朵黑放牧去了吗?你想不想才让哥哥?”梅朵说:“想。”“才让哥哥肯定也想你,下次见面时他说不定就会唱歌啦:梅朵不是花里的人,梅朵她是人里的花。”梅朵咕咕咕笑起来。父亲问:“你是不是也应该用歌声回答他?”梅朵说:“噢呀。”然后就唱起来:
群山里的高峰,众马里的骏马,
我家的哥哥,草原上的好汉,
人堆里的尖子,人人喜欢的赛马王。
父亲问:“真正的骏马你见过没有?”梅朵摇头。“走走走,我领你去看。”他拉着梅朵的手,来到帐房外面,走向了在草滩上吃草的日尕。日尕看到主人,立刻仰头摆出一副目视远方的姿势,然后移动眼球,鼻孔一掀一掀地闻了闻梅朵的气味。父亲说:“这么灵性的马没见过吧?它知道你要骑它。”说着抱起梅朵放在了卸去鞍鞯的马背上。平阔的马背让梅朵无法叉开两腿骑着,她跪了一会儿,看马背纹丝不动,便站了起来。日尕朝前走去,没有一点起伏,梅朵站在马背上,也没有一点摇晃。父亲欣赏地看着:“梅朵天生是个好骑手,再长一长,就可以骑着日尕参加赛马会啦。”日尕走出去不远又走回父亲身边。父亲要抱梅朵下来,她却拽着鬃毛趴在了马脖子上。日尕立刻低头,梅朵跳到了地上。父亲说:“你们好像商量好啦。”说着摸了一下日尕,让它继续去吃草,自己拉着梅朵,走过去盘腿坐在了草地上梅朵红的身边。梅朵红一身赤炭似的长毛,卧在那里就像堆了一大堆牛粪火。它看都不看父亲一眼,耷拉着厚重的耳朵,把三角眼藏在毛后面,一眨一眨地盯着前面。它不理父亲是因为父亲在家里住过,在它的意识里住过的人就是家里人,对家里人有什么必要盯住不放呢?它需要盯紧的是开会的人,那些人它大都没见过。在它貌似漫不经心的盯视中,警惕和威慑会像风一样传给那些懂得藏獒的牧人。
桑杰和卓玛还有央金提着铜壶端着糌粑匣子朝父亲走来。父亲赶紧从上衣口袋掏出碗来:“轮到我了吗?谢谢啦。”卓玛倒茶,桑杰捧茶,央金放下了糌粑匣子。卓玛问:“强巴县长啦,下边有没有草原和牧场?”“下边没有草原,下边有田地,种的是庄稼。”“怪不得下边人要吃沁多的牛羊肉。”央金跑向不远处的溪流,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鱼。梅朵跟了过去。卓玛要去帐房继续烧茶,有礼貌地说:“强巴县长啦,你慢慢吃慢慢喝。”父亲说:“多谢啦。”桑杰弯着腰小心翼翼地问:“强巴县长啦,才让可好?”“我正要告诉你呢,阿尼琼贡的曼巴治不好才让的聋哑,我把他送到西宁去啦。西宁有我的家,家里人会照顾他,请你一万个放心。”“啊嘘,西宁?”“西宁在哪里知道吧?”“我不是西宁我不知道。”桑杰望望天又说,“西宁比太阳还要远吧?远得我都看不见啦。”“西宁比太阳近多啦,太阳在天上,无遮无拦,自然看得清,西宁在地上,山山水水挡住啦。”桑杰又望望限制了视野的山:“站在最高的山顶上就挡不住了吧?”父亲想回答又没有回答。桑杰又问:“才让什么时候能回来?”“不要着急,治好了病就会回来。”桑杰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能放下一万个心,牵扯才让的心就是放不下。”父亲笑着安慰道:“那就多念几声祈福真言,让雪山大地保佑他,你念我也念。”桑杰提着铜壶,再次望了望远方阻挡着西宁和才让的群山,念着祈福真言,给开会的人添茶去了。
父亲喝了一碗酥油茶,正吃着糌粑,就听角巴大声说:“今天明天后天,太阳落山之前,各大队必须按照分配的数字把上交的牛羊赶到‘一间房’,三千五百只羊,五百头牛,一根毛也不能少。记住啦,肥肥的羊、大大的牛,快快地赶来,传染上牛尸林的一个不要。”父亲寻思:这就对啦,角巴就是角巴,撤换的事只能往后推啦,或者根本就不要再提,完成了调肉任务,我就去州上给才让副州长说,没有角巴就没有沁多,撤换角巴跟毁掉沁多是一个样子的。
父亲当天就回了县上,午夜到达,第二天便安排屠宰和剥皮。靠近县城的公社已经把活畜赶来,牧养在周边的姜瓦草原上。一个星期的忙碌之后,省上来的五辆卡车装上了第一批内运牛羊肉。接着沁多公社的牛羊到了。角巴骑着一匹枣红马,兴冲冲来到屠宰现场父亲的面前:“强巴县长啦,我们来啦,没有来晚吧?我看见大汽车上都已经装满啦,没有空汽车啦,不会不要了吧?”“不会不会,大量的运输还在后面,我一会儿就去打电话催。”“那就好,不然我们就白忙活啦。走,去看看我们沁多的牛羊,是不是比其他公社的更好些。”父亲骑上日尕,跟着角巴去了。姜瓦草原东边的珠姆山下,个个肥壮的牛羊正在吃草。父亲一边看一边赞叹,突然看到囊隆从牛群里走来,神色紧张地叫着“主任啦”。角巴问:“怎么啦?”囊隆说:“帐房忘记带啦。”角巴说:“等公家人验收了我们就走,用不着帐房嘛。”囊隆回头看看牛群边上另外几个赶羊赶牛的牧人,几个牧人也看着他。父亲说:“县上人手不够,才让副州长从州上带了些人下来支援,即刻就到,到后立马点数验收,你们几个先去县政府食堂吃饭,碰上什么吃什么,不是节日不便招待,请多多原谅。”其实县政府食堂不负责给下面的人供应饭食,但父亲一直在下乡,食堂欠了不少他的饭菜,足够这些人吃的。角巴答应着,囊隆却为难地摇了摇头。父亲说:“客气什么,走嘛。”角巴看出囊隆有些异样,便说:“强巴县长啦,你忙你的去,食堂就不去吃啦,我们在这里吃口糌粑,等着验收。”
父亲走了。囊隆立刻来到角巴跟前,只说了一句话,就让角巴惊叫不已:“啊啧啧。”他快步走向牛群,看着那头流着眼泪和鼻涕、卧倒在地的牛,半晌无语。准备送往下边的牛群里发现了牛尸林,这可不是小事情。囊隆说:“主任啦,赶紧挖坑埋掉的要哩,给公家人就说少赶了一头。”角巴环视着散开的牛群。囊隆说:“别的都好着,再没看到流泪流鼻涕的。”“怕是好不到哪里去。”角巴知道牛尸林传染性极强,独病独死的比较少,而且有潜伏期,一旦传染开,过不了一个星期,这一片牛就都得倒下。囊隆又说:“明天后天就要宰掉,传没传染上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牛从各家各户来,聚拢到一起没几天,传染上是一个巴掌,没传染上也是一个巴掌。”他的意思是传染与否一半对一半。角巴说:“别说一个巴掌,就是一个指头,我们心里也不踏实嘛,拜雪山大地的时候想,念祈福真言的时候想,见了上面的人还是想:说不定我们送去的是不干净的肉。”“那怎么办?”“我得和强巴县长商量一下。”“主任啦,千万不能告诉公家人。”角巴没有犹豫,骑着马,再一次去找父亲。
父亲从食堂出来,攥了半个馒头边走边吃,一见角巴就说:“饿啦?又想吃啦?”角巴沮丧得叹口气:“好事情是等来的,坏事情是找来的。肚子再饿白糌粑再好也吃不下啦。”又说起病牛的事,父亲吓了一跳:“你的意思是……”“雪山大地在上,不干净的肉是不能运走的。在我们草原上,就是塔娃乞丐也不吃病牛的肉。”“说得不错,不过你也仅仅是怀疑。这样办行不行?珠姆山下有个昂欠谷,深得很,你们赶紧把牛赶进去,过一个星期再看,要是没有传染上再屠宰,要是传染上啦,就地埋葬。”“噢呀噢呀,这个办法好,羊也得全部赶进去,牛尸林也能传染给羊。”角巴拉直马缰绳就要走,父亲一把攥住:“都到食堂门口啦,哪有不吃饭的道理,再急也不在这一会儿,可惜只有白馒头没有甜米饭,白给你许下啦,以后会有的。”角巴在父亲的陪同下急慌慌吃了一个馒头,然后被父亲送出了县政府。角巴庆幸地说:“幸亏发现得早,不然就会屠宰了病牛。”父亲问:“下一步怎么办?”角巴沉重地摇头,说他不能确定牛尸林是正在消失还是正在蔓延,但上交内运牛羊是大事,他不想落下。他准备去别的公社求援,先借他们的牛羊交够沁多应该交的数,等牛尸林过去,明年后年再给他们还上。父亲觉得这样也不错,便说:“那就辛苦你啦。如果实在有困难,少交或免交也没关系,我给上面说,情况特殊嘛。”
角巴飞马来到县城北边,看到草滩上空荡荡的,只有囊隆和几个牧人正在掩埋那头已经死去的牛,喊道:“我们的牛羊呢,赶回去了吗?”囊隆跑过来,拉住角巴的马头,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才让副州长,他们看了看肥瘦,把牛羊大略一数,赶起来就走,说是验收通过啦。“你没说牛尸林的事?”“说啦,还给他们看了死牛。才让副州长说,我是个老草原,一眼就能看穿这些老牧民动的是什么心眼,想吃肉杀死了一头牛,就说是病死的,还能找借口把其余的牲畜赶回去,绝对不成。”角巴说:“雪山大地啊,这可怎么办?”掉转马头第三次去找父亲。父亲正在办公室打电话,对方的话嘟嘟囔囔怎么也听不清,他就喊起来:“第一批五辆卡车已经全部装满出发啦,等他们到了西宁,卸了车再返回就来不及啦。牧人交的是肥羊肥牛,不吃不喝两三天就会瘦下去,屠宰是不能停下的,你们赶快派车来,越快越好,越多越好,不然就放臭啦,现在不是冬天,草原没有冷库。”喊完了放下电话,大喘一口气,看到角巴立在门口,喝了一口水才问:“角巴主任啦,你又怎么啦?”
等父亲和角巴骑马奔到屠宰现场时,已经来不及了。沁多公社的三千五百只羊和四百九十九头牛全部散开,混杂在了其他公社的大片牲畜里。牛羊身上没标记,挑不出来。父亲来到才让副州长跟前,说起沁多的疫情。副州长说:“真的假的?你不要让角巴骗啦,他可是沁多草原名声远扬的大头人,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父亲急得直跺脚:“才让啦,州长啦,这些话以后再说。沁多的牛羊有可能已经传染上了牛尸林,现在混群啦,怎么能找出来?传染给别的牲畜怎么办?”才让副州长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埋怨道:“牛尸林的事你为什么不早汇报?”皱着眉头想了想,“现在你说怎么办?”“你是州长,我请示你呢。”“总不能把所有的牲畜都赶回去吧?那就等于没完成任务,你我的公家人还要不要当啦?再说有没有病畜,也只是个怀疑,赶紧屠宰赶紧运走。”“万一……”才让副州长急躁地跺跺靴子:“你这个人,办起事来拖拖沓沓,听我的,就这么办啦。”父亲呆愣片刻,走向站在不远处朝这边张望的角巴,无奈地摇摇头。角巴说:“以我的办法,把这里的牛羊统统赶进昂欠谷,圈起来,病倒一个埋一个,看冬天还有没有活着的,有,那就是没传染上病的。给内地的牛羊重新挑选,哪怕瘦的弱的,也不要牛尸林的,大不了拖延些日子嘛。”父亲又转身来到才让副州长跟前,说了角巴的意思。副州长说:“你听他的?他一个头人,当然不会爱惜集体财产,也不会像你我一样为完成任务着急上火。上面给我们是限了时间的,拖延不得。”父亲再次来到角巴面前说:“你回去吧,忙完了牛羊肉内运,我就去找你。”角巴呆然不动,茫然地望着面前的牛羊,不断自语着:“雪山大地啊,雪山大地啊,牛尸林要去下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