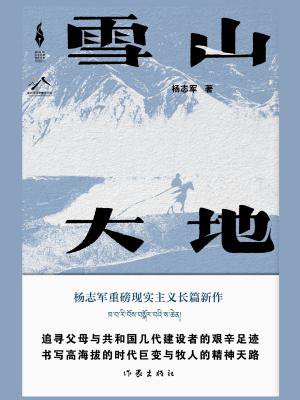3
父亲失策了,他虽然想到才让副州长也许会追到西宁,却没想到会追到家里来。不,不是追,是堵。当他和角巴拉马走过街道,来到我家的巷口时,吉普车早就守候在那里。才让副州长从车里下来,冷峻地望着父亲说:“你想干什么?连我的话都不听啦?”又对角巴说,“跑得快呗,还想往哪里跑?”角巴一声不吭,求救似的望着父亲。父亲茫然无措,心说才让副州长亲自来追,可见他寻找替罪羊的心情多么急迫,非要栽赃的话谁能挡得住?父亲从角巴手里接过缰绳说:“你先跟他去吧。”角巴乞求道:“强巴县长啦,你可不能不管我。”父亲说:“我是撒手不管的人吗?”角巴跟着才让副州长上了车,泪汪汪的。父亲追上去问:“你们要去哪里?”才让副州长不回答。车走了。父亲目送着吉普车直到消失,然后拉着两匹马走过小巷进了院子。
两匹大马来到四合院里的情形我只能想象:西房北房东房的大人小孩走出来围观,问候着父亲,父亲也问候着他们。免不了有小孩要骑马,父亲抱上去再抱下来。姥爷姥姥呵呵笑着。父亲提着一小布袋糌粑进了家门,那是离开草原的路上角巴从一顶帐房要来的。正是下午,母亲还没下班,我和才让去河滩放羊了。父亲和姥爷姥姥说了会儿话,就拉着两匹马匆匆而去。他先去了省政府,在大门前的行道树上拴了马,去传达室给办公厅打电话,说要见副秘书长李志强。对方说李秘书长下乡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准。”这可怎么办?又来到阿尼玛卿州驻西宁办事处,这里有马厩和草料,是寄放马匹的最好去处。父亲交了草料费,又给了马倌两角钱,叮嘱他好生看护。马倌是个汉族人,捋着日尕的鬃毛说:“一马一对待,一看你这两匹马,就知道一点都不能马虎。”晚上父亲回到家,不停地摸着我和才让说:“怎么都这么瘦啊?才让比在草原上瘦多啦,肋巴骨都出来啦。”晚饭吃的是糌粑糊糊,一人半碗。父亲问:“我要是不带点糌粑回来,你们晚上吃什么?”母亲说:“前天医院给每个大夫发了两棵大头菜,家里还有蔓菁,晚上就是大头菜蔓菁汤。”父亲黯然不语,半晌才说:“日子都快过不下去啦,你们还养着两只羊,为什么不宰了吃掉?”大家都看着才让。才让知道说什么,想摇头却连身子都摇起来。父亲说:“我还觉得县政府食堂吃得不好,现在看来,比你们好多啦。”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洗了把脸就出去了。他再次来到省政府,直接去了办公厅,打听副秘书长李志强去哪里下乡啦。人家说是青海湖边的天峻县。他看了看墙上的地图,估计离西宁有两百多公里,立刻回家,说要外出几天,然后直奔阿尼玛卿州驻西宁办事处。他从马厩牵出日尕,拿出工作证和钱,在食堂说破嘴皮买了一斤糌粑二两酥油,骑着日尕朝西出城去了。他连夜赶路,第二天中午便来到天峻县政府。那里的人又指给他李志强下乡的公社,他奔驰而去。
李志强吃惊父亲会跑来这里找他:“就走了一天一夜?什么马?跟汽车差不多嘛,你就不会在西宁等着?”他看了王石的信,又听父亲详细说了内运牛羊肉里混进瘟牛肉的过程,说:“我明天回省上,回去就给阿尼玛卿州打电话。”父亲在天峻县住了一宿,第二天看着李志强的吉普车上路后,才打马踏上归程。回到西宁是翌日下午,他直接去了省政府,李志强的车居然也是刚刚到达。“看来我得学会骑马,路不好,车也不好,这个时候到就已经不错了。”李志强说着,带父亲去了他的办公室,立刻拨通了阿尼玛卿州。他先给州长说,州长便叫来才让副州长解释清楚。才让副州长陈述了抓角巴的理由:一是可以认定他是故意破坏,二是省上催得紧,不得不这样。李志强气愤地说:“办公厅的文件也只是说严加追查,找到原因,没有说直接抓人,你们神经过敏什么?把人放了,需要抓的时候再抓。”才让副州长说:“人已经交给省公安厅了。”“啊?你可真是快刀斩乱麻。”原来才让副州长带走角巴后,连夜在车上审讯,第二天就带着材料去了公安厅。李志强又打电话跟公安厅联系,完了对父亲说:“麻烦了,角巴德吉自己都承认了。”父亲急得捶捶胸脯:“这个角巴,没有的事怎么能往自己身上揽?他不知道后果很严重吗?”“恐怕连你也不知道。”“那怎么办?秘书长得想个办法。”又说起角巴德吉的历史。李志强说:“这件事要办好,办不好会伤了角巴的心。”
按照李志强的吩咐,父亲拿着李志强的饭票去省政府食堂吃了晚饭,然后回到副秘书长办公室,连夜写了一份证明角巴无辜的材料,想趴到桌子上眯瞪一会儿,突然想到了日尕,赶紧来到了大门外。日尕正在站着睡觉,听到主人的脚步声后忽地扬起了头。父亲摸着它的脖子,心疼地说:“辛苦啦,我吃啦,你没吃。”说着上马去了办事处,再次寄放在马厩里,抱了两大抱干草让它吃。自己回家,睡了一会儿,便空着肚子,去了公安厅。也是李志强的主意,借口县领导有工作事项需要询问,要求见见角巴。角巴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父亲从铁门上的小窗口望见他时,他正在烦躁得走来走去,一见父亲就说:“你怎么才来?”父亲说:“你承认了,为什么?”“才让副州长说只要我承认,就放我回家。我说只要放我回家,你要什么我承认什么。”“你这个糊涂蛋,上当啦。”“那怎么办?”“翻供。”“什么叫翻供?”父亲离开时,角巴说:“强巴县长啦,你快去沁多县拿些食物来,这个地方吃不上肉,饿得肚子天天提意见。”父亲说:“忍一忍吧,我跟你一样。”
三天后,角巴放出来了。父亲的证明材料和角巴的翻供,是他获得自由的保证。但同时阿尼玛卿州委做出决定:免去父亲的副县长职务,给予党内记大过处分;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王石做出深刻检查。鉴于目前还无法知道瘟牛肉是不是给人造成了食物中毒后或病或死的结果,暂不追究刑事责任。省上认可了州上的决定,也就是说,这件事的替罪羊变成了父亲。李志强说:“这是我提的建议,只能这样,没有人承担责任是不行的,要么是你强巴副县长,要么是才让副州长,但要是让才让副州长承担责任,他一定还会揪住角巴不放。现在就看你了,如果你要保自己,就提出申诉来;如果你要保角巴德吉,就什么话也别说,悄悄回到沁多县去。以后嘛,当副县长的机会还是有的,毕竟是高海拔的牧区,严重缺少身体适应能力强的领导干部。”父亲说:“我要是提出申诉,角巴会怎么样?”李志强说:“那就又变成才让副州长的办法了。”父亲说:“好好好,只要上级的决定不变就好,我这个副县长,不当就不当啦。”
父亲去公安厅接角巴回家,一进家门,角巴就扑通一声给父亲跪下了:“强巴县长啦,谢谢啦,我以为我再也出不来了,多亏你像雪山大地一样保佑了我。”父亲赶紧扶他起来:“我已经不是副县长啦,回到沁多就得重新分配工作。”又对我们说,“按年龄算,他应该是洋洋的爷爷,藏族人叫阿尼。”姥姥赶紧去了厨房,先是端来两茶缸开水,一会儿又端来两碗掺了蔓菁的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糌粑糊糊。角巴端起来就喝,一口气喝完,又把碗双手捧给了姥姥,意思是还要喝。父亲把自己的那一碗放到角巴跟前:“你喝这个。”角巴端起来又是一口气喝完。碗被姥姥拿走了。角巴默默地盘腿坐在炕上,突然扬起头说:“姐姐啦,不用太麻烦啦,有什么就吃什么,快一点的要哩。”他以为姥姥还在给他做饭,很诧异这么长时间啦,真正的饭还不端上来。父亲和姥爷对视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你已经吃过啦,再没有啦。”角巴啊了一声,这才看到我和才让坐在门边的板凳上,一人端着一只小碗,小碗里头是清水煮蔓菁,连糌粑糊糊都没有。他下炕来到我和才让跟前,坐到地上,掐着我们两个的脸蛋,抬头问姥爷:“肉呢?”姥爷说:“现在哪里还能吃到肉?大人物小人物都吃不到。”角巴说:“我是说两个孩子脸上的肉哪里去了?”他虽然第一次见我,却也不相信我一出生就是现在这个瘦骨嶙峋的样子。至于才让脸上的肉,他真的想问问,是不是叫老鹰叼去啦?怎么原来鼓出来的脸蛋变成了两个深坑呢?家里一片沉默。角巴说:“啊啧啧,你看我是什么人嘛,到了家里连一点食物都没带,还要吃你们的。”突然张开双臂,把我和才让搂在了怀里。我们碗里的清水蔓菁全部洒在了他的皮袍上。
角巴在我家住了几天,每天只能吃一顿掺了蔓菁的糌粑糊糊。父亲带来的一小布袋糌粑已经吃完,只能从办事处高价购买,而且只能两天买一次,一次买半斤,算是办事处对本州干部的照顾。角巴急着回草原,几次催父亲上路。父亲说:“急什么,再等等。”他等着母亲回来,按照和医生的约定,母亲带着才让又去了兰州。角巴说:“那就等着,你也难得回来一趟,洋洋都这么大啦,下面也该有个弟弟或妹妹啦。”父亲说:“还等着办妥另外一件事,也跟才让有关。”原来父亲在和李志强的接触中,偶尔听说了西宁保育院。保育院原来只有二十多个孩子,这两个月突然增加到了五十多个,需要政府增加粮食和副食供应。李志强当着父亲的面,给粮食厅打电话:一定要想办法,亏谁也不能亏了这些孩子,一天三顿,一顿也不能少。父亲一打听,知道能进保育院的都是没人管的孤儿,就想才让算不算呢?才让在西宁治病,阿妈不在了,阿爸顾不上他。他给李志强说起来,李志强说你写个申请,把详细情况都写上,我交给保育院,让他们研究决定。角巴说:“保育院是干什么的,有没有肉食糌粑?不如让两个孩子跟我们走,草原再不好,也不会饿得连屁都放不出一个。”我说:“角巴爷爷,羊也可以去吗?”角巴说:“草原上有的是羊,带去干什么?就在西宁养着,养到明年宰了吃肉。”我说:“不能宰了,这是才让的羊。”
角巴没事干,又坐不住,就跟着我去河滩里放羊。看到河边低矮的土坯房,他会说:“我见过的矮房子多啦,没见过这么矮的,人怎么能住在这里头,不憋死吗?”看到有载重的卡车经过桥梁,他会提心吊胆地攥起拳头,死死地盯着,总觉得货物摞成山的卡车会压塌桥梁,每一次成功的过桥都会让他庆幸得长舒一口气。看到有人在河里捞鱼,他会说:“不念祈福真言的人啊,河里的东西是吃不得的。”有一次他坐在石头上实在无聊,问道:“你听过故事没有?”我说:“听过。”“你给我讲一个。”我讲起来:“孙悟空一个跟头到天上,打败天兵天将,吃了点心又吃桃子。完了。”“孙悟空是汉族人还是藏族人?为什么不吃糌粑?”“糌粑吃完了。”“你再讲一个。”我说:“孙悟空碰见白骨精,举起金箍棒说,你给我扯一碗拉面来,辣子和醋多放上些。完了。”“拉面有手抓好吃?”我咽着口水说:“不知道,我没吃过手抓。”“你连手抓都没吃过?太可怜啦。什么时候到我家来,我给你杀羊做手抓。”我答应着说:“我再讲一个,孙悟空大战牛魔王,牛魔王说,我们家又没有肉包子,你战我干什么?孙悟空说,快说,哪里有肉包子?完了。”“肉包子我知道,哪里有嘛?他到底吃上了没有?”“吃上了。”我的口水来不及吞咽,直接流到了地上。角巴说:“听了半天,你讲的孙悟空活像我们藏族人的格萨尔,战马一骑,走南闯北,上午吃胸叉,下午吃肋巴。”
几天后母亲和才让回来了,看了大夫开了药,差不多用光了母亲一个月的工资。角巴再次说起带走才让和我的话,母亲坚决不同意:“三种药得岔开了吃,你们不知道怎么吃,前功尽弃了怎么办?”父亲问:“治疗时间已经不短了,到底有没有效果嘛?”母亲说:“我也说不上,看病的大夫说治总比不治好,万一能治好呢?”又过了两天,保育院通过邮局送来了才让的入院通知。才让要去保育院了,父亲和母亲都松了一口气,至少那里能吃饱肚子,还不耽误治疗。角巴说:“强巴啦,现在该走了吧?你要是不走,我就一个人走啦。”离开西宁的这天,父亲和角巴从办事处牵来了马,驮上了我和才让,我和才让一人抱着一只羊。到了湟水河滩有草的地方,人和羊下来。父亲说:“给这两只羊起个名字吧,藏族人的家畜都是有名字的。”我和才让忽闪着眼睛:叫什么呢?父亲又说:“这只头上有黑色的斑点,像雨点,就叫它‘德牧’,这只的毛色就像披了一件雪花织成的衣服,就叫它‘冈拉’,记住了没?”我说:“记住了,德牧和冈拉。”父亲抱了抱才让,角巴抱了抱我,然后跨上了马背。角巴边走边喊:“扎西德勒。”父亲叮嘱我们:“早一点回家。”然后不断回望着,走了。阳光追逐着父亲和角巴的背影,把秋天最后的温暖涂抹在前去的路上,父亲的蓝色中山装和角巴镶着绿边的紫色皮袍突然融合在一起,变成了马的颜色。他们的马都是枣红马,都闪耀着明晃晃的光泽。父亲和角巴打马跑起来,很快不见了。我问才让:“草原有多大?马多还是羊多?我也想骑马。”才让看着我的嘴,突然走过去,抱起一只羊掂了掂,又过来拦腰抱了抱我,高兴地把羊牵到了我跟前。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可以骑羊,以后还会明白,骑羊的前提是我的重量不能超过羊。羊大了,已经是大绵羊了,我骑了一下德牧,看它走得踉踉跄跄,就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骑羊,以后再也没骑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才让的羊,才让对羊好,我也应该对羊好,为什么非要骑它?才让要去保育院了,以后就是我一个人放羊了。
家里人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急着要回草原的角巴又来了,还带着一个年轻的藏族人。他们把两匹马拉进院子,从马背上卸下一个圆鼓鼓的布袋和一个同样圆鼓鼓的羊肚,带着一股风走进了家门。姥爷赶紧让座,姥姥捯着小脚去了厨房。角巴把羊肚放在桌子上说:“姐姐啦,你要去烧开水吗?开水再不喝啦。”姥姥站在厨房门口说:“开水里头放些盐,放些蔓菁。”角巴说:“盐要哩,蔓菁不要。今天我来,是要吃糌粑喝酥油茶的。”说着打开了布袋,满满的都是糌粑,又打开了羊肚,满满的都是酥油。姥爷姥姥惊讶得不知说什么。我喊了一声“角巴爷爷”,扑了过去。角巴一屁股坐到地上,抱住我,用他的脸贴了一下我的脸,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袋,塞给我:“打开看看,是什么?”里面是风干肉,我抓出一块就往嘴里放。姥爷说:“煮熟了再吃。”角巴说:“煮熟就不好吃啦,现在就吃。”我把风干肉分给姥爷姥姥。三个人嘎嘣嘎嘣嚼起来。姥姥说:“给才让留上些。”角巴说:“要是放在过去,我会带些新鲜的羊肉来,可以煮一锅手抓。现在是公社,不到冬天不许宰牲。虽说我的女婿、才让的阿爸是公社主任,但也不能不守规矩。手抓我先欠着,以后一定补上。”然后指着身后的年轻藏族人说,“这是你叔叔。”又抬头望望姥爷姥姥,“我儿子尼玛是哩。”尼玛笑着弯了弯腰。姥爷说:“你这个人好,我还想你急着回草原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原来是为了我们,早一点走早一点来嘛。”姥姥烧了酥油茶,就是在水里加茯茶和盐,烧开后再放些酥油。角巴说:“草原上的酥油茶是先烧水煮茶,再加牛奶和盐,最后在奶茶里头加酥油,比这个还要香。”我心说这个已经够香啦,怎么还有比这个更香的?
角巴和尼玛喝了酥油茶,吃了几口糌粑,说要去看看才让。姥爷和我就带着他们去了。到了保育院门口,传达室的人让我们在门外等着,自己跑去叫。一会儿,一个女老师领着才让走了出来。才让穿着保育院发的黄制服,一见我们就默默淌眼泪。姥爷问:“怎么了,想家了?”才让擦掉眼泪,询问地望着我。我知道他想知道什么,赶紧说:“德牧和冈拉今天没去河滩,家里还有我割的草。”尼玛是第一次见才让,惊讶地说:“你怎么这么白?不像个草原上的藏族人。”才让的确比刚来时白了些,姥爷说这是地势低,太阳不毒,天天用肥皂洗脸的原因。角巴说:“才让可怜,肚子里有话说不出来。”姥爷说:“才来几天,他还没习惯,以后就好了。”角巴说:“你们不会不管吧?”姥爷说:“他一个星期回一趟家,星期六下午接,星期天下午送。洋洋的阿妈也会常来送药,保育院里有大夫,天天管着才让吃药。”又指着门内院子里跑来跑去打闹的孩子说,“过几天他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放心。”角巴说:“就是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不会连开水蔓菁也没有吧?”姥爷说:“保育院是公家办的,有的是办法弄吃弄喝。”说着摸了摸才让的肚子。才让知道大人们在说什么,用手比划出一个碗,指头捞了一下,又捞了一下。姥爷说:“怎么样?才让说中午吃的是面条,能做面条的都是白面,杂和面只能擀成破布衫,一片一片的捞不起来。”
看过了才让,回到家,角巴要立刻动身回去,说哪里累了就躺在哪里睡,醒了再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姥爷姥姥不答应,非要他们住一宿:“虽然没有八盘酒席招待,但是有炕,炕上睡总比野地里睡舒服些。”母亲下班回来,抱着单位发的一棵大头菜,一见角巴和尼玛就说:“是你们来了吗?巷口有喜鹊叫,一进院子就看到了马。”母亲用酥油炒了大头菜让大家吃。角巴说:“这比开水煮的好吃多了嘛。”饭间母亲问起父亲的情况:“抹掉了副县长,重新分配了什么工作?”角巴说:“听说有三个工作让他挑。”“哪三个工作?”“畜牧科长、商业科长、学校校长。”“他挑了什么?”“不知道。”“你一定把我的话带到,要是还没挑,就挑学校校长,科长之类的再也别当了。”角巴打着哈欠说:“噢呀。”我们家是一堂两厢,厨房在堂屋后面,门开在堂屋里。平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睡小一点的西厢房,姥爷姥姥带着我和才让睡东厢房。来了人,姥姥就会带我和才让去跟母亲挤,留下姥爷跟客人睡一条炕。这天晚上睡觉时,尼玛死活不脱皮袍,不盖被子,也不上炕,指着堂屋的地上说:“这个地方是最好的。”问他为什么,他说热。姥爷说:“秋天都快过去了,还热?真要是热,你就随便睡,睡到院子里也没关系。肯定是牛羊肉吃多了,以后要少吃,吃些菜的要哩。”半夜,尼玛果然就到院子里去睡了,皮袍裹身,靴子作枕,他呼呼睡到天亮。院子里早起的人都在看着他。姥爷赶紧出去解释,不是我们不让进家上炕,是他自己不肯。有人说:“知道,知道,你们是厚道人家,不会把客人赶出来。”角巴和尼玛一睡醒就走了,没吃没喝。姥爷姥姥一直在念叨:他们路上吃什么?我说:“吃牛魔王的肉包子。”
姥爷曾说:“洋洋的话,大西瓜。”意思是说我的话有一定的预言性。据说在我一岁多时,有一次我指着院门外说:“瓜、瓜。”傍晚,父亲从牧区回来,一手提着半只羊,一手抱着一个从街口买的西瓜。这一次也是,我说了肉包子,肉包子就来了。星期六下午才让被姥爷接回来,一进家门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三个包子,包子都压扁了,但没有烂。他给姥爷一个,给姥姥一个,给我一个。姥爷拿着包子,咽了一下口水,突然拉下脸来,生气地说:“才让,你把你的饭给我们拿来了吗?肯定是一顿一个包子,你是不是三顿没吃?你一个娃娃家能管住自己的肚子,我们就谢天谢地了,谁叫你操心我们了?”说着,把包子放在了桌子上,又夺过姥姥手里的包子,也放在了桌子上。我看着姥爷生气的样子,恋恋不舍地把包子还给了才让。才让看我们不吃,明晃晃的大眼立刻湿了,啪嗒啪嗒落下眼泪来,无声的哭泣里,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委屈。姥姥心疼地抱住才让,对姥爷说:“你发什么脾气?才让也是想我们了,他说不出来,就想用包子说话。”姥爷说:“我不发脾气,他下个星期还会这样。”我问:“包子说什么话了?”姥姥打我一下:“包子说才让比你知道疼人。”又对姥爷说,“别让娃娃伤心,你不吃我吃。”包子还是按照才让的心愿被我们吃掉了,馅是白菜和肉,菜多肉少,但在我们的感觉里,吃进去的全是肉。之后姥姥拿出留给才让的几块风干肉让他吃,姥爷拉着才让看了看角巴和尼玛送来的糌粑和酥油:“我们现在有吃的,千万不要从你的嘴里给我们省。你正在往大里长,不吃怎么长?将来洋洋马大,你变成小绵羊,我们对得起谁?”家里的糌粑和酥油,我们吃得很节约,也就是每天晚上一人多半碗糌粑糊糊,里面放一块拇指大的酥油。院子里的孩子、街上的孩子,有时候来我家玩,姥姥也会请他们吃一点糌粑和酥油。两个月以后,糌粑和酥油没有了,更难熬的冬天悄然来临。
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有些猛,寒冷和大雪同时降临,一夜之后,西宁就盖上了厚厚的雪被儿。我天天把德牧和冈拉关在厨房里,去河滩里扒开积雪拔干草。姥爷则天天去街上,看有什么食物可买,偶尔也能带回来几个洋芋、几个胡萝卜、一碗豌豆什么的。母亲差不多一个星期会抱回来一棵带着冰凌的大头菜和冻成冰疙瘩的蔓菁,医院有农场,农场似乎只种大头菜和蔓菁。姥姥把冻过的蔓菁和大头菜煮在一起当饭,就算我们经常吃不饱,也觉得那种难吃是饭菜里没有的。雪过天晴以后,母亲给才让请了假,带着他又去了一趟兰州,回来后沮丧地说:“大夫说这是最后一次治疗,吃完这次开的药,再不好就没办法了。”而姥爷关心的是,今天是星期五,现在是下午,得赶紧把才让送回保育院,过了晚饭时间,才让就吃不上了。他拉起才让就走。才让正和德牧、冈拉在一起,两只羊跟了出来,我赶紧挡住了它们。两个钟头后姥爷回来,庆幸地说:“正赶上吃晚饭,再差几分钟,人家就吃完了。”但晚上天刚黑,才让自己就又跑了回来。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了一根草绳,扎住棉衣下摆,在怀里揣了四个杂和面馒头。姥爷说:“你又自己没吃,又给我们拿来了?”母亲说:“肯定不是一顿的,他请了四天假,正好一天一个。老师把干的给他留下了,稀的留不住,吃掉了。”才让望着母亲说话时嘴型的变化,点点头。这天晚上,我吃着才让拿回来的馒头,那个香甜似乎从来没有过。姥爷要把才让连夜送走。才让一副不想去的样子。姥姥说:“那就算了,他想跟洋洋一起睡。”姥爷急了:“晚上不送,明天早饭吃不上,在家里他能吃到什么?”才让看姥爷执意要送他回保育院,走进厨房抱了抱德牧和冈拉。两只羊此起彼伏地叫起来。
德牧和冈拉似乎知道它们是才让用一对描金画龙的小瓷碗换来的,尽管是我在天天照顾它们——不是牵它们去河滩吃草,就是割草拔草给它们吃——但它们对我总不如对才让亲,才让来时它们会咩咩叫,走时也会咩咩叫。星期天,才让会和我一起带它们出去,它们宁肯忍着饥饿不吃草,也会待在才让身边,期待他抱一抱。才让会轮番抱起它们走很长的路。我有时也想抱,但就是力气太小抱不动。我想,羊跟人一样,要是一个母亲从来不抱自己的孩子,孩子肯定也会疏远她。除了抱,才让还会在它们身上抠来抠去。我说它们又不痒痒,你抠它们干什么?后来听父亲说,羊在长毛、脱毛或有寄生虫时都会痒痒,牧人是知道的,总会想办法解除它们的痒痒。要是才让会说话,一定早就告诉我这些了,我也会天天给它们挠痒痒。
一个星期天,母亲去医院值班,我和才让牵着德牧和冈拉正要去河滩,去街上的姥爷突然跑回来说:“快快快,粮店里卖干板鱼呢,一人只能买一斤,都走,洋洋才让今儿别去放羊了。”我们锁了家门,把羊拴在院子里,直奔粮店。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站累了的就坐在地上,用屁股一点一点往前挪。我们三个人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姥爷的手一直放在口袋里,那里有二十块钱,他必须攥在手心里才放心。干板鱼就是从青海湖打捞上来晒干后的鳇鱼,五块钱一斤,我们正好可以买四斤,也就是说四斤干板鱼要花掉母亲半个月的工资。好不容易买到了鱼,回去一看:德牧和冈拉呢?明明拴在院子里,怎么不见了?姥姥轮番敲开院子里其他三家的门:看见我家的羊没有?都说没有。我们放下鱼,就去街上寻找,逢人就问:见到两只羊没有?突然有个吃过我家糌粑和酥油的孩子从后面跑来说:“我知道你们的羊在哪里。”他带我们朝城外走去。到了城门口,姥姥走不动了,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揉她的小脚。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座土墙围起的院子前。那孩子指着关闭的院门说:“就在这里头,我看见有人把羊拉进去了。”姥爷说:“这里头是先祖的陵墓,肯定有守墓人,你们不要过去,小心有狗。”他自己蹑手蹑脚走到跟前,耳朵贴到门扇上听了听,轻轻敲了几下,看没有反应,又重重敲了几下,还是没有反应,便哗的一下推开了门。
院子里没有房屋,只有三面木头支起来的草棚,草棚下面坐着或躺着一些人。院子的一角,放着几块石头的地方,有人正在拿麦草生火,身前是一堆柴火,柴火旁边拴着两只羊,正是德牧和冈拉。姥爷走了进去,我们都走了进去。姥爷大声说:“我们的羊,怎么在这里?谁偷的?”没有人作出反应。德牧和冈拉一见我们就咩咩地叫起来。才让抢先跑过去,从柴火上解下绳子,拉起来就走。还是没有人作出反应。生火的人回头看着,一脚踩灭了已经燃起的麦草。我们牵着羊出了院子,不紧不慢地来到城门口,看姥姥还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姥爷说:“你怎么不回家?”姥姥说:“你们都在外头,我一个人回去干什么?羊找到了?好,好,这下才让高兴了。”一路走去,姥爷突然说:“坏了,还没把才让送到保育院,晚饭错过了,这可咋办?”姥姥说:“不是有鱼吗?”姥爷说:“对了,忘掉干板鱼了。”暮色降临,我们疲惫不堪地走进院子,却见一匹大马站在家门前。家里亮着灯,下班回来的母亲正在跟人说话。姥姥说:“洋洋,你阿爸回来了。”我跑进家门,看到的不是父亲,而是角巴爷爷。
角巴又来了,正在给母亲说父亲的事:就像母亲希望的那样,父亲已经是学校校长了。“草原上办学校,就是把星星搬到地上,再把星星的光搬到人心里,阿卡们都做不到,可把强巴累坏啦。”他来给我们送吃的,这次送的是一只冻羊和一羊肚酥油。姥姥迫不及待地挖了两勺子酥油,放在了才让和我的嘴里。姥爷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又说:“你来了,正好,我们有好东西招待你。”他去厨房让姥姥赶紧把干板鱼蒸上,多撒点盐,藏族人喜欢咸。很快鱼就熟了,当姥姥把三条半尺长的鱼用盘子端上来时,角巴吃了一惊:“就让我吃这个?这个不能吃,这是水里的。”姥爷这才想起藏族人不吃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他千辛万苦弄到的食物对角巴说都不能说。姥姥说:“那就吃你带来的,我们家除了你不爱吃的冻蔓菁,什么也没有。”这天晚上,鱼我们放着没动,打算角巴走了再吃。我们的晚饭是一人一碗姥姥煮的羊肉汤,汤里有肉,一人拇指大的一块。角巴把他的肉一撕两半,分别放在了才让和我的碗里,又说:“这一只羊只能细水长流煮了喝汤,不能吃手抓,手抓费肉。洋洋,我给你许下的手抓,还得欠着。”饭间,才让不止一次地跑进厨房去安抚咩咩叫的羊,羊好像惊魂未定。姥爷便说起坏人偷羊的事。角巴叹口气说:“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你们怎么还能养羊?”他拍了一下才让的头,“你是念祈福真言的藏族人,把羊拉回来是不对的。”才让瞪着角巴说话的嘴,眼睛扑闪扑闪的,突然伸手在角巴拍他的地方也拍了一下。我们知道他听懂了角巴的话,却仍然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角巴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走时又说起把才让和我带去草原的话。母亲说:“才让不能走,他还在吃药,下一步我打算带他去扎干针(针灸),大夫已经找好了。”姥爷说:“才让不走,洋洋也不能走,他走了羊谁管?”角巴说:“羊还是吃掉的好,你们不吃,就叫别人吃掉。饥荒的时候,雪山大地怪罪的不是偷窃的人,是把着食物不肯舍散的人。”才让一眼不眨地瞪着角巴说话。角巴念着祈福真言摸摸才让,也摸摸我,朝姥爷、姥姥和母亲弯了弯腰,拉起马走了。我们送他到巷口,看着他骑马消失在街道那边。
我们回身进家,姥爷要送才让去保育院,才让却跑进厨房,牵出了德牧和冈拉。姥姥说:“你牵羊干什么?叫洋洋去放,你赶紧跟你姥爷走。”才让知道姥姥在说什么,却还是拉着羊出了家门,也出了院门。姥姥要拉他回来,姥爷摆摆手制止了她:“才让是藏族人,藏族人有藏族人信的,你没听角巴说嘛?”姥姥说:“他说什么了?”母亲说:“不行,他不能这样。”追了过去,在院门外拦住了才让和两只羊。才让仰脸望着母亲,眼里泪汪汪的。母亲叹口气,突然挥了一下手:“去吧,去吧。”看我走出了院门,又说,“洋洋,你们两个一起去。”我莫名其妙地跟着才让走过街道,走向城外,来到了我们昨天来过的那座土墙围着的院子前。我说:“这里头有偷羊的坏人。”说完了才意识到我们就是来找“坏人”的。我抓住了拴着羊的绳子,想把羊夺过来,看看才让严肃而虔诚的表情,又什么话也没说,好像我跟他一样,辛辛苦苦养大了德牧和冈拉,就是为了在这样一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把它们送人。才让上前推开门,拉着德牧和冈拉走进去,看了看草棚下面坐着或躺着的那些人,最后一次给它们挠了挠痒痒,然后解下拴在它们脖子上的细麻绳,退到了门口。德牧和冈拉咩咩叫着跟过来。才让迅速转身,关上了吱吱扭扭的院门。才让跑起来,我跟着他跑起来。以后,姥姥不止一次地念叨:“后悔死了,我挡下就好了。”姥爷有一次说:“谁也没有把你捆住,你为什么不挡?你是狠不下心来把它们宰掉,毕竟是自己喂大的嘛。就算你能请个人来宰,事后你又会说,后悔死了,我怎么把羊宰掉了?我还不知道你?你别再叨叨了。”我知道姥爷说的是对的。
才让吃完了所有的药,却依然是个听不见说不出的聋哑人。母亲说:“兰州再不去了,看样子西医不成。”她把希望寄托在扎干针上,每天下班后都会去保育院把才让接出来,完了再送回去。我没事干,有时也会去保育院门口等才让。扎干针的是个老头,母亲叫他大夫,他却说我不是个草泽医人,扎针管用不管用不靠我,得靠他自己的醒力。我问什么叫“醒力”?母亲说就是苏醒的力量,好比有的人睡够了还在睡,那就是昏迷了或者死了,有的人睡够了就会醒来,醒来是要有力量的。才让的耳朵和嗓门现在睡着了,扎干针就是用针找到它的醒力,刺激它一下:你该醒了。才让望着母亲的嘴,一脸的迷茫。我知道他没有搞懂,其实我也没有搞懂。扎干针持续了一个月,还是不见效果。姥爷说:“藏族人的病恐怕还是要藏族医生治哩,不行的话领才让去藏医院看看?”母亲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是说:“藏医院我是去不成了,受不了路上的颠簸。”母亲的肚子大起来,她得为自己考虑了。姥爷说:“我领着去。”
去藏医院的这天自然是才让不上保育院的星期天。姥爷领着才让和我坐上了去湟中县的长途公共汽车,坑坑洼洼的土路颠得我们前仰后合,但我们都笑着。姥爷说:“就像我们骑了一匹大铁马,颠得屁股疼。”两个多钟头后汽车到达湟中县的县城。我们下来,顺着一条上坡路走去,临近中午时,来到了一个房子很多人很少的地方,那些有高有低的房子都在山峦里连绵,就像一座古旧而安静的城。我们在一些曲里拐弯的街巷里穿行,东看看西望望,见人就打听:“藏医院在哪里?”人们都朝上面指,我们也就顺着山峦朝上走,走到尽头,也没见藏医院的牌子,正在疑惑,就见一座绛紫色的高门上面,吱呀一声打开了一扇窗户,一个少年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招手,又指了指后面喊道:“门,门。”我们从后门走了进去,看到那个少年迎面而来:“到这边来。”姥爷问:“干什么去?”少年说:“你们自己不知道吗?那你们来藏医院干什么?”姥爷说:“我们自己能不知道吗?但就是还没给大夫说。”“不用说啦,老师知道。”少年朝前走去。
姥爷心神不定地领着我们跟过去,来到楼上一间陈设拥挤的小房子里,看到低低的床榻上端坐着一个年老的藏医。姥爷鞠了一个躬说:“大夫,我们是来看病的,这个娃娃……”老藏医摆摆手,制止了姥爷的话,然后把手伸向了才让。才让站着不动,定定地看着老藏医身后的一幅丝绸画(以后我知道它叫唐卡),画上是一头白色的大象、三只吉祥的鹿、一只威风凛凛的狮子和一些好看的花。姥爷推了才让一把说:“快,给大夫磕头。”才让正要跪下,引我们来的少年拉起才让的手,把他拽到了老藏医跟前。老藏医端详着才让,吐了吐舌头,机灵的才让也吐了吐舌头。老藏医张大了嘴,才让也张大了嘴。老藏医朝喉咙深处看了看,又抓起他的胳膊号脉,然后打开一个皮毛做的盒子,拿出了一根粗大的针。姥爷顿时有些失望:怎么还是扎干针?老藏医看着才让满是扎针痕迹的耳根说:“针已经扎得不少啦。”姥爷说:“是啊,不能再扎了吧?”老藏医说:“现在就差这一针啦,不扎的话,以前的针就是白扎。”又掰开才让的眼皮看了看,“吃了不少药吧?”姥爷说:“吃的药有一麻袋。”老藏医又说:“现在就差一种药啦,不吃的话,以前的药就等于白吃。”姥爷问:“你是说过去的针没有白扎,药没有白吃?”“噢呀噢呀。”之后老藏医用那根粗大的针轮换着扎了好几个地方,都是在头上脸上。每扎一下,才让都会皱起眉头咬紧牙,看样子很疼。然后给了药,药是一盒褐色药丸,一共七丸,说是一天一丸。姥爷说:“吃完了我们再来。”老藏医说:“不用来啦,吃了不好,那就是永远不好。”姥爷掏出一张十块的钱,双手递给了老藏医。老藏医打开身边一个木头箱子,指着半箱子钱说:“不用再给我啦,你给了我,我也是给别人。”姥爷收起钱,带着我们匆匆往回赶,一路上一直在嘀咕:“不会看错吧?我们没说才让是聋子是哑巴,大夫怎么知道要看什么病?”我们坐着最后一班长途车回到了家,天已经黑透了。
又是吃药,七天很快过去了,才让依然如故。大人们再也不抱希望了,只会望着无声无息的才让唉声叹气。母亲说:“要是角巴再来,还想带走才让,就让他带走,我们没办法了。”姥爷说:“洋洋呢,也跟着去?”姥姥说:“我可舍不得,舍不得洋洋,也舍不得才让。”母亲说:“舍不得的话再别说,吃肚子要紧。”然而,角巴再也没有来。冬深了,春节就要到了。一个星期天,才让还在睡觉,早早起来要去医院值班的母亲照例叫了一声:“才让。”才让倏地睁开了眼睛。母亲不相信才让是被她叫醒的,又叫了一声:“才让。”才让扭头疑惑地看着母亲。母亲说:“才让,起来。”才让坐了起来。母亲转过身子去,不让他看到自己嘴型的变化,又说:“才让快穿衣服。”才让便从炕角拿起外衣套在了身上。“才让,你能听见了?才让能听见了。”母亲激动得喊起来。这天早晨,我们全家人围着才让问这问那。他不用死死地盯着我们的嘴判断我们的意思,就能做出反应,而且反应越来越敏捷。母亲说:“这下好了,只要耳朵能听见,就知道别人说什么,就能模仿,慢慢他自己也就会说了。”这一天,我们全家兴高采烈,母亲忘了去医院值班,姥爷忘了送才让去保育院,甚至大家都忘了饥饿,一遍遍地和才让说话,说着已经说了许多遍的话,却依然兴趣盎然,一点也不觉得重复。到了晚上,临睡觉时,才让突然随着我叫了一声“姥姥”。我们惊呆了。我又说:“你叫姥爷,姥爷。”才让吃力地说:“姥爷。”“叫阿妈,阿妈。”才让说:“阿妈。”全家人都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