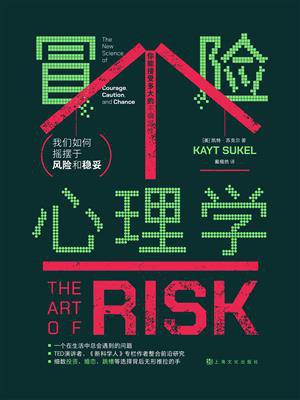第二章
冒险究竟指什么
盖尔·金(Gayle King)65岁,来自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远远看去,你就会觉得这位从事柏油研究的科学家像那种对风险避之不及的人。
事实上,他会坦率地告诉你,他不爱接受改变。他希望一切都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他和妻子结婚40年,生活幸福。(他也始终蓄着一种浓密的八字胡。)他总是穿着舒适的鞋子和夏威夷风的素雅暗纹衬衫。他有一整个衣柜的同种风格的衬衫,因此在放假聚餐时,他的家人总会为某件衬衫到底是何时、在何处买的争执不休。他曾环游世界,但更喜欢在邮轮的舒适客舱中完成旅行。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中西部人,他看重勤奋和礼貌,在生活中也践行着这样的标准。即使身处压力很大的情境下,他也脾气温和、表现得体。金的事业非常成功。虽然现在60多岁的他已经可以享受轻松的退休生活,但他喜欢固定收入带来的稳定性,于是继续工作,尽管更多的是兼职。我说过,远远看去,金是那种竭力抗拒冒险的人。不过,他很熟悉冒险行为。他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家庭农场里长大,父母从事着高风险的工作,所以他很小就明白,务农并不适合自己。
“农场上的工作完全没有保障,风险很高,压力也很大。”金指出,气候、政策和农产品市场行情等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农场的运营。这份工作也很危险。尽管农场上的工作并没有多刺激,但畜牧业和种植业的从业者总是出现在高危职业排行榜上,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农场工人受伤或死亡。
考虑到农场生活的高风险性,金想找一个能够保障稳定性与安全性的工作。他为此努力着。上大学时,他选择了他所知道的最安全的职业领域:化学。
“当我进入这个领域,我就可以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了。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受教育情况和经验判断出自己的薪酬大概在什么区间,”他坐在露台上的凳子上,远眺着海滩,手指轻轻敲着自己的肚子,“你甚至能在《化学》杂志的背面找到这些数字。拿到大学学位之后,我就找到了符合我心理预期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几乎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这样的工作,只要付出的努力足够。”
金在生活中总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做决定。他会查找这些数据,尽己所能做出分析,并根据结果做出决定。“所以风险大小对我来说,是可以通过分析数据得出的。”金自信地表示。同时,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他处理这些数据并根据结果做出安全决定的能力。
金解释风险的方法与经济学家通过实证方法研究风险的方式大致相同。在那个时代,风险并不涉及攀登珠穆朗玛峰、喝到人事不知或以100英里的时速冲下一条黑暗而曲折的路。那时风险的概念很简单,指的是在决策行为中对某一特定结果的可能性的量化。
金是个理性、重逻辑的人。他信仰的是数据分析。他甚至形容自己“有时会过度分析”,尽管通过数据分析做出决定的方式令他有安全感。用金这种方式做决定的人并不占大多数。我知道自己不是。(但是,金做决定时也不总是依靠严格的数据分析,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
变化中的冒险概念
想象一个简单的决策任务,比如掷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你会赢得1美元;如果不是,你什么也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你有50%的机会赢得1美元,很容易吧?也就是说,你赢得1美元的风险是50%,但你不会有实际的损失。所以,你知道可能出现的结果,还有50%的概率赢钱,为什么不试试呢?
但如果把条件改变一下,会发生什么呢?假设你只要问候别人,对方就会给你一枚50美分的硬币,你也可以选择通过掷硬币的方式赢得1美元。规则还像之前一样:正面朝上,赢得1美元;正面朝下,则什么也得不到。此时的风险就变得复杂了一些。你可以只打个招呼,就拿着50美分径直离开;也可以赌一把,赢得1美元。现在,你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一种情况是肯定能拿到钱(虽然少一些),另一种情况则是要么多拿一倍的钱,要么什么也拿不到。你会怎么选?
尽管径直离开就能得到50美分的意外之财,但大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毕竟,这种游戏风险不高,况且赢钱的概率始终为50%。但如果对游戏做些改变,又会发生什么呢?比如,提高赌注,延迟支付奖金,必须进行多次游戏或者和你的朋友、上司、另一半或你的妹妹的一个漂亮的女同事玩,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向游戏中加入情感因素,你会怎么办呢?或者让游戏更紧张?或者让你在一个无关任务中犯了好几个错误后再来玩这个游戏?这些正是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研究的问题。他们进行了多次实验,不断调整变量,观察人们的决定行为有何差异。
约书亚·巴克霍尔兹(Joshua Buckholtz)是哈佛大学一位研究决策行为的神经学家,他表示,认知神经学领域对风险的定义与传统经济学的很像。“我们讨论风险时,讨论的实际是某个决定出现某种后果存在一定概率,而这些概率是已知的。”他解释道。但与朴素经济学定义不同的是,这种“神经经济学”视角下的定义考虑到了风险认知的个体差异,承认人们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风险。
“以轮盘赌为例,在你下赌注之前,输赢概率非常清晰。所以,人们都会忽视那些风险较大的选项:如果我告诉你,赢10美元的概率是100%,赢12美元的概率是1%,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会下注第一个,”巴克霍尔兹说,“但人们对风险的接受度存在差异。如果告诉你,赢10美元的概率是100%,赢1000美元的概率是30%,人们的决定就会有所差别。一些人会下注确定的10美元,另一些人则会下注风险较大的1000美元。因此,在不同的风险情境下,人们会比较不同决定的主观价值,包括某一决定的收益—亏损情况、不同后果的概率以及其他因人而异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而做出决定。”
虽然经济学中风险的概念已被逐渐扩展,囊括了“因人而异的具体影响因素”,但其逻辑性依然让盖尔·金这样的人信服。风险指的依然是出现特定后果的可能性,需要我们的理性分析。然而,研究决策行为的认知神经学家(有时也被称作“神经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重要观点——人们对待风险存在个体化差异。也就是说,我对某一决定的后果的可能性做出的判断可能与其他人的迥异。
不过,尽管考虑了个体化差异,这一定义仍有不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决定并不涉及意外之财、掷硬币或者轮盘赌等行为,不会穷尽各种后果的可能性,也并不必须明确地在确定和不确定的后果之间做出选择。另外,人们也不总能保持理性,虽然我们希望如此。所以,即便我们都采取盖尔·金的方式,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做出决定——我们得承认,我们办不到——我们中大多数人也无法准确计算出某一决定的全部可能后果的发生概率。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因素简直太多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做出选择时,也许我们自己都不清楚这一选择会带来的全部可能后果。
认知神经学家扩展了传统经济学对风险的定义,但这一定义仍无法有效地运用于实验室之外,那么,我们该如何将这一定义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呢?我邀请朋友们帮我定义风险,得到了不同的回答。大多数人的定义都很具体。有一些人对风险有消极看法,认为它是“可怕的”“含糊的”“危险的”,而且是“一种无法预知结局的情况”。它被称作“赌博”或者“愚蠢的选择”。但另一些人的态度更加积极。他们表示风险是“刺激的”“令人充满活力的”,是“充满未知的”。
显然,如何看待风险取决于个人。你对风险的认知,与你的经历、价值观以及你是否渴望参加摩托车越野赛息息相关。因此,巴克霍尔兹使用了“主观价值”和“因人而异的具体影响因素”等对个体化差异的描述。个人认知是影响风险性决定的重要变量,决定了我们是大胆向前还是保守退后。
不过,不论积极或消极、具体或宽泛、共性或个性,所有对风险的定义都强调了不确定性。与传统的风险强调已知的可能性不同,现实生活中的风险意味着我们无法预知(也可能不想知道)行为的后果。
综上所述,科学家对风险或冒险并没有统一的定义。随着冒险研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等其他领域,这一定义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马文·扎克曼(Marvin Zuckerman)是一位走在前沿的人格心理学家,主要研究对象是寻求刺激者——为娱乐而寻求新奇经历的人。扎克曼将冒险定义为“对行为不良后果可能性的评估”。其他人将冒险定义为“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还有人将冒险定义为“最终将导致危险、伤害、病痛和死亡的行为”。通常来说,经济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关注的是个体如何计算冒险公式中诸多变量的价值,而其他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这种计算会导致怎样的不良后果或如何避免它们。
即使是同一位科学家,对冒险的定义也可能不同。杰夫·库珀(Jeff Cooper)曾是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决策行为研究的神经学家,如今在一家企业工作。当我询问他对冒险的定义时,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内心的教条主义与烦人的科学家立场让我认为,一切结果并非100%确定的行为都属于冒险。冒险决定与安全决定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他告诉我,“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我认为冒险是一种选择,而这个选择很可能会带来糟糕的后果。我们认为冒险是危险的——真正的危险意味着真的存在这样的后果,且你很可能见证它。”
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就算我们接纳优秀科学家的观点,坚持采用风险的基本定义,如果不将其放在实际语境中考察,我们对风险理解得再深刻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不能把计算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神经学家也在思考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在期刊《认知科学趋势》(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博士后汤姆·舍恩伯格(Tom Schonberg)呼吁学界缩小理论意义上的和自然语境下的冒险行为之间的差异。他还呼吁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设计一些符合真实风险情境的实验,而不仅仅是赌博。他的同事莎拉·赫尔芬斯坦(Sarah Helfinstein)同意他的观点。
“经济学家将风险看作简单的结果差异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现实生活。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眼中的风险。现实中,这个词尤其常和吸毒、进行无保护性行为等情况联系在一起,”她解释道,“但很多神经科学家倾向于采用经济学中对风险的定义,因为方便量化,会用到很多数学方法,而科学家都喜欢数学。但这种方式也导致问题产生:我们真的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在考察风险吗?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在考察普通人认为我们在考察的风险吗?”
像研究数学一样研究决策行为有其合理性。科学家喜欢采用这种方式,像盖尔·金一样的普通人也喜欢这种方式。然而,面对不同人群对风险定义的不同看法,我们应该如何让普通人更好地认知风险并做出更好的决定呢?我们应该如何收集必要的知识,明确哪些风险值得冒而哪些不值得呢?
日常生活中的冒险概念
也许是时候讨论一下普通人认为科学家该考察哪些冒险行为了。我想明确如何成为更睿智的冒险者,所以我需要一种对风险更生活化的定义。综合了科学家、朋友、我认识和钦佩的冒险者们的观点后,我把冒险行为定义为“一种有可能导致消极后果的决定或行为”。比如,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因为玩二十一点游戏而输掉大把工资;是否会因为要求涨薪而惹怒上司,被派去应付更挑剔的客户;或者下次跳伞时降落伞能否顺利打开。这些是我们每天做的每一个决定的组成因素——无论这些决定是早餐吃什么,还是是否要接受求婚。毕竟,生活中的决定很少自带确定的后果。生活本身就需要冒险。
诚然,数学计算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我们一生中一直在做各种决定,因此头脑也一直处于计算状态:我们衡量(通常还要调整)一项决定导致的不同后果的可能性,迫使自己做出选择,排除不可控因素,尽量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经济学家说对了一点:冒险是一种计算。不过,这种计算并不简单,也不总能保持理性。我们再说说喜欢数据推算、抗拒冒险的盖尔·金。哪怕身处赌场,他也讲究方法,循规蹈矩,极其信任数据。
没错,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盖尔·金,那个因为能根据杂志背面的数字明确自己的薪资水平才选择了当前职业的人,却喜欢时不时去赌个钱——即便他并不认为冒险是个好主意。不过他赌钱的方式和你印象中的赌徒并不一样。他在赌钱时也靠数据行动,并将博弈游戏视为一种概率上的博弈。实际上,在计算机刚刚面世时,他就计算出了很多赌场游戏的概率,包括二十一点游戏中所有结果的可能性。他甚至考虑到了不同赌场的规则造成的差异。他做得极其详细、深入,并向我介绍了他的计算过程。
“通常,二十一点游戏胜算最大,数据分析得当的话,赢率会超过99%;如果规则对玩家有利,赢率则会超过99.5%。”他对我说,下意识地捋着自己的花白胡子。他还能(并真这么做了)快速说出他计算出的不同游戏的概率:双骰子游戏的赢率为84%~99.4%,视频扑克为95%,基诺游戏为60%~65%。不过,他也承认,不论你玩什么游戏,庄家都是最大赢家。“胜算大的话,你玩的时间会更长,赢的次数会更多,但从长期看肯定是亏的,”他叹了口气,“这就是赌博的糟糕之处。”
就像我之前说的,乍一看,金是那种竭力避免冒险的人。或者说,他至少会通过计算将风险最小化,保障自己的利益。可当我问他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时,他却说他特别喜欢双骰子游戏。令人诧异的是,这位数学分析大师最喜欢的游戏并不是赢率最高的。这令我惊讶,毕竟他是那么擅长分析的人。
“我喜欢游戏中建立起来的友情,”他露出了羞涩的笑容,“周围所有的人都跟着我一起赢钱时,我感到特别快乐。我真的很享受这点。”
从金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胜算有多少,知道最终总是庄家获胜,但他还是会去赌场。尽管他玩二十一点最有把握,最有可能赢钱,但他并没有选择赢率最高的游戏,而是选择玩双骰子。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胜算并不大,但他还是投下赌注,在欢呼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摇晃骰子。
“我觉得我在掷骰子时体验到的快感跟有些人蹦极时的差不多。”他咯咯地笑着说。虽然他擅长数据分析、抗拒风险,但他发现,影响他决定的并不仅仅是数据。
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计算出赢率,可以把每个决定都转化为算式,对预期结果展开详尽的推演。不过,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忽略了整件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无法表明我们的游戏体验如何影响了我们玩游戏的方式。数据无法告诉我们,掷骰子时一群人围着你欢呼、跟着你一起赢钱是什么感受。数据无法展现游戏如何振奋人心。数据无法告诉我们游戏中的压力、情绪等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玩法。数据更无法说明,我们为什么明知会输,在玩游戏时却欢呼雀跃、无比兴奋。
因此,尽管数据分析很有用,但它无法让你在面对风险时成为睿智的决定者。就拿我男友出人意料的求婚来说吧。根据《时代》周刊中一篇文章“为什么‘二婚’更危险”的观点,我应当警惕第二段婚姻。它会暴露出我们没能从第一段婚姻的失败中吸取充足教训的事实。美国国家再婚家庭资源中心(National Stepfamily Resource Center)的数据显示,15%的再婚家庭维持不到3年;即便维持的时间更长,39%的再婚家庭也迈不过10年这道坎。这种数据注定无法带来希望和鼓舞。
但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再婚对我有益。找个伴侣会让我的生活更健康、快乐,经济上更有保障,不用独自一人面对世界。这种观点让我觉得好受一些。
我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情境下的数据,做出数据意义上的理性选择。(不过,我并不清楚该怎么计算。我可能得让盖尔·金帮帮忙,而我感觉他肯定很乐意帮我。)但是,数据不论好坏,都并不具备足以影响我决定的重要信息。那些数据无法告诉我,我的男友穿西装有多帅,他是个多么出色的父亲,以及他能如何轻而易举地获得我儿子的好感。它们无法告诉我他有多幽默,我们如何一连几个钟头说些没营养的话也甘之如饴。那些数据同样无法告诉我们,当我们因为各自有事而无法见面时我有多想他,而仅仅是瞥到他走过房间的一瞬,我的内心又如何小鹿乱撞。那些数据也无法表明我们有怎样一致的价值观与目标。总而言之,数据无法体现我们之间关系如何,以及这种关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因此,尽管在考虑他的求婚时,令人失望和欣慰的两方面数据始终在我脑海中浮现,可我很清楚,它们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
认同神经经济学家对决策行为的认知——它无外乎是一种计算,而人类是理性的,都能管理风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很正常的。但只要看看随便哪天的本地报纸,看看那些不容忽视的、由错误判断引发的各式令人担忧的结果,你就会明白,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哪怕是向来理性的盖尔·金,在赌场里也没有凭逻辑做出最优选择。我们都想在面对风险时实现利益最大化,想控制风险以获得成功和快乐,但如果我们并非始终保持理性,我们能否学着做到这一点呢?
冒险的感情色彩
研究过风险的定义后,我们再讨论一下另一个方面:谈论冒险行为时的语气。在谈论冒险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伤害以及财产损失、关系破裂的后果时,我们的语气听上去很吓人。的确,大多数可能导致危险、伤害、病痛和死亡的事肯定不符合个人利益,就算谈论的并非具体事件。我对库珀提起这种对风险的消极论调时,这位曾经的神经学家大笑着告诉我,冒险行为确实带有很多情绪因素。
“对很多人而言,风险的确带有消极含义,”他说,“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学和商科领域内对风险的早期研究。那时,这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商业决定的风险最小化。随着对风险的研究扩展到其他学科,人们接受了这一先决条件——寻求风险的最小化,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结果的确定性。人们必须遵守这一规则才能做出最优决定。”
传统的风险观念始终认为,人们应当避免冒险:商业决策的制定者通过各种手段控制风险,以保护公司的利益;父母、教师和立法者希望避免冒险,以保护孩子健康成长;流行病学者努力缩小淋病、麻疹等传播速度快的传染病的扩散范围;司法系统努力改造高风险的失足青年和囚犯,以期他们安分守己;金融从业者试图把控风险,以避免经济损失。风险这个概念在不同方面均与不良嗜好、精神不稳定等情况密切相关,这些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想避免的。不必要的伤害或死亡是所有人都想避免的。
大趋势是这样的:无论你怎么定义风险,无数人谈论它的方式会让你觉得,人们应该永远待在舒适区甚至家里才好。风险是危险的、病态的,没有一点儿好处。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社会定义风险的唯一方式。在文学作品、电影和大众文化中,对冒险行为的刻画都是极其正面的。冒险者是现实生活中的超人(和女超人),是我们最爱的名人和英雄。当我们谈论冒险者时,我们总是钦佩他们的成就,尽管潜在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而且,我们通常认为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勇于面对危险。
经久流传的故事告诉我们,愿意冒险的人——尽管他们聪明而精于计算——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冒险者能得到金钱、伴侣、威望和优渥的生活。所以,我们周围充斥着类似“高风险,高回报”“不付出,没收获”“勇者取胜”的口号。我们身处的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唯有将顾虑抛诸脑后,我们的梦想才能实现。
我们对冒险的认识存在两种极端:冒险是糟糕的,会带来危险和死亡;冒险是有益的,能带来荣耀和快乐。哪种认识是正确的呢?我们如何理解这两者的矛盾,才能更好地把控生活中的风险呢?
我想明确什么风险值得冒,不,是我需要明确这一点。我想,是时候抛开这些故事,丢掉情绪包袱,专注于事实细节了。神话和童话故事听起来是很轻松,可它们虽然有趣,却无法帮助我进行自我风险计算,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它们无法解释大脑如何判断已知后果和未知后果出现的概率,如何由此选择冒险行为。它们无法解释冒险行为如何受到人类的本质——基因和生理结构的影响。它们也无法告诉我们环境因素如何影响我们计算风险的方法。
我准备抛开掷硬币等博弈游戏的思维,重新认识风险。我想知道我的基因如何影响我的决定——当我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基因能起到多大作用。我想知道我的性别如何左右我的风险认知,有哪些积极、消极影响。我想知道环境因素如何影响我选择冒险行为。我确信,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想知道,为做出正确决定,应该如何应对情绪、压力和失败。
生活中充满了风险。选择正确,成功近在眼前;选择错误,后果不堪设想。我想利用生活中的风险去实现目标。现在我明确了风险的定义,但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应当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境相结合。现在,我们就开始讲重点吧。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科学家和成功的冒险者如何看待基因在冒险行为中的作用,是否有一些人天生具有认知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