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邦:投奔哥哥当上新四军卫生兵
口述人: 王海邦
采访人: 王志龙、肖晓飞、王元萍、裴源
采访时间: 2016年9月23日
采访地点: 马鞍山市公安新村
整理人: 王喜琴、王骅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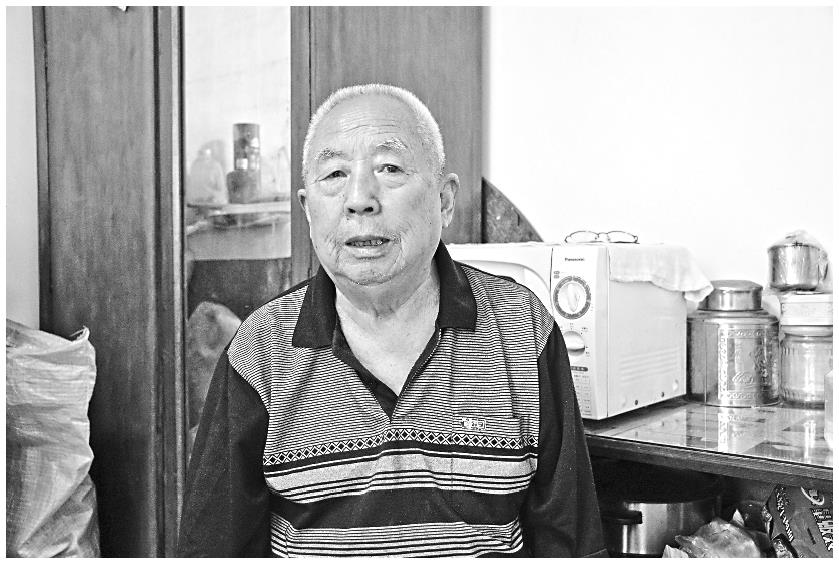
王海邦
【老兵档案】
王海邦,男,1928年5月生,河南周口西华县人。1938年国民党制造黄河花园口决堤,日军的进攻未能阻止,造成百万难民和河南大饥荒,王海邦与父亲衣食无着,1944年前往江苏泗洪县投奔在新四军4师抗大四分校的哥哥王殿邦,8月在哥哥引导下入伍抗大四分校卫生队。历任卫生队勤务兵、华东军政大学通信兵,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调炮7师20团运输队任驾驶员,1951年入朝任运输队班长,全程参加上甘岭战役,1953年回国,赴宣城炮校学习、1954年转业,赴安徽省文化干校学习,1958年到马鞍山工作。
【关键词】
抗大四分校 华东军政大学 炮兵第7师20团 上甘岭战役
一、为了温饱去参军
我叫王海邦,是河南周口市西华县红花集镇张庄村人,生于1928年5月。家中父母健全,种自家七八亩地,生活马马虎虎,在庄上属于中农,父亲叫王富春。我兄弟三人,我是老二,哥哥1937年参军,也在部队,后来转业去了山东淄博,现在已经去世了,弟弟是小学教师,现在在老家。我小时候没上过学,系统接受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抗美援朝回来后去宣城炮兵学校学习了7个月,因为不识字又送到文化干校学了3年。
我是1944年8月参军的,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呢?归根结底还是天灾加上兵祸。河南是传统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但是天灾和兵祸让我们的日子无法再过下去。1938年,由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豫、皖和江苏等地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约有千万人受灾,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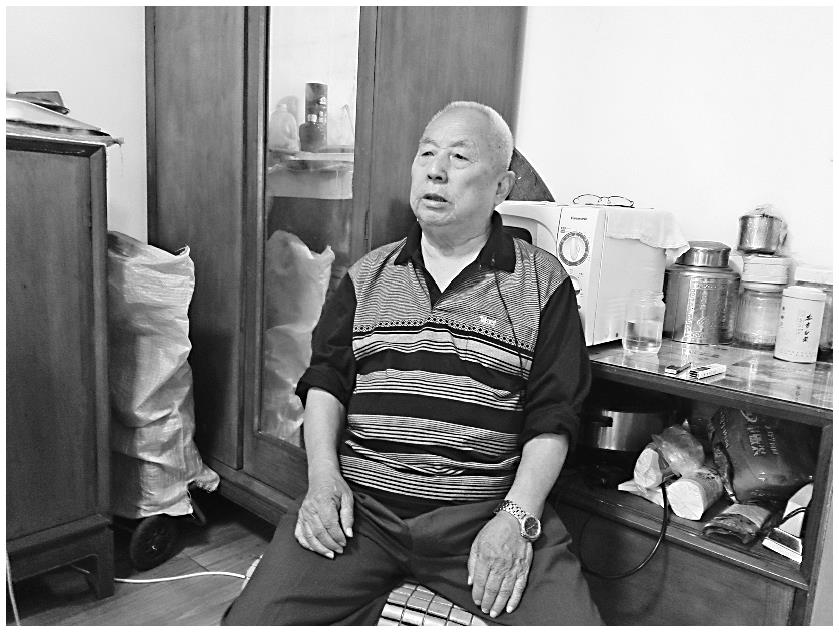
项目组访谈王海邦
我们老家那里还算边缘的,结果土地全都没了,人不能不吃饭啊,走投无路之后只好去当难民。国民党政府组织我们去淮阳,离我们老家大概300里路。政府安排我和嫂子、父亲、侄子在淮阳当难民,母亲和弟弟则仍留在西华县老家。在淮阳逃难时政府给我们安排住宿,也会给我们派粮,不够吃就自己去搜粮,有时搜不到粮,有的老百姓多给点,有的不给,不够吃的话只能去讨饭。就这样我们在淮阳呆了一年多。期间我和父亲就做点贩卖农具的小生意。但是光要饭也不行,后来得知我哥哥在新四军4师,就是彭雪枫的部队,于是就去找我哥哥。
我哥哥叫王殿邦,1919年出生,上过高小,在农村不会干农活,我父亲要打他,他吓跑了,跑出来后参加我们县城的地下党,在前线打仗受伤后去了抗大四分校学习。在四分校毕业后,被安排在造弹药的一个单位,4师有个兵工厂,制造手榴弹、土枪什么的。哥哥写信说他在做小生意,不能讲在当兵。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说家里有人是新四军,收到哥哥的信我们就准备去找他。在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后,我们就出发了。我父亲用独轮车推着侄子,我背着锅碗瓢盆,晚上随便找个地方,铺点稻草就能睡觉。沿路主要靠要饭,秋天路上的庄稼也会拿来吃。就这样我们凭着信一路摸索从淮阳到泗洪找到我哥哥,找到哥哥后我就参了军。我哥哥向领导报告了情况,领导就给我们安排事情做。我刚到部队是在抗大四分校卫生队,在江苏泗洪半城镇。父亲把我送到部队后就在部队炊事班干活,嫂子在部队服装厂工作,给士兵做衣服。后来父亲不放心,家里还有弟弟和母亲,想把母亲和弟弟接到部队来,回去找到母亲和弟弟再来泗洪,我们的部队却转移了,后来就失去联系。等到家乡的洪水退了,老百姓陆陆续续也回家了,要活命,地总是要种的,父亲就带着母亲和弟弟回家种地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整个部队去山东,后来从济南到苏州,1949年7月到南京,这时候称华东军政大学,部队驻在孝陵卫,专门培养排级以上干部。
二、抗大四分校
我1944年8月入伍,一直在抗大四分校卫生队。刚到部队,没什么想法,我就想着原来当难民没饭吃,现在有饭吃了,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干活,不要偷懒。抗大四分校全名叫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1940年3月在河南永城创建,在淮北洪泽湖畔发展,是新四军中成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所分校。抗大四分校由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兼校长,副司令员吴芝圃兼副校长,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教育长先后为刘作孚、刘清明、方中铎,支队领导成员任教员。邓子恢、张爱萍、张震、李干辉、冯文华、陈锐霆等都曾先后担任过抗大四分校的领导工作。在抗大四分校的日子是很难忘的。我们有政治课、军事课,部队有文化教员和政治指导员给我们上课。我在卫生队,主要学习包扎、换药。主要是帮助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打饭、打扫卫生。卫生队也分内外科,专门有医生救护伤员,做手术,有护士帮伤员换药,我从来没换过。我则只负责扫扫地、打打饭。那时候伤员主要是吃药,吃中药、丸药,很少打针。部队在南方生活还不错,吃大米,一天三顿饭,有时候改善生活能吃到馒头,还能吃到肉。部队里是没有报酬的,但是发衣服,穿蓝军装,冬天的衣服不是年年都有,有时候两三年发一次,夏天的衣服是年年有。衣服的料子是洋布,不是老百姓织的布,质量挺好。打内战到山东后,条件艰苦,吃得不好,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后,在山东三年多吃窝窝头,有时候好几天搞不到饭。现在想想,还是南方生活好些,北方生活比较艰苦。抗大四分校非常大,除了卫生队,还有军事队、政工队,每个大队分三个连队。卫生队的房屋就是老百姓的住家,住宿也在老百姓家,上课就在外面的场地上,印象中没用过地主家的房子。我们卫生队有100多人,女同志不多,队长倒是个女的。卫生队接待伤员最多时有几十个人,有从前线来的,也有学员生病来治疗的。这些伤员如果死亡的话,只能就地掩埋。
在卫生队的时候,日军经常来“扫荡”,所以部队经常要挪地方,日军一来,我们就躲到洪泽湖里去了,在小船上生活,船是附近老百姓的,有时候在船上要1连生活好几天,最多一次在船上呆过十几天。机关有事务长,吃饭就靠他们在岸上烧好,把饭送到小船上,我们医护人员和伤员吃的没什么区别,伤员吃的相对要好一点。在南方时,有时候会吃到鸡肉。抗大四分校是新四军的机关单位,不是战斗部队,所以我没见过日军。日军不定期来“扫荡”,去村子里杀人放火,我也了解许多日军烧杀抢掠的事,但没有亲身经历过。
伤员都是从前线受伤的,伤胳膊断腿的常有的事,恢复后有的还能上前线,有的不能战斗的就去后方或安排在其他机关,但没有送回家的。那个时候征兵不容易,兵源难搞,哑巴聋子也有来当兵的,去了部队可以当炊事员,挑水啥的,这些活都需要人。所以,只要你去当兵,部队都愿意要。抗战要扩大部队,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你不去,会来好多人强行把你抓去。我们的部队士兵大部分都是自愿的,一般都是部队去地方动员,宣传抗日,宣传日军烧杀抢掠,动员老百姓积极参军。
1947年,在山东的时候,我们有个洗衣班的女同志,被疯狗咬了,不久她也疯了。不得已把她关到小房子里,我们不敢去给她送饭,你要进去她给你身上吐唾沫,会传染给你。如果不把她关起来,她就会到处跑,最后这个女同志不幸饿死了。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很少有西医的针水,吃穿全靠解放区的老百姓。在山东,穿的是老百姓织的粗布,看上去粗糙难看,可是能发服装就已经不简单了。
卫生队的娱乐活动很少,我们平时也学唱歌,那时候也不会跳舞,就唱一些军歌。有时候也有文工团来唱歌,但来的很少。一般是晚会,过节的时候活动规模会大一些。
我在部队的日子里,没有回家探过亲,但请人帮忙写过信给家人报平安。我不识字,就找个识字的战友帮我写信,内容一般多是我很好,不用担心啥的。我1951年二三月份到了朝鲜,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回来。从朝鲜回来后,我父亲就去部队找我,让我回老家结婚,那是我出门后第一次回老家。
三、抗战胜利后辗转各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我们部队在淮安,听到消息后,我们都很开心,组织游行庆祝胜利。后来跟随部队去了江苏宝应,在那儿呆了几个月,1946年六七月份我们部队从江苏涟水去了山东,到山东后学校名字改成华东军政大学。这个时候我不在卫生队了,学校都分大队了,学员几乎都学军事,我调出来去了三大队通信班,一个大队分好多中队,我们通信班的任务就是上级有什么事或命令,上传下达,来回都是靠步行,没有自行车。
解放战争时期我是通信兵。1946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飞机大炮追着轰炸,我们部队天天都在跑,白天不敢跑晚上跑,一天跑100多里路,脚上都起泡了。解放战争时期,把整个山东跑了一圈,从东南跑到东北,从东北又转到西北。1948年解放济南时,我们在潍坊,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入的党,在部队表现好的,就可以入党,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张燕北,还有一个姓左的通信兵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那时候党员不公开,我们那几个人里你也不知道谁是党员,党员通知开会的时候互相碰碰手,这都是秘密的,开会的时候通知小组,党员也是分在一个小组一个小组,一个组也就几个党员,一个礼拜有一次组织生活。开会一般都是检讨生活,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意见,表示我们的党支部在正常运转。党员预备期各不相同,中农16个月,贫农三个月,我刚填的时候是中农,后来家乡被洪水淹了,没有土地,组织上就改为贫农,所以我的预备期是三个月,1949年1月份转正。
1949年渡江后,我们从南京去了苏州。1950年从华东军大调出来去了炮兵第7师20团运输队,在紫金山东边有营房。1950年下半年在南京学开汽车,学了几个月,教练都是从国民党过来的,汽车是从国民党缴过来的,学汽车就在中山陵,一个班4个人,那时候汽车都是烧木炭的。刚开始听说部队要打台湾,后来没打台湾,我们学开汽车的调到山东,在淄博学了一个多月。因为要打仗,坐火车去了沈阳,就把车子运到辽宁宽甸县,在沈阳苏家屯区开的全是苏联车,从浮桥过去去了朝鲜。
四、艰苦的援朝岁月
我是1951年二三月份入朝的。过了鸭绿江,跑大概二三百公里才能到达前线,叫三八线,我们一个队大概是20多辆车,刚到朝鲜开始搞防空哨,那时候全靠听,不打枪,敌机来了就敲脸盆子,哗哗哗……,一响后我们就知道敌机来了,赶快把车灯关掉。车全是晚上开,白天怕敌机轰炸不能开。我们在运输队,团里有好多炮,全靠这些车从后方仓库里运到前方,送到炮阵地。在路上经常遇到飞机,牺牲了好多小伙子,他们有的车子被击中着火烧掉了,有的被烧得就剩下那么一点,我们就拿坏油桶装上遗骸,在路边把他们掩埋了。
我后来被提拔当了班长,我们一个连队有七个排,一个排有三个班。我有个战友,他拉了一车子炮弹到前方去,我到后方去拉东西,路上遇了我们还讲了一会儿话,后来他往前方去了,我就往后方开,第二天我回来后,大家说他已经牺牲了,听说跟我讲完话没多久他就被炸死了。一个熟悉的战友突然就没了,感情上冲击很大,心里非常难受。最后怎么办呢?又没棺材,就锯一些碗口粗的树,给他弄个大棺材,那个棺材太大太重,几十个人往山上抬,埋他的那个地方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一夜一夜地开车真累得够呛,开一整夜,天不太亮的时候,得赶快找个地方找个山沟,拿树枝把车子盖起来,再去找朝鲜老百姓解决吃的。他们那儿不像国内,他们的门是能随便开的,一间房子就是一家人。你进去之后,拿灯一照,看哪儿有空位,你也不用给他家人讲,你要睡觉就把你的东西放下睡呗,把你要吃的东西放在他家门后边,他起床后一看,哦!家来了几个人,他就会给你烧饭,等到八九点钟把你喊醒叫你吃饭。吃的就是我们自己带的米面,没有菜,我们经常在一条线上跑,有时候不得已也会煮些老百姓的小青菜吃。吃完饭还不能睡,还要维修车,看看哪里有毛病啊,需不需要加油啊,直等到天黑了才能出发。那时候苦啊,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43天我都参加了,我们炮7师20团在这次战役中就伤111人,亡64人,全师发射炮弹5万多发,占战役发射炮弹总数的五分之二。我们每天夜里都在运弹药,炮和弹药都是苏联的,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我参加的上甘岭战役后来闻名全世界。
在运输队的时候,我们一个人配两颗手榴弹,一杆苏联冲锋枪。有一次晚上开车,中途休息时,我把枪搁在背包底下,走的时候拿起背包就走了。走了一段路想起来忘了拿上我的枪,赶快回去找到枪,那时候丢枪是要被杀头的。1953年7月,从朝鲜回来,当时中美停战谈判停顿时回国的,过鸭绿江后回到了祖国开心得不得了,在朝鲜战场的枪林弹雨中活下来很不容易。
上甘岭战役打过之后,要派一辆车回中国,步兵师师长要求找我们的人,给他们掩护,结果就找到我来执行任务。原来这个师长的老婆来前方了,这趟回去叫我捎带她。我心想:“这怎么带?前面就我和副驾驶两人,副驾驶还是个大个子,两个人坐驾驶室都够挤的,前面怎么坐?”最后没办法,我说:“你坐上去吧!”走到路上麻烦了,一根刹车管子断了,无奈之下脱下外套把刹车管子扎好,接着开车又出了情况,车子下坡时没有留神,车速陡然快起来,猛地一刹车,车身不听使唤撞到路边树上,我低头一看,底下就是悬崖,一眼看不到底!这下死里逃生可真吓得不轻。安全回来到了她单位,她给我吃这个吃那个,我寻思着糖我也不吃,香烟我也不抽,不如直白地告诉她:“你还是搞顿饭给我吃算了!晚上我就要走。”这件事每次想起都后怕哦!
抗美援朝回来后,部队安排我去宣城炮兵学校学习了7个月,9月去南京,我们部队是南京炮7师20团,当时住在汤山。过一段时间就转业了。1954年安徽发大水,需要干部,我就到了安徽,因为我不识字,被送到省文化干校又学了三年,省干校原来在六安苏家埠,学了大概三四个月,后来搬到无为,在无为呆了一年多,在巢县呆了不到一年,1957年到合肥七里墩,1957年底毕业。1958年2月,到马鞍山共青团工作,从此一直在马鞍山生活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