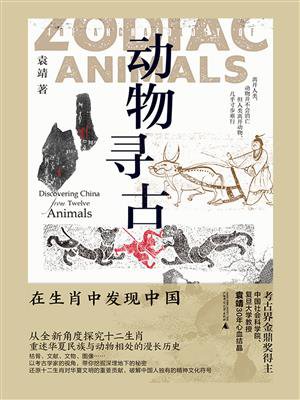农耕时代的第一生产力
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变革是伴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世界上最早的犁地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中国古代牛耕技术的兴起,很可能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从中国的古代文献及考古材料来看,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铁农具和牛耕,至战国时期,铁农具已经广泛应用,牛耕技术也有所推广。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战国策》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历史,其中提到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避免与秦交战时,历数秦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优势,其中经济上很重要的一点是“秦以牛田”,即秦人用牛犁地。把用牛犁地作为秦人取得经济优势的证据,可见牛耕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联系上文提到的春秋时期或春秋时期之前可能就存在用牛犁地的现象,但用牛犁地到战国时期尚不普及,这种耕作方式的推广耗费了数百年,可见古人对先进的生产力的认识是相当保守的,价值观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牛犁地的首要条件是让牛完全听从指挥,这样才能进行牛耕。古人利用牛鼻敏感的特点,在牛的两个鼻孔中间穿孔,然后穿上环,环上连着绳索,或直接用绳索穿在牛鼻孔上,驾驭牛时,就扯动绳索,使牛顺从人的意志,方便人的操控。世界上最早的给牛鼻穿孔的图像是苏美尔人制作的《乌尔王军旗》(图2-2),出土于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王室墓穴,距今4500年左右。《乌尔王军旗》的底盘是木头,上面用贝壳、石灰岩、天青石组成人像和动物形象等多种图案,镶嵌在沥青上,表现出色彩绚丽的画面,画面上牛和驴的鼻子上都穿环。苏美尔人给家养大型动物鼻孔穿环的年代相当早,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不能证实中国的牛鼻穿环技术是否来自西亚地区。但是,家养黄牛来自西亚地区,因而给牛鼻穿环的技术也很可能是从西亚地区引进的。

图2-2 《乌尔王军旗》上鼻子穿环的牛
中国的牛鼻穿环技术最晚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牛形牺尊(图2-3)便是春秋晚期的青铜器。这件青铜器的首、颈、身、腿等部位都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纹饰华丽繁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牛鼻上穿有一枚巨大的铜环。这种穿牛鼻的环在古代被称为“蒱”或“桊”,《说文解字》记载:“桊,牛鼻中环也。”五代时南唐的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进一步解释道:“以柔木为环,以穿牛鼻也。”现在给牛鼻穿孔有专门的金属工具,售价区区数十元,但放在数千年前的古代,给牛鼻穿孔却是古人的一项重大发明,即抓住了控制牛的关键点,残忍而有效,以至于《庄子·秋水》专门记载:“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在这里透露了他认为给牛鼻穿孔是一种毁灭自然的人为举动,他的论述充满了哲学的思考,这里不展开讨论。客观地看待历史,通过发明给牛鼻穿孔的方法控制牛、驾驭牛耕地,是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的一场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图2-3 春秋晚期的牛形牺尊
古代牛耕的图像自汉代开始出现,现在发现的汉代牛耕图像有十余幅,分别出自山东、江苏、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等地。从地域上看,这些资料集中分布于长江以北的华东北部地区和西北地区;从时代上看,从最早的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晚期,这恰好是中国北方地区牛耕技术和工具快速发展的时期。据《汉书·食货志》载,牛耕的方式为“用耦犁,二牛三人”。关于二牛三人如何搭配,比较可信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二人各牵一牛,二牛拉一犁,一人在其后扶犁。还有一种是二牛抬杠拉一犁,一人在前边牵牛,一人在辕头一侧控制犁辕,一人在后边扶犁(图2-4)。
据学者们考证,到西汉晚期,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以牛犁地时不再需要由人在前面牵牛,同时,由于出现了可供调节犁地深浅的犁箭,中间控制辕的人也不再需要,于是牛耕便发展为二牛一人的方式(图2-5),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此后,二牛一人的犁耕法便成为东汉时期牛耕的基本形式。到魏晋时期,在二牛一人式耕作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更简便的一牛一人式耕作(图2-6)。
古人驾驭牛的时候,要在牛脖子上套一副弯曲的木头,称为“轭”。有学者考证,轭的形状和放在牛脖子上的位置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牛耕使用的是直角轭,即把一根长的横木绑在两头牛的角上,横木中间与犁的长辕相连接。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民族学家在四川西部地区做调查时,发现当地还在使用这种方法驾驭牛犁地。但使用直角轭容易损伤牛角,而且主要是牛的颈部受力,耕牛的力量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此后又出现了直肩轭,即将横木由牛角后移至牛肩峰处,横木上按一定距离凿有数个小孔,用于穿绳,以便将横木固定在牛肩部,使之不易滑落,这种方式被称为“二牛抬杠”。与直角轭相比,直肩轭能充分发挥耕牛的力量,对耕牛的损伤也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木杠本身横直,与牛颈肩部位并不贴合,所以增加了役使耕牛的难度。目前发现的两汉牛耕图像中,使用的多半是直肩轭。汉代开始出现曲式肩轭,据元代王桢的《农书》载,曲轭“用控牛项,轭乃稳顺”,比二牛抬杠的直木杠更贴合牛肩部的曲线,牛的肩部受力也更均匀。魏晋时期,已经普遍使用曲式肩轭,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魏晋墓群6号墓出土的画像砖上便有耙地图,牛脖子上套的就是曲式肩轭(图2-7)。

图2-4 二牛三人耕地图

图2-5 二牛一人耕地图

图2-6 一牛一人耕地图
铁制农具及牛耕的使用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牛耕带来的第一个效果是深耕,能比较彻底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有效改良土壤,增加地力,还能进一步扩大人工施肥、水利灌溉的作用,继而明显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牛耕带来的第二个效果是取代了用人力踩耒耜翻土的劳动(图2-8),不但直接减少了人的劳动量,还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为大量开垦荒地,继而提高粮食总产量做好了铺垫。牛耕和铁犁的使用是相辅相成的。在牛耕、铁农具广泛应用的同时,再辅之以兴修水利设施,改进灌溉方法,推广人工施肥等,就能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更多的粮食,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食物保证。农业的稳步发展,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词、乐曲、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牛可谓是一肩托起了整个华夏文明。

图2-7 一牛一人耙地图

图2-8 神农用耒耜翻土的形象
自牛耕应用以来,在此后数千年里,尽管朝代不断更换,社会制度屡有变革,农村的土地政策也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农业生产中牛耕的方式始终维持,直到现代化的拖拉机出现才逐渐被取代。在使用拖拉机耕地之前,牛耕始终是中国农业的第一生产力。可见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和发展,耕牛实在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