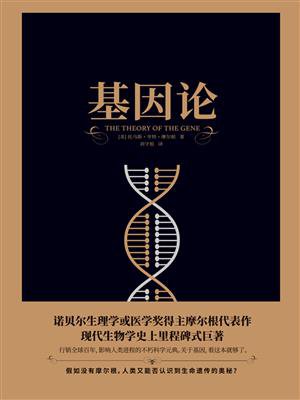第二章
遗传粒子理论
从前一章给出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生殖细胞内有遗传单元,在后代个体之间以不同的程度独立分配。更准确地说,两种参与杂交的个体的性状在后代中独立再现的现象,可以用“生殖物质内有独立单元”这一理论来解释。
这些性状为基因论提供了数据,性状本身也源于所假定的基因;从基因到性状,则是胚胎发育的全部范围。这里所陈述的基因论,并没有指出基因与其最终产物即性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这方面知识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胚胎发育过程对遗传学来说无关宏旨。毫无疑问,关于基因如何对发育中的个体施加影响的知识,将大大拓展我们对遗传的相关认知,也可能使目前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得到解释。不过,现实是现在仍然可以在不谈及基因如何作用于发育过程的前提下,解释性状在后代中的分布。
然而,在上述论点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发育过程严格遵循因果律。基因变化会对发育过程产生一定影响—它影响到以后该个体在某些情形下出现的一种或多种性状。在这一意义上,无须试图解释基因与性状之间产生关联的因果过程的本质,基因论就能得以证明。而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对该理论的不必要的批评,正是因为没有认清这种关系。
例如,有人指出,假设生殖物质中有不可见的要素,那它们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这些假定的要素的特性,正是该理论所要阐释的。不过,事实上,基因的特性只是从个体所提供的数据中推论出的。与其他类似的指责一样,这一批评没有弄清楚遗传学问题与发育问题之间的区别。
这一理论也招致了不公正的批评,批评的根据是有机体属于物理-化学机制,而基因理论却不能有效说明其中的组织机制。但是这一理论提出的假设,即基因的相对稳定性、基因自我繁殖的性质、生殖细胞成熟时基因的联合与分离,并未与物理原理不一致。虽然这些假设所涉及的物理-化学过程不能精确地表述出来,但它们至少与我们所熟悉的生物现象有关。
由于没有理解孟德尔的理论所依赖的证据,也没有认识到该理论与以往关于遗传与发育的其他粒子理论在方法上的不同,也导致了一些对孟德尔理论的批评。这类粒子理论很多,所以生物学家倾向于按照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假定存在不可见要素的理论都有些质疑。对一些早期的理论假说进行简要的检验,有助于更为清楚地指出旧方法与新方法之间的区别。

1863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生理单元论,该理论假定每一种动植物都由类似的基本单元组成。他认为这些要素比蛋白分子更大,结构也更为复杂。斯宾塞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有机体的任何部分都可以再造一个整体,卵子与精子都是这个整体的断片。每个个体的结构差异被模糊地认为是由身体不同部分中要素的“极性”或某种结晶化排列造成的。
斯宾塞的理论纯属推测性的,它赖以支撑的证据是:身体的某个部分可以制造出一个同样的全新的整体。据此,有机体的所有部分都含有可以发育成一个全新整体的遗传物质。这虽然至少部分正确,但事实上整体并不一定必须由一种单元组成。我们现在解释部分发育出全新整体的能力,也必须假定:对整体结构而言,机体的每一部分都含有构成一个整体的遗传要素,只是这些要素可能彼此不同—这一特性关系到身体的差异性。只要有一个完整的单元,就可能具有产生全新整体的能力。
1868年,达尔文(Darwin)提出“泛生说”,指出存在不同的、不可见的粒子。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粒子被称为芽体,它们持续地由身体的每一部分向外抛离;进入生殖细胞的粒子,与原本存在的其他遗传单元组合在一起。
该理论主要着眼于解释获得性性状如何传递。如果父母身体上的特性变化传递给后代,就需要这种理论。如果身体上的性状变化不传递,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883年,魏斯曼对整个传递理论提出疑问,并且说服了很多但不是全部的生物学家。魏斯曼指出获得性传递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并由此发展出有关种质独立的理论:卵子不只制造新个体,也产生新个体所携带着的与原卵子一样的新卵子;卵子产生新个体,但个体除了保护与滋养卵子外,对卵子含有的种质并没有产生其他影响。
以此为起点,魏斯曼发展了典型要素的粒子遗传理论。他引用从变异现象中得出的证据,并通过对胚胎发育的纯粹规范化的解释发展了他的理论。
首先,我们注意到,魏斯曼的观点体现在他称为遗子的遗传要素的本质上。魏斯曼的晚期著作中记载,当很多小染色体存在时,他便把小染色体当成遗子;只有少数染色体存在时,他假定每一条染色体都由几个或很多个遗子构成;每个遗子都含有对单一个体的发育至关重要的所有要素;每个遗子都是一个微观世界;遗子各不相同—每个遗子都与其他遗子在某个方面存在区别,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祖先个体或种质的代表。
动物个体的变异是由遗子各种不同的再组合导致的。这是卵子与精子结合的结果。生殖细胞成熟时,遗子的数目缩减一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遗子的数目将趋向于无穷大。
魏斯曼还构建了一个精密的胚胎发育的理论,这一理论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即随着卵子的分裂,遗子被分解成更小的要素,直到身体内的每一种细胞都含有遗子的最终成分—定子。在那些注定成为生殖细胞的细胞中,遗子的裂变不会发生,由此才有种质或遗子群的连续性。胚胎发育理论的观点超越了现代遗传理论的范围;现代遗传理论忽视发育过程,其假定条件也与魏斯曼的理论截然相反,认为身体的每个细胞里都存在着整个遗传的复合体。
由此可见,为了解释变异,魏斯曼在他巧妙的推理里引入了一些与我们今天所采用的类似的过程,他相信变异是来自双亲的单元再结合。这些单元在卵子与精子成熟的过程中减少了一半,它们各自作为一个整体并各代表祖先的一个阶段。
生殖物质的独立性与连续性的观点主要归功于魏斯曼。他批判拉马克(Lamarck)的理论,从而对澄清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性遗传理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使关于遗传的问题都变得模糊不清。魏斯曼的论著把探讨遗传学与细胞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摆到前沿位置,这也是他的一项重要成果。我们很难估计他出色的推理对我们后来尝试着从染色体构成及其行为方式的角度阐释遗传学问题产生了多大影响。
这些以及其他更早的假说,在今天只具有历史上的意义,不足以代表现代基因理论发展的主要路径。现代基因理论成立的根据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它有能力预测某一特定种类的精确的数字结果。
我冒昧地认为,虽然现代基因理论与早前理论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基因理论是根据实验得出的遗传证据一步步推导出来的,这些证据的每一处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所以它与旧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基因论不需要也不会自以为是地宣称是终极的。毫无疑问,它将经历很多变革,并循着新的方向发展。目前我们已知的绝大多数遗传事实可以通过现有理论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