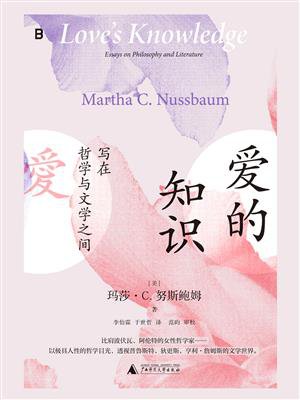前言
本书收录了我发表过的有关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论文。它在之前发表的基础上,扩充和修订了三篇文章,添加了两篇全新的文章以及一篇实质性导论。这些论文探讨了一些关于哲学和文学间联系的基本问题:探索伦理问题时风格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道德知识的性质及其与书写形式和风格的关系、情感在慎思和自我认知中的作用。文章主张建立一种同时涉及情感和理智活动的伦理理解的观念,并且相对于抽象的规则,它赋予了对特定人的感知以及情境以某种优先性。这些文章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含糊的、非理性的,它实际上更合乎理性、更精准。这些文章进一步论证,文学而非哲学通常是这种伦理观念最恰当的表达和陈述形式,并且,如果想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扩大道德哲学观念的范围,以便将这些文本囊括进来。它们试图在更广泛的伦理探询中清楚阐明文学与更为抽象的理论要素之间的关系。
这些文章隐藏在发行量不大的期刊和丛书中,非专业读者不太容易接触到。甚至对于学术读者来说,其中一些也很难读到。学科定位也是个棘手的问题。这些文章跨越了传统学科的界限,而且我认为,如果不跨越这些界限,某些重要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答。但讽刺的是,正是由于这些文章所批判的学科割裂,这些文章基本上被相互分离,发表它们的出版物,有些是哲学家读的,有些则是文学学者读的。目前的这部作品集应解决这一问题,使所有读者不分背景和兴趣,都可以对它们以整体的方式进行评估。
本书与我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紧密相关,尤其是《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即将出版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以及即将出版
 的基于1986年马丁古典讲座内容写成的《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
的基于1986年马丁古典讲座内容写成的《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
 。这些书中有关文学和伦理的讨论都在本书中得以延续。本书还收录了两篇与《善的脆弱性》同时期创作并已发表的文章《感知的洞察力》和《柏拉图论可通约性与欲望》。它们比某些文学论文更详细地阐述了伦理学中部分重要的概念,本书对这些概念做了整体性研究。(前者已针对本书进行了修订和扩展。)先前未发表的《超越人性》,将我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与本书探讨的当代问题关联起来。《索福克勒斯<菲洛克忒忒斯>中的结局与性格》(《哲学与文学》,1986—1987年第1期第25—53页)以及《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关于学习实践智慧》(《耶鲁古典研究》,1980年第26期第43—97页),这两篇较早创作的关于古希腊文献中哲学与文学联系的文章并没有收录于此。我仍然赞同以上作品中的论点,并希望有机会将它们收录于其他文集中。但由于它们在讨论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问题时,没有问及伦理内容与文学形式的关系,因此,比起其他囊括这些讨论的论文,这两篇略偏离本书的中心论点。
。这些书中有关文学和伦理的讨论都在本书中得以延续。本书还收录了两篇与《善的脆弱性》同时期创作并已发表的文章《感知的洞察力》和《柏拉图论可通约性与欲望》。它们比某些文学论文更详细地阐述了伦理学中部分重要的概念,本书对这些概念做了整体性研究。(前者已针对本书进行了修订和扩展。)先前未发表的《超越人性》,将我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与本书探讨的当代问题关联起来。《索福克勒斯<菲洛克忒忒斯>中的结局与性格》(《哲学与文学》,1986—1987年第1期第25—53页)以及《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关于学习实践智慧》(《耶鲁古典研究》,1980年第26期第43—97页),这两篇较早创作的关于古希腊文献中哲学与文学联系的文章并没有收录于此。我仍然赞同以上作品中的论点,并希望有机会将它们收录于其他文集中。但由于它们在讨论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问题时,没有问及伦理内容与文学形式的关系,因此,比起其他囊括这些讨论的论文,这两篇略偏离本书的中心论点。
我最近几篇关于希腊的文章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但没有收录在内,它们将被修订并出现在《欲望的治疗》中。它们是:《治疗性论证: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自然的规范》,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第31—74页),《斯多亚学派论根除激情》(《阿派朗》,1987年第20期第129—175页),《超越痴迷和厌恶:卢克莱修论爱欲的治疗》(《阿派朗》,1989年第21期),《凡间的不朽:卢克莱修论死亡与自然之声》(《哲学与现象学研究》,1989年)以及为纪念斯坦利·卡维尔,即将出版的由T.科恩和P.盖尔编辑的《灵魂中的巨蛇:解读塞涅卡的〈美狄亚〉》。斯多亚学派那篇详细阐述了情感和信念的联系,上述文章中有几篇对此论述得更为简要。塞涅卡那篇探讨了爱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与《感知的平衡》《斯蒂尔福斯的手臂》这两篇联系特别密切。关于卢克莱修的作品与《叙事情感》密切相关。在欧里庇得斯《酒神的女信徒》的新译本(于1990年由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出版,C.K.威廉姆斯译)序言中,我进一步探讨了一些《超越人性》中讨论到的关于人性与超越的问题,并更深入地评论了亚里士多德与希腊悲剧的关系。
在写作关于哲学与文学关系的当代问题时,我略去了在《新文学历史》原刊中随《有瑕疵的水晶》一同发表的对理查德·沃尔海姆、帕特里克·加德纳和希拉里·普特南几人的回复。这些主要观点在导论和《有瑕疵的水晶》的尾注中均有提及。我对保罗·西布赖特关于《一位女士的画像》的论文的评论文章也没有收录进来,它与《叙事情感》同册出现在《伦理学》杂志中。我计划将其扩展成一篇独立论文。我的部分评论和评论性文章涉及了文学/哲学问题。其中唯一收录进来的一篇是关于韦恩·布斯《我们所交往的朋友:小说的伦理学》一书的——因为这是篇很独立的文章,也因为它讨论的是一部将在未来几年一直会被阅读的重要著作。
在导论之外,我还写了尾注,因为我觉得有更多问题需要被讨论和澄清,而不是仅仅在导论中用一行论证简单概括。尾注对各篇文章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具体评述,并指引尚未阅读导论的读者了解其中讨论的一些中心理论问题。
为了引用的一致性,所有脚注都做了调整。必要处已将参考资料更新。
玛莎·C.努斯鲍姆
1989年10月于罗得岛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