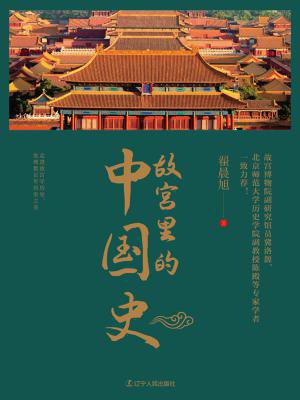庆寿寺之谋
意外发生在两年后的夏天,就在这一年,皇太子朱标因病逝世,年仅三十七岁。
朱标的死是一场“蝴蝶效应”,很快在整个大明朝引起巨大的风暴。
壹
首先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的是朱元璋,老来丧子。洪武皇帝朱元璋戎马一生,活到七十一岁,已经是相当的硬朗了,估计朱元璋自己都没想到他是大明朝最长寿的皇帝。
古代人均寿命比较低,所以年纪大的皇帝免不了要面对皇太子英年早逝的问题。换成一般皇帝可能还好,但朱标属于开国皇太子,他当太子的时间跟朱元璋当皇帝的时间一样长,班底都给他搭好了。
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的时候,朱元璋开始让朱标代理国政,比朱棣就藩北平还早三年。朱元璋连太子幕府都没有设立,所有的重臣全都在太子府有兼职。其中,开国第一文臣李善长担任太子少师,中山王徐达兼太子少傅,大将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后面跟着冯胜、刘基等一批名臣。
简而言之,朱标可能是整个明朝历史上最稳的皇太子,整个洪武朝只有一个“太子党”,就是朱元璋本人,其他人都得往后站。
结果朱标一死,朱元璋所有的政治安排全乱套了,必须把手底下那些人清理一遍才能安排继承人。所以,他被迫清理了蓝玉、冯胜、傅友德等一批大将,导致本来人才济济的明朝军界居然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尴尬现象,也为后面建文朝的无人可用埋下了伏笔。
朱标之死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迁都。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朱元璋改变了建国之初的思想,开始谋划着迁都的问题,但不是迁到北京,而是迁到长安(今西安)。因为汉朝和唐朝的首都都在这儿,从历史角度上说正儿八经地经营中原,这里最合适。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时候,正好在西安就藩的秦王朱樉多次犯错,朱元璋急了,把他叫回了南京,臭骂了一顿,责令他反省一年。然后,朱元璋派出太子朱标去西安巡视,捎带着勘察一下迁都的准备工作。
没想到可能是水土不服,朱标从西安回来以后突然一病不起,在病中还上疏筹建新都的事,结果第二年直接暴毙了。这件事导致朱元璋一看见“西安”俩字就有心理阴影,迁都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朱标一死,朱元璋就得重新安排继承人。过去的家族传承是按分支走的,从朱标确立太子开始,基本上朱标的血脉就是属于“帝系”,除非帝系血脉断绝,否则不太可能考虑其他人。所以,朱元璋就把孙子朱允炆确立为了皇太孙,准备让他继承大统。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于南京,葬在了明孝陵,就在现在南京的紫金山风景区。朱允炆毫无争议地继承了帝位。
过去皇帝继承帝位,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先帝的遗诏,得先表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且,朱允炆并不是朱标的长子,他是二儿子,上面还有个大哥,只不过后来夭折了。结果在给朱标出殡的时候,朱允炆哭得撕心裂肺的。朱元璋一看这孩子真孝顺,再加上朱允炆熟读儒家经典,很符合朱元璋心中的“仁君”形象,就把朱允炆立为太孙。因此“仁孝”属于朱允炆的标签,别管是不是真的,起码得把牌子打出来,所以遗诏显得特别重要。
朱元璋的遗诏上有一条特别引人注意,就是“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翻译过来就是,藩王们在自己的地盘悼念一下就行了,用不着来一趟京城了。
这一点问题比较大,按理说当爹的去世,儿子奔丧属于正常礼节。所以,很多人从这里开始就觉得,朱允炆已经对叔叔们起了戒心了,否则不会这么不近人情。
这下也搞得朱棣非常郁闷,自己亲爹临终一面都见不到,只能在北平哭几声。结果还没等哭完呢,那边的建文帝朱允炆就开始削藩了。
贰
朱允炆放到今天来说,属于那种假装好孩子的文艺青年。朱元璋在的时候还比较老实,结果一当上皇帝直接开始放飞自我了。爷爷“洪武”,我“建文”,天天跟齐泰、黄子澄等一群书生在那里纸上谈兵,商量着把这个国家改为井田制,就是跟商朝的农业制度一个水平,非常富有理想主义色彩。
这时候,建文帝手下的一群儒生们就开始建议了,说:“咱们这么改制,很容易遭到反对,谁敢反对呀?大臣们肯定不敢,有这个胆子的都被太祖给带走了,只有皇上您的那些叔叔,仗着辈分比较高,敢教训您,所以我们开始‘削藩’吧。”
朱允炆一听,乐了,早就看这些叔叔们不顺眼了。《明史》载,朱允炆还是皇太孙的时候,就在当时明故宫的东角门边上跟黄子澄聊天,说: “诸王拥重兵,多不法,奈何?” 就是问他,这些叔叔一个个兵强马壮的,而且都不太守规矩,怎么办?黄子澄马上回答: “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 您叔叔那几个兵自我防卫还可以,真要是打起来,朝廷大军一到,全都完蛋。
这一听就是书生之见,打仗哪是单纯拼人数呀?但这俩人一个敢说一个敢信,朱允炆居然当真了。朱允炆继位之后,马上把黄子澄找了过来,开口就是“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您还记得咱俩当年在东角门时聊的雄心壮志吗?黄子澄马上跪下磕头,表示不敢忘。
其实“削藩”这个思路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要加强中央集权,“削藩”是必然的。中国几千年来都这么干,不然藩王很容易尾大不掉。但“削藩”不是平叛,藩镇的存在是合法的,人家藩王合法的权利被剥夺,后果会很严重。
因此我们看历朝历代,“削藩”都是一场持久战。比方说汉朝,历经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明君,才把这件事摆平,即使是这样也出现了“七国之乱”这样的局面。但朱允炆完全没想这么多,说干就干。
朱允炆当时的一个优势在于,排名比较靠前的藩王在洪武朝的最后几年都死的差不多了,其中老二秦王朱樉病死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晋王朱棡则病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比老爹朱元璋早了三个月不到。这样一来,燕王朱棣就成了建文帝最年长的皇叔,而且离得比较远。
这时候,朱允炆有两个“削藩”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擒贼先擒王”,这是齐泰的建议,挑最硬的骨头啃下来,直接削掉四叔燕王朱棣,这是年纪最长而且军功最大的一位藩王,摆平了他,其他人肯定没人敢反抗。但朱允炆想了一会儿,还是动摇了,决定按照另外一个思路,先从软柿子下手。
谁是软柿子呢?周王。周王朱橚和朱棣是一个娘生下来的,而且人就在凤阳,离得比较近。所以,朱允炆等人就教唆周王的二儿子朱有爋,告发周王谋反,并承诺封朱有爋为王。
这件事干得相当不地道。朱橚是个老实人,属于学者类型的王爷,热爱医学事业,他编纂的《救荒本草》,后来被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大量引用。这种人哪有精力造反,编书的时间都不够用的。但朱允炆不管这个,自导自演,直接把周王押回南京囚禁起来了。
有了第一个,下面就好办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建文帝连续举起“削藩”的大刀,代王朱桂、齐王朱榑、岷王朱楩、湘王朱柏先后落马。一年削掉五个叔叔的王位,成绩斐然。
其中,代王和齐王等人还好,只是被圈禁或者是被废为庶人。湘王就比较惨,估计是心理落差比较大,心想父皇在的时候我活得好好的,现在侄子对我动手动脚的,一气之下,直接自焚而死。
到了这份儿上,朱棣就是再傻也明白过来了,造反是很难造反,可也得做两手准备。何况这一年里建文帝没少敲打他,建文帝刚继位不久,就开始拿着隆福宫说事,说他僭越。
朱棣很愤怒,我都在这儿住了快二十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直接回信道: “谓臣府僭侈,过于各府,此皇考所赐……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 意思是,这地方是太祖爷给我的,我接手以后连块瓦都没敢加,当年《祖训录》里就讲了,跟其他王府不一样,不服你去查。
建文帝一看,不吱声了,他还没胆子跟朱元璋的遗训过不去,不过这不耽误他从别的地方下刀子。他扯了一个理由,说蒙古军队有可能要南下,把朱棣手底下的军队调到了开平。我们之前讲过,开平就是元朝的上都,在现在的内蒙古境内,当时离蒙古军队还远着呢。
朱棣自己就在抗击蒙古军队的一线,哪能不知道消息的真假,气得鼻子都歪了,但也没办法。之后,建文帝又把朱棣的得力手下观童,就是之前劝降乃儿不花的那位调走,派宋忠过来管理朱棣的军队。朝廷又在北平城安排了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为都指挥使,就在北平城内。当时北平城不算太大,所以基本上对朱棣开启了全天候的监视。
到这一步,朱棣头都大了,造反又打不过,老实待着又被朱允炆折腾,这种情况必须找个地方静静心,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
去哪儿呢?庆寿寺!
叁
庆寿寺始建于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位置就在现在北京的西单边上。对于明代初年的北平城来说是很有名的宝刹,距离朱棣所住的隆福宫也很近,走路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元朝大汗蒙哥在这里建了两座佛塔,所以又被称为“双塔寺”。这对佛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还保存着,直到1953年西长安街扩建才被拆除,这让建筑学家梁思成倍感痛心。
当然,朱棣去庆寿寺肯定不是为了看双塔,而是去找一个住在庆寿寺里的老和尚,和尚法号道衍,俗名姚广孝。
姚广孝是元末明初那个乱世特有的人物,他本人出身于医学和儒学世家。这种世家在元朝很多,都是被民族制度坑惨的人。之后,他在姑苏出家,法号道衍,拜的老师却是著名的道家名师席应真,也就是说他一个人贯通佛道儒三家。传说这老和尚双目三角眼,跟之前兴建元大都的那位刘秉忠一个相貌,属于“病虎”之相,主一生杀伐。
当年马皇后去世之后,朱元璋为了纪念她,就派了一批僧人,跟随儿子们去就藩,引导着儿子们信佛,为马皇后祈福。姚广孝的路子比较广,和当时的文人领袖宋濂、高启等人关系很好,再加上是难得的“通儒之僧”,就被派到燕王朱棣身边,和朱棣非常聊得来。很多人觉得姚广孝应该和朱棣是一代人,但实际上他只比朱元璋小七岁,算是朱棣的长辈,更像朱棣的老师。
一见面,朱棣就问姚广孝这事怎么办,总不能活活等死吧。结果姚广孝一开口,大不了咱们就造反呗。
朱棣一听,人都吓傻了,心说这到底是谁被“削藩”,怎么老和尚比我还急?其实很好理解,姚广孝那会儿都六十多岁了,佛道儒学了一辈子,再不找机会疯狂一把,满腹经纶就带到棺材里去了,所以力劝朱棣造反。
问题是当时朱棣手底下的军队都没多少了,就剩下一群护卫,加起来大概不到千把人,这要是造反,难度不比老爹朱元璋起家来得小。何况朱元璋还算是乱世出英雄,浑水摸鱼成功率比较高。现在大明已经建国三十多年,天下太平,中央政府的威信很高,你一个叔叔去和侄子抢位子,说破大天也不占理。所以,朱棣哆哆嗦嗦地问了一句: “民心向彼,奈何?”
造反这种事没什么回头箭,要么一飞冲天荣登九五,要么全家被诛九族。既然准备动手,甭管动机是什么,总得奔着成功的目标冲。但在古代,你想得天下,第一要素就是大义民心。比较典型的就是晋朝,连续三代弑君上位,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别人觉得你得国不正,你能上我也能上,那国家就完蛋了。
这个时候,老和尚很霸气地回答道: “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摆明了就是耍流氓,管民心干吗,咱造反属于替天行道,跟宋公明哥哥一个级别。
而为了给朱棣洗脑,姚广孝还劝说了自己的好朋友袁拱和金忠去辅佐燕王。这俩是干吗的呢?一个是相面的,一个是占卜的,主要的作用就是给朱棣洗脑。这下朱棣就开始坚定信心了,至少要做最坏的打算,不然就得跟湘王一样在隆福宫里自焚了。
既然确定了想法,那很多事就好办了,姚广孝当仁不让地接过了最重要的任务——练兵。
现在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会感慨这老和尚真的是造反专业户出身,构思太缜密了。《明史》记载,姚广孝 “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意思是,挖了地洞,盖上厚墙,埋下了大量的瓷缸,用来吸收声音,然后开始造兵器。就这还不算完,又养了一群鹅和鸭,扰乱练兵和打造兵器的声音。
这里也亏了是隆福宫,如果换成普通的王府,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些活动。隆福宫的面积大,这些全部在燕王家的后院就办妥了。就这样,在姚广孝的安排下,造反的物质条件就这么具备了。
但打造兵器、选拔将领、制订作战计划都需要时间。这时候,姚广孝又给朱棣出了个主意,让他装疯,以此来迷惑建文帝,反正天高皇帝远,他也没法当面确认,只要把北平这些盯梢的瞒过去就行。
所以,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开始装疯。他大夏天穿着皮袄在北平的大街上乱跑,又哭又笑,时不时地抱着个炉子喊冷。张昺和谢贵他们几个一看,六月天你不吃冰镇就算了,还吆喝冷,马上就信了,赶紧汇报给建文帝,说您四叔疯了。
但这种事情也就瞒一下外人,朱棣不可能天天穿着皮袄,回到家就脱下来了,要不然回头中暑就麻烦了。所以,当时燕王府的长史,也就是大管家葛诚,一看朱棣回去以后判若两人,就明白了,燕王是装的。他为什么装呢?肯定是想造反,就跟张昺和谢贵告了密。
建文帝一听,装的?马上告诉都指挥使张信,赶紧找机会把朱棣抓起来,南京也有“精神病院”,不差他这一个。
到这一步,造反已经是一触即发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