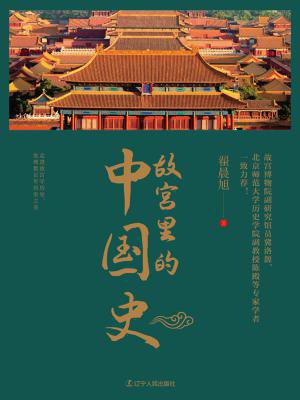从北平到南京
现在我们常常讲,历史往往是由无数个小人物构成的,而张信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最终让建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张信这厮看上去浓眉大眼的,居然反水了。
壹
如果按照建文帝的安排,张信应该找一切机会抓捕朱棣。结果这件事被张信的母亲知道了,就劝儿子说,我早就听说燕王要夺取天下,这种人是抓不得的。不知道老太太在哪儿听说的,真要有这样的流言,估计朱棣早就死十次了。张信就去找到朱棣,想把实际情况告诉他。
一开始朱棣压根儿不敢见,张信去了两次,连门都不让进。所以,张信急眼了,想了个办法,直接找了一辆妇人坐的小车,伪装成女眷,进入了燕王府的后苑,这才见到了朱棣。
刚一见面,朱棣还在装,跟中风一样,不说话。张信说您甭装了,我都知道了。朱棣马上回答: “疾,非妄也。” 意思是说,我真有病,不是假的。
张信一听,乐了,病人哪有自己承认有病的,这演技也太差了。他就告诉朱棣,你要是再装,我就按照命令直接动手了。
朱棣这才明白过来,这兄弟真是来帮忙的,马上叩首拜谢,说您这是救了我全家老小呀。然后,燕王朱棣马上联系姚广孝,养兵多日,用兵一时,马上召开动员大会,咱也替天行道一把。
结果这件事比较匆忙,没选好日子,那天风雨大作,直接把房顶上的瓦片都给掀起来了,落在地上。过去出征都得找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大风吹瓦,相当不吉利,会直接影响士气。朱棣自己也
 了,当场就变了脸色。
了,当场就变了脸色。
这时候,姚广孝站出来了,一开口就是: “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 这话简直绝了,意思是说这太吉利了。为什么有风雨?说明飞龙在天哪;瓦片为什么掉了?说明灰瓦不能用,得换黄的,什么人用黄瓦,皇上啊!一段疯狂解释,成功地把士气提上来了。
动员完了士兵,就该动手了。首先就是得控制北平城,这对朱棣来说太容易了,他在这里混了接近二十年,要是连个北平都稳不住,那干脆就别起兵了。
当时北平城还保存着元大都的建制,一共九座城门,朱棣只用了一晚上就取得了所有城门的控制权,捎带着杀了叛变的长史葛诚。这就正式打响了对抗建文帝的战争,号称“靖难”。
“靖难”是一个简称,全称是“奉天靖难”,跟姚广孝当时在庆寿寺里的话差不多。另外给出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说不是我侄子想除掉我,而是齐泰、黄子澄那些小人挑拨的。
而且,这话也不算瞎扯,因为朱元璋在《祖训录》里面写得很明白: “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 朱元璋的意思是,如果朝廷上奸邪当道,藩王可以组织军队讨伐奸邪之人,让皇帝身边干净一下。
问题是朱元璋说这话的时候没琢磨过来,到底怎么算奸恶?这样一来,等于给了藩王一个合法造反的理由,当然一般情况下没人用。但是,到了朱棣这里,起码证明了自己的合法性,这在造反的过程中非常重要。
这边建文帝一看四叔造反了,很高兴,因为在他的认知里,这种造反基本上等于送死,而且给了他一个“削藩”的理由。所以,他就派出了老将耿炳文,去镇压燕王的叛乱。
耿炳文是明朝当时硕果仅存的开国元勋,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跟徐达是一个等级的功臣。只可惜打仗这种事不看年纪,耿炳文一开始也没太把朱棣当回事,没想到朱棣敢主动出击,遭朱棣当头一棒,大败于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随后采取了守势。
建文帝一看,急了,这到底谁造反哪,你去平乱怎么还守着不动呢?果然老同志靠不住,没冲劲,就让耿炳文回来,换上了曹国公李景隆。李景隆在对付周王的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是“削藩”的一把好手,所以朱允炆可能觉得他行,就让他统兵镇压朱棣。
贰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景隆打朱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输的,双方兵力悬殊。当时李景隆手底下有差不多五十万大军,整个江北都归他节制。但是,朱棣戎马半生,对李景隆这种靠祖上功勋起家的货色太了解了,他对付一下手无寸铁的周王还行,真打起来基本上不行。所以,朱棣评价他为 “纨绮少年耳” ,花花公子,啥都不会干。
而且,朱棣也明白,造反这种事情,你要指望防守,那肯定是必死之局,所以他选择了主动出击。由姚广孝和王妃、世子坚守北平城,自己带兵穿插到敌人的后方。
那段时间,理论上是“靖难之役”中朱棣最艰难的时候,因为李景隆就算再草包,朱棣老巢就在北平,所以举兵攻打北平。
千钧一发之际,世子朱高炽,也就是朱棣的大儿子开始站出来了,说: “君父身冒艰险在外,此岂为子优逸时?且根本之地,敌人所必趋者,岂得不御备。” 我爹在外头拼命,现在哪里是当儿子的在这享福的时候,而且北平城是老窝,敌人也不傻,肯定过来,必须做好准备。
朱高炽是个大胖子,而且身体不太好,但他咬着牙, “每四鼓以起,二鼓乃息” ,二鼓相当于晚上9时到11时,四鼓差不多是现在凌晨不到3时,朱高炽每天晚上11点才睡,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巡逻,确实够拼命的。当时姚广孝是他的老师,这俩不愧是师徒,可能一碰上造反的事都比较亢奋。
燕王妃作为徐达的后代,也不是吃素的,不光帮助进行城防部署,甚至亲自上阵,带着城里的娘子军参加防守。后来,一直到好多年后她本人临终之际,都始终记得这些军嫂们,并嘱托儿子朱高炽多加抚恤。
但即使是这样,当时也打得非常困难。当时明军的大将瞿能,一度从彰义门登城。彰义门就是现在的广安门,在当时北平城的西边。眼瞅着城要破了,但李景隆给了机会,感觉早晚都能打上去,干吗把功劳给瞿能呢?所以,就让瞿能回来了。朱高炽一看,马上亡羊补牢,往城墙上浇水。那时候已经是北方的冬天了,第二天城墙上冻了一层冰,根本上不去,这才勉强守住。
北平城没打下来,朱棣就有了发挥的空间了,从后面包抄李景隆的大军。李景隆一看,害怕了,直接跑回了德州。当时南北交通主要靠大运河,所以德州属于战略要冲,等于李景隆直接把整个河北(当时叫“直隶”)给丢了。
这算是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第一个大胜仗。回去之后将士们给他庆功,说燕王用兵如神,朱棣都没好意思承认,说 “此适中尔,无所喜也” ,说这都是运气好,没什么好高兴的。朱棣自己也在后怕,万一北平真被端了,那基本上属于必死之局。所以,还是得感谢李景隆。
但是,就算打赢这一场,对于朱棣来说成功依然遥不可及,因为当时全国的大多数地方还是在建文帝的控制下。所以,之后的几年里,朱棣带着他的军队在中国北方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得非常惨。
当时济南是块硬骨头,李景隆在接连战败后逃到了济南。当时的山东参政铁铉和李景隆手下大将盛庸不信邪,就在济南城跟朱棣硬杠,硬生生地把朱棣挡在了北方。然后,朱棣一看打不下来,想走。盛庸等人趁机追杀,让朱棣大败于东昌,还折损了手下大将张玉。
这次失利让朱棣非常恍惚,一度打起了退堂鼓。关键时刻,还是姚广孝站了出来,鼓励朱棣重振旗鼓。第二年,朱棣在河北打败了盛庸。
叁
一场胜仗当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造反这种事风险很高,百胜不足定乾坤,一败足以失天下。
不过打到了这一步,姚广孝开始慢慢地琢磨过来了,就劝朱棣: “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就是说,别天天盯着济南那些城市了,你是“清君侧”,又不是“清济南”,在这儿耗着没用,直接冲南京,南京的兵都调出来放在江北了,直接杀进去这事就稳了。
姚广孝看明白了这场战争的实质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造反,这是叔叔打侄子,打来打去天下还是姓朱。建文帝说破大天也就是一个皇帝的名号,你冲进南京当了皇帝,那些军队就都是你的了。
朱棣一听,明白了。所以,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朱棣带着军队直接绕开济南和徐州,长驱直入,几个月就冲到了长江边上。而且越往南打越好打,像扬州和泗州,比较认可“朱元璋儿子”这个身份,直接投降了。
就这样,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二日,朱棣直接杀到了南京郊外,就是现在南京市的浦口,准备过江。到这一步,朱棣距离他大侄子朱允炆只有几十里路的距离,放到现在坐地铁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
到这一步,朱允炆慌了,就想割地求和,咱叔侄俩按长江一人一边。朱棣一听,生气了,可能是觉得侄子在侮辱他的智商,这缓兵之计也太低级了。直接放话说: “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为。” 我人都快死了,要地有什么用,干净利落地就过了江。水军一看人家叔侄两个相攻相杀,咱也别掺和了,果断投降。
到这一步,南京城已经算是近在咫尺了,但打南京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打个济南都这么费劲,何况当时的首都南京呢。这要是拖得久了,估计赶回来支援的军队能把朱棣生吞活剥了。
关键时刻,又是李景隆站了出来。他一琢磨,当时我带着五十万大军都没打过朱棣,现在更打不过,所以直接开了城门,卖给朱棣一个面子。就这样,几乎是兵不血刃的,朱棣就打进了南京。从渡江到进城,朱棣一共用了不到十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景隆帮助朱棣创造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奇迹。
进了城的朱棣第一反应就是找侄子算账,但可惜没见到。朱允炆一看四叔进城了,吓得点了把火,自焚而死。关于建文帝到底死没死这件事,历史上争议比较大,有传说他到了正统年间还活着。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新的时代来临了。
在假模假样地悼念了一番朱允炆以后,朱棣毫无争议地荣登九五,改元“永乐”。
肆
永乐帝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建文”这个年号取消。他宣布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着,朱棣的皇位到底来得正不正。
如果承认“建文”这个年号,就意味着明朝的帝系还是“朱元璋—朱标—朱允炆”,那么朱棣就相当于“外人”,是毫无争议的篡位。但是,现在一否认“建文”,帝系就变成了“朱元璋—朱棣”,纯粹父子之间的传承,所以简单的一个年号,背后所含的意义非常深远。
再接着就是要面对建文朝的老臣了,黄子澄、齐泰甚至铁铉这些人不用说,基本上就是诛九族,但有一个人,让朱棣感到很棘手。
这个人就是建文帝的近臣方孝孺。当初建文帝跟朱棣商量割地求和,主意就是方孝孺出的。他相当于建文帝的半个老师,天天给学生灌输心灵鸡汤,比如劝建文帝说北方士兵不擅长水仗,咱在长江上跟他们决战,结果没几天朱棣就过江了。
按理说,这种书呆子没有任何用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又属于“清君侧”的范畴,直接杀了就完事了。但是,早在北平还没出兵的时候,老和尚姚广孝就对朱棣再三叮嘱,千万不能杀方孝孺,这个人是文坛领袖,你打天下可以刀枪棍棒,治理天下还是得靠文人,因此留他一条命,便于收买人心。
方孝孺是宋濂的学生,宋濂编写了《元史》,方孝孺总编了《太祖实录》。在古代,能负责修这种正史的,绝对都是官方认证的文坛硕学加朝廷重臣。比如说,元代负责编史的脱脱帖木儿,就是当时的宰相,从治理黄河到镇压红巾军都有份儿,编史顶多算兼职。
既然姚广孝都开了口,再加上确实需要收买人心,于是朱棣就耐下性子,忍了方孝孺。不光没杀他,还让他继续当官,反正大明朝不差你这一口饭吃,也算是一段佳话。
结果,没想到方孝孺给台阶不要,犟劲儿上来了。朱棣让他上朝,他直接穿了一身丧服,哭哭啼啼地就过来了。朱棣的脸色很难看,但还是安慰他: “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就是您别伤心了,我这是学周公辅佐成王,帮我侄子一把。
谁知道方孝孺还是不罢休,就质问朱棣,你干吗不立你侄子的儿子当皇帝呀,你想干吗呀?问来问去把朱棣问急了,来了一句 “此朕家事” ,我们老朱家内部矛盾,你管不着。然后就让方孝孺起草继位诏书。
按理说到这一步,给个台阶你就下呗。没想到方孝孺把笔直接摔在地上,说: “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这诏书打死不写。
朱棣一看,火了,说那你就去死吧。直接下令把方孝孺车裂,就在当时的南京明故宫的午门外。现在南京市的午朝门公园正是明故宫的遗址,进门不远有一块“血迹石”,相传就是方孝孺的血迹溅在上面染的。
现在传的比较邪乎的是方孝孺被诛十族的故事,意思是朱棣一气之下,诛杀了方孝孺传统的九族以外还加上师生关系,凑了个整数。

方孝孺血迹石 现存于南京明故宫遗址,相传为方孝孺被车裂时的血迹染成。
其实,这件事属于传说,最早见于祝枝山所写的《野记》,原文很具有神话色彩,不怎么可信。因为《明史》里记载得很明白: “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 就是说,明朝中晚期以后被方孝孺牵连的人的后代还活着,只是方孝孺本人一家老小被灭了门。何况当时方孝孺是文坛领袖,弟子、门人很多,永乐帝要是真按师徒关系去诛杀,那大明朝估计会陷入动荡,所以这不可能。
现在方孝孺的墓就在南京雨花台。方孝孺在万历年间被平反,当时写《牡丹亭》的汤显祖正好在南京,就给他修建了坟墓,后来清朝的李鸿章也曾经帮助重修。
无论怎么说,方孝孺的反抗给了永乐帝当头一棒,让他意识到他所建立的政权并不是简单的叔侄互换。因为建文帝无论多么不堪,但在读书人眼里却很符合“仁君”的形象,这为永乐帝收拢人心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朱棣本来以为方孝孺的事件会是一个结束,但他没想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就在永乐帝登基没几天,一个叫作景清的人开始发难了。
建文初年景清在北平做过官,和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关系不错,后来回南京任职。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加封他为御史大夫。
结果就在一天早朝,景清穿了一身大红衣服,带着刀子就进了朝堂。忽悠朱棣说“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翻译过来就是天上有一颗星星变成了红色,冲撞了皇帝所对应的位置,这事比较急,能跟您聊聊吗?
那个时候的人都比较信这个,但这事应该归钦天监管,你一个御史大夫这么急干吗?何况那一天是早朝,不是大朝会,我们讲过明朝四品以上官员穿红色,那是正式朝会才这么穿,平时都是常服。所以,朱棣就怀疑了,觉得景清很反常,就让人搜他的身,结果把刀子搜出来了。朱棣一看,既惊且怒。
这时候,景清一看事情败露了,就开始骂朱棣,说我是为了建文帝报仇来的。朱棣怒火中烧,好心当成驴肝肺,我给你升官,你还为了我侄子要杀我,直接让人抽他。结果可能是当时朱棣离得比较近,景清一口血直接喷在了朱棣的龙袍上。朱棣大怒,直接把他车裂了。
方孝孺和景清,是当时比较突出的为建文帝死节的文人,但绝不是孤军作战。很多文人在朱棣进城的时候就直接自杀了,比如理学大师程颐的后代程本立,服毒自尽;再比如礼部右侍郎黄观更绝,全家都投水而死。
这些人在精神上给了朱棣很大的打击,因为他感觉和南方的这些文人没法沟通。这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从宋代开始就传承的文化世家,而朱棣在北平待了二十年,是一个豪爽的北方汉子。
所以,在南京的皇宫里待着,朱棣感到了精神上的孤立和政治思想上的格格不入,他必须打破这种僵局,为明朝的政治文化注入新的力量。
朱棣动了迁都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