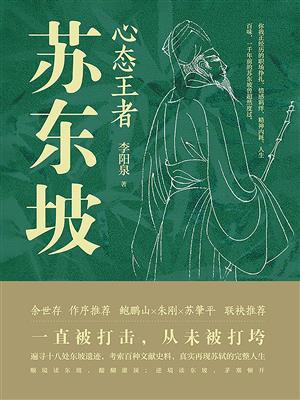凌虚台上“泄私愤”
苏轼在凤翔任上的工作顺风顺水,多半是因为太守宋选对他的赏识,宋选给了他很多施展的机会,再加上他确实也很用心,因此得了一个“苏贤良”的称号。可惜两年后,宋选被调任他处,新来的太守名叫陈希亮,为官三十多年,很有经验,而且人送外号“白脸青天”。这“白脸青天”是什么意思呢?青天,说明他公正;白脸,说明他不好接近。
的确,陈希亮的到来,是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挫折的开始。怎么讲呢?我们前面说过,苏轼写的文书,宋选一字不改,而且宋选给他出人头地的机会。到了陈太守这里,风格突变,苏轼很快就感到别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别扭之处来自文书的修改。苏轼的文书开始被圈圈点点了,而且不是小范围圈点,是大刀阔斧地修改。被删改掉的部分,往往是苏轼最得意的部分。陈太守说了,他只要求把话说清楚,不要有浮靡的词汇。那些文艺范儿、有风采的东西,他都不喜欢。这让苏轼有些不开心。
第二个别扭之处来自“苏贤良”的称号。有一天,在升堂的时候,有一个衙役见到苏轼,一口喊出了“苏贤良”,结果陈希亮听见后说:“把这小子给我拉下去,重责三十杖。这个人叫苏轼,不叫苏贤良,不可以在我的公堂之上如此叫嚣。”实际上,打的是谁呀?打的是苏轼。谁都看得出来。
第三个别扭之处来自中元夜的聚会。按照惯例,每年的中元节之夜,知府要把主要官员召集起来聚会,苏轼收到了陈希亮的请帖,却借故不去。陈希亮为此上表朝廷,罚了苏轼八斤铜,虽然不多,但是这个脸打得很疼。
苏轼心中暗想:“这个老陈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行,你最好别找我办事。”年轻气盛的苏轼把陈希亮对不起他的地方都记在心里了。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陈希亮在府衙官舍的后院修了个高台,并命名为凌虚台。这是宋代官员的习惯,在职期间修建一个建筑,以彰显自己的政绩,并为辖地留下个念想。台子建好后,陈希亮找到苏轼,说:“你文采出众,平常写公文埋没了你,这次你放开了写,我保证一字不改。”
苏轼满口答应下来,心说:“可让我逮着机会了。”很快,他写就了《凌虚台记》。这篇文章实在是够劲爆,堪比求雨时和山神“抬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
苏轼在表达什么呢?他说,站在凌虚台上可以看到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二宫,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二宫,以及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当年它们何等宏伟奇丽,又是何等坚固而不可动摇,应该比脚下的凌虚台坚固、宏伟百倍吧?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它们的样子,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能怎样呢?
新台落成本当祝贺,苏轼这样写堪称煞风景,纯粹是扫知府之兴。本以为陈希亮又会像以往那样对文章进行修改,谁知陈希亮看了文章后,哈哈大笑,说:“看来苏轼跟我真结梁子了。赶紧把这个年轻人请来,设宴款待。”
苏轼坐在陈希亮对面,心里有几分胆怯,但表面上还是故作镇定。陈希亮一改往日的严肃表情,语气也温和了许多。他对苏轼说:“子瞻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儿太难对付了,故意写这篇文章来气我,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和你可是有因缘的。我和你们苏家是世交,你夫人王弗是青神县人吧,我也是青神县人,你夫人论辈分应该喊我一声爷爷。你知道吗,你一举成名天下知,你身上的傲气呀,不敲打敲打你,我不放心哪……”
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苏轼一听,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当即提出想把这篇文章撤回来重写。
陈希亮说:“我说过一字不改的,来人,一字不许改,雕成碑。”《凌虚台记》就这样传世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苏轼在文中提到的那些宫殿都倒掉了,但是凌虚台从宋代起建立,中间经历几次修葺,如今仍屹立在东湖畔,见证着这段佳话。
陈希亮在苏轼的人生中或许不如欧阳修那么重要,但也算是较早打击他的一个人,这种打击其实是对他的一种关爱。后来,苏轼和陈希亮的儿子陈慥成了极为要好的朋友。苏轼被贬至黄州的时候,正是陈慥陪伴他度过了最孤寂的时光。
陈希亮去世以后,陈慥请苏轼写墓志铭。苏轼洋洋洒洒写了三千多字,此外还写了一首长诗,来表达怀念之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
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
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
我因为才华高,导致我情绪特别容易激动,只知道一门心思前行,不知道变通。如今,凌虚台修好了,站在这高台上,可以邀青山一起喝酒。青山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它应该知道陈公你的高风亮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