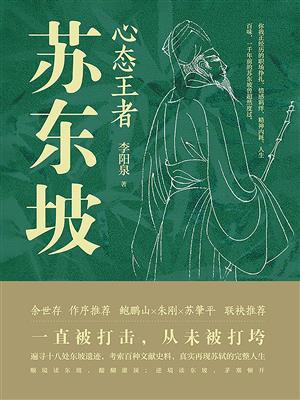第四章
拍案汴京
时间: 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七月
地点: 开封
苏轼结束了凤翔的任期回到京城开封,父子三人再次相聚,其乐融融。苏轼被任命为殿中丞,兼任直史馆,这位文艺天才得以借此机会饱览宫廷藏书和书画。
几个月后,苏轼的爱妻王弗因病去世。
时隔不到一年,苏洵病故。
兄弟二人护送父亲和王弗的灵柩回眉山,为父丁忧守制三年。期间,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
他们再次回到京城,已经是熙宁二年(1069)了。新上任的神宗皇帝励精图治,希望让积弱的北宋迅速强大起来。于是,他起用了王安石,实行新法。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在实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由于改革力度太大,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一时间,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都站到了反对变法的队伍中,苏轼于情于理地加入了同一阵营,他上书皇帝,痛陈变法的诸多弊端。然而,一心想要强国的神宗早就和王安石“肝胆相照”了,改革之路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
倏忽匆匆过半生
苏轼在凤翔任上的任期已满,回到了汴京。父子三人终于又可以朝夕相处了。
这时朝廷的任命也下来了,苏轼任殿中丞,同时兼任登闻鼓院判官。“登闻鼓”三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群众申诉,确实如此。苏轼对这个官儿实际是不太喜欢的,采取了消极对待的态度。恰在此时,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位君王——宋英宗。
英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他对宰相韩琦说:“把这个大才人调到翰林院吧,让他做知制诰,给朕起草诏书。”韩琦说:“圣上啊,那可不行,大宋开国以来,列祖列宗选择官员都必须经过特殊的考试,您这样直接提拔他,是不符合祖制的。”英宗点了点头说:“那要不然让他当个起居注吧,记载一下我朝日常,总可以吧?”老韩琦说:“圣上,依臣看,这也不行。先帝在位四十多年,对于内廷官员的考核和提拔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您看看苏轼,虽然他有才,但资历浅,是不是?您得考试!”英宗不高兴了,说:“我们过去用考试来提拔人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人,我了解的人,为什么还要考试啊?”韩琦胡子一翘,脸一拉说:“皇上,您可不能让微臣为难啊。仁宗皇帝在的时候,常常告诫我们,祖宗先例不可轻废。如今您做这样的决定,老臣恕难从命。”韩琦眼看拗不过皇帝,就搬出太上皇来。这样一来,英宗很扫兴,就不再聊这个事儿了。
欧阳修得知此事,专门把苏轼找来谈心。“小苏啊,老韩这人我了解,他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是针对你,你可别往心里去啊。”苏轼说:“恩师大人您放心,韩相的脾气我早有耳闻,坚持原则是值得敬仰的,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再说了,这么多年,学生我也没怕过考试啊。”他这样一说,倒把欧阳修逗笑了。
不久,朝廷真的安排了一次考试,苏轼毫无悬念地通过了。考过之后,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直史馆。负责什么呢?其实就是修史的文官,虽然官阶不高,但是非常重要。他的老师欧阳修也曾经做过这个官,后来编修了《新唐书》。直史馆的工作内容,更多的是阅读内府藏书,品鉴著录内府书画,这样的工作对一个文人而言,实在是莫大的幸福。
然而,造化弄人。苏轼在直史馆任上仅仅待了几个月后,他的爱妻王弗一病不起,任凭百般医治,病情也毫无起色,不几日竟撒手西去。这个打击对于苏轼而言,实在是有些沉重。他不敢相信,如此年轻而贤淑的妻子怎么说走就走了呢?那段时间,他常常搂着爱子苏迈呆呆地坐着,巨大的悲伤和孤独感涌上心头。
祸不单行,时隔不到一年,他敬爱的父亲苏洵也因病离世,年仅五十七岁。他和苏辙陷入了更大的悲伤中。
苏轼请欧阳修为父亲写了墓志铭,请司马光为母亲程夫人写了墓志铭。兄弟二人护送着父亲和王弗的灵柩,回乡为父丁忧。
丁忧制度对于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人而言,或许显得有些残酷。因为三年后再回到朝堂,不知会有多少变数。然而,这项关乎孝道的制度在北宋时期已经突破了民俗,发展到了法规的程度。官员如果不为父母丁忧守制,则可能被免官甚至坐牢。苏轼兄弟为父母丁忧,还得到了英宗皇帝特别的照顾,由朝廷安排船只护送他们回到四川老家。皇恩浩荡,给兄弟二人悲伤的内心带去了不少温暖。
他们回到了人生的起点——眉山,那里的山山水水是那么美好,父老乡亲是那么熟悉。此时的苏轼兄弟早已不是数年前进京赶考的少年,他们都取得了功名,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因此,远近来访者络绎不绝。
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丁忧结束。苏轼续弦。他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这是王弗在弥留之际的安排。数月后,兄弟二人携家眷再次启程。故乡虽好,前程却在汴京。
苏轼兄弟不会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亲近故乡的山水。
他们回到开封之后,发现天变了。
就在他们为父丁忧的第二年,也就是1067年,宋英宗赵曙因病去世,其长子赵顼继承大统,宋神宗时代开始了。年仅十九岁的宋神宗,不甘心自己的大宋王朝如此积贫积弱,非常希望通过他这一朝的努力让国力回到开国时期的兴盛局面。他也深刻认识到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于是,他想到了变法。
满腔热血且经过多年基层历练的王安石和神宗有着同样的梦想。他给皇帝上书万言,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改革的想法和决心,深得宋神宗的认同。于是,宋神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王安石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很快,募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多项改革法规应运而生。
改革自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招来不同的声音。每当有保守派批评王安石时,他便亮出三面挡箭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王安石铁了心地要把新法推行下去,而皇帝是他的支持者。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久而久之,执拗的王安石得了个外号——拗相公。
苏轼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争论,他在神宗面前痛陈变法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试图让皇帝回心转意。然而,神宗皇帝太需要这场改革来证明自己了,他选择信任王安石,而且信任到底。
很快,苏轼遭到了改革派的攻击,进而转入白热化的程度。无法忍受的苏轼向皇帝提出发外任的请求,于是在熙宁四年,苏轼踏上了去杭州赴任通判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