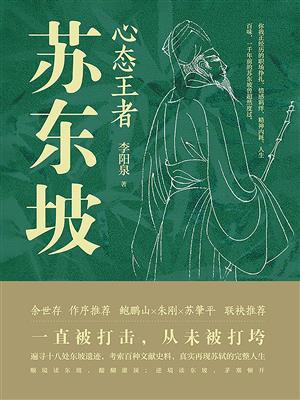反对王安石变法的N个正当理由
熙宁二年到四年(1069—1071),苏轼先后多次给宋神宗上书谏言,矛头直指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
苏轼并非不主张改革,只是他看到的更多的是变法的反面。熙宁四年,苏轼写了《上神宗皇帝书》,理性批判了王安石施行的新法。在这次上书中,他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其一,结人心;其二,厚风俗;其三,存纪纲。
在对“结人心”的论述中,苏轼拿商鞅变法来举例子,说“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在苏轼看来,商鞅变法失了人心。而之所以失了人心,是因为变法的初衷会伤害很多人的利益。
谈到“厚风俗”,苏轼说“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在他看来,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礼崩乐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好的道德基础,没有上行下效的良好风俗,即便是富有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谈到“存纪纲”,苏轼则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在他看来,当时已经出现了冗官冗兵的社会现实,很多岗位被无能无用的人占据着,真正有才、能实干的人却得不到重用。
苏轼直陈王安石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不能不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他提的诸多意见也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甚至有远见的,尽管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情绪化的东西。
另外,苏轼的恩师欧阳修以及苏轼非常尊重的司马光都反对变法,这是他不得不站的队。
对于苏轼真诚直谏,宋神宗颇为欣赏,对他的进言表示首肯和鼓励。而面对变法的推行,宋神宗也不得不做出抉择。事实上,苏轼三番五次的谏言根本没有改变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定,变法依然沿着既定的方针在推行。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苏轼明知宋神宗变法的决心和毅力,但是他依然上书提示改革措施的弊端,这也足以看出他的执着。
我们用尽可能简单的逻辑来梳理一下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苏轼有足够的理由不赞同新法,上书神宗却没有任何效果,而他作为新法反对者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于是,他很自然地受到了新党骨干的排挤,他被挤出了权力中心汴京,接连被下发外任到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不甘心的苏轼在此期间写了为数不少的描述百姓苦难的诗文,当然,这其中也的确有直指新法弊端的讽刺性文字。这些文字被新党骨干李定等人收集起来,进行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曲解,就变成了苏轼处心积虑讽刺新法、讽刺皇帝的“罪证”。神宗皇帝也由于和苏轼分开多年,无法准确判断苏轼是否真的出格了,于是就点头同意把苏轼调回汴京问话。拿到了皇帝的尚方宝剑,李定等人故意制造恐怖气氛,下定决心要把苏轼置于死地。这才有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所幸的是,北宋有不杀文臣的祖训,且神宗是个比较英明开放的君主,他支持新政,但也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和忠心,在曹太后以及众多重臣的求情下,做出了对苏轼从轻发落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的求情者中,就有苏轼的“老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说到底是君子之争,否则他们也不会有后来的相见与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