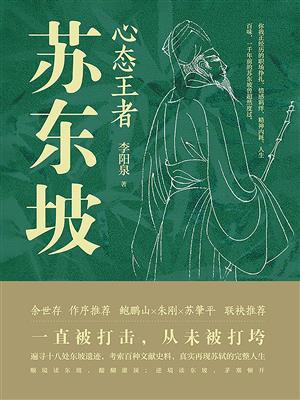第五章
初遇杭州
时间: 宋神宗熙宁四年七月至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
地点: 阜阳、杭州、苏州
杭州在北宋是仅次于都城开封的城市。苏轼能被委以杭州通判的官职,还是得到了神宗的特殊照顾。
远离了政治旋涡的苏轼,尽情享受着杭州美景。这里让才华横溢的苏轼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然而他很快厌倦了官场上的应酬。觥筹交错之下,是他孤寂的心灵。
公务之余写诗、会友、观潮、赏花、郊游……苏轼的日子不亦乐乎。杭州治下的富阳,一派好山水,他入山访僧、荡舟江上,写出了“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周边的城市也经常可以寻到他的足迹:他在宜兴看地,在宿州看灵璧石,去无锡饮二泉水,去湖州饮酒于溪上……
三年时光转瞬即逝,而此时朝堂之上依旧乌烟瘴气,他选择继续外任。为了离知济南的弟弟苏辙近一些,他向皇帝上书请求知山东密州,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想起恩师,就来一碗“六一泉”
熙宁四年九月,苏轼因反对变法而被外派到杭州任通判,在上任的途中特意取道颍州(今安徽阜阳),拜访同样是不满变法而退隐的恩师欧阳修,与其共度了数日欢乐的时光。此时欧阳修已改号为“六一居士”,并作有《六一居士传》,其中说道——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在愉快的相处中,欧阳修向苏轼郑重地介绍了他的朋友惠勤法师,说这位惠勤法师文采出众,并嘱咐苏轼代自己去问候他。
恩师所托,岂敢怠慢?熙宁四年的腊月初一,苏轼来到杭州的第三天,就去孤山拜访了惠勤法师。
按照惯例,腊月初一这天是要在家里陪家人的,而苏轼却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中说“名寻道人实自娱”。这个天性烂漫的人,就是这样真实而洒脱。在苏轼笔下,孤山是静谧的、雅致的。寻僧访道,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清净。“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他巧妙借助孤山的“孤”字,表达出对修行之人的羡慕和向往。辗转来到僧房,苏轼报上老师欧阳修和自己的名号,两位高僧岂能不知苏轼?他们初次相见,品茗谈诗直到深夜,仿佛多年的老友。
第二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走完了他的一生,在颍州西湖之滨的私宅溘然西去。消息传来,苏轼悲伤不已。他再次来到孤山,和两位僧人一起祭拜欧阳修。惠思写了一首悼亡诗,东坡和之,其中有句“犹喜孤山下,相逢说旧游”。
为什么恩师走了,苏轼会在诗里写到“喜”呢?这就是苏轼的心态。他读过《庄子》,庄子的妻子去世以后,庄子鼓盆而歌,这是对有修为之人的一种最好的追念。苏轼用这个“喜”字用得非常妙,是他内心深处对恩师的一种赞美、一份无与伦比的敬意。
东坡再次出任钱塘太守,已经是十八年之后的元祐五年(1090)。顺着原路,苏轼再访惠勤的僧舍。此时,惠勤却去世已久。堂上挂着欧阳公和惠勤的画像,栩栩如生。他的弟子告诉东坡,师父旧舍中原来是没有泉眼的,他来之前几个月,孤山脚下,讲堂之后,甘甜的泉水突然涌了出来。他们就在此地开凿岩壁,垒起石头,造了一间房子。他们认为这奇异泉水是其师之灵闻东坡来,特意“出泉以相劳苦”。于是,弟子就请苏东坡为泉取名。
苏东坡想起当年与惠勤的交往,又念及自己恩师欧阳修,遂将此泉命名为“六一泉”。
从此以后,这孤山上的六一泉就因苏轼与欧阳修的这段故事以及苏轼的《六一泉铭并序》而闻名于天下了。世人常说文人相轻,然而苏轼与欧阳修的这朵友谊之花,却是如此璀璨夺目,香飘万世。
百年之后,南宋偏安杭州。“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杭州热闹非凡。然而,愤怒的诗人总不会缺席。诗人杨万里登场,他以年迈之躯来到六一泉,汲泉水烹茶,遥想欧阳修、苏轼、惠勤、惠思和黄庭坚,老泪纵横。他说:“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一个伟大时代的远去,留给诗人更多的是遗憾与孤独,于是杨万里“自看风炉自煮尝”。还有什么纪念比这样的自斟自饮更让人感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