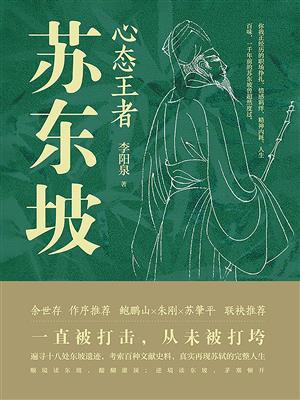爱煎茶的监考官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写了一组诗,名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其五是这样写的:
未成小隐聊中隐,
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
故乡无此好湖山。
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大意是:目前在我所待的这个地方,我有一些无奈,但是这种无奈和上天赐给我的这美好的风光相抵消了。我认为我可以忍受眼下的这一切,我可以在这种苟且的生活中得以喘息,得以与山河大地同在。
之后一个多月,便是秋闱考试了。
大家都知道,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对科举制度变法的,并曾写文章在四个层面反驳,意见得到了神宗的赞赏,却最终没有被采纳。科举新法还是在熙宁四年二月公布实施,从此废除了明经诸科,取消了进士的诗赋考试,只考《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顾《论语》和《孟子》。
苏轼认为,以前考生在考试前无不遍读五经,由于自小就学,且经常温习,所以终生难忘。而今,只能选择一部经典来读,其他的就自然会被忽略,这样的考试如何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呢?
尽管有这么多不满,作为乡试的主考官,他又不得不去监考。无奈之下,苏轼选择了苦中作乐,他在望湖楼上看潮起潮落,而且写了《试院煎茶》。
这诗的题目就有点儿斗气,试院明明应该监考,他非要写在试院煎茶,很明显就是不合作的态度。
这首诗开篇就提到了“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
什么是蟹眼?什么又是鱼眼呢?这都是与煮茶有关的专业术语,早在唐代就已经流行开来。
明代陈鉴在《虎丘茶经注补》中有明确解释:“汤之候,初曰虾眼,次曰蟹眼,次曰鱼眼。若松风鸣,渐至无声。”
虾眼,指煮茶初沸时所泛起的小气泡。煮水时,如直视水底,可以看到底面泛起相当小的气泡,似虾的眼睛。虾眼阶段水温跨度大,为50℃~90℃。
蟹眼,指在水沸之前,水中开始出现连续上升且更大的气泡,状似螃蟹的眼睛,小而细,团而圆。此阶段时间短,温差小,为90℃~92℃。
鱼眼在茶圣陆羽的《茶经》中也被称为一沸,“其沸,如鱼目,微有声”。鱼眼阶段,水面开始出现细小如鱼目的气泡,还会发出一些细微的声音,温度为92℃~96℃。
鱼眼阶段,有时会伴随一些声音,这细微的声音有一个颇具风情的名字——“松声”。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写道:“水一入铫,便需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原本平凡的煮水步骤,因古人的想象而倍添雅趣。
接下来的松风鸣就更美了。“松”和“风”这两个词产生关联,是中国意象当中绝美的存在。为什么不是蕉风?芭蕉是挡风的,风吹到芭蕉叶子那里就不动了。为什么不是竹风?竹子间是停不住风的。我们可以适度展开一下,有一副流传很广的文人对联——“竹露松风蕉雨,茶烟琴韵书声。”每一个意象都有对应的载体,变换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每一种东西都会有最适合其性格的美的表达。而松和风的结合就是这么完美,松既能过风,也能停住一部分风,而且松很坚韧,它可以一直和风同在。松风的美,大家可以想象,是伴随整个煮茶过程的一种细小的声音,而这种细小的声音非对生活有大爱者不能体会。
若干年后,苏轼被贬至海南儋州,写出了另一首煎茶诗——《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
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
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
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
坐听荒城长短更。
松风又一次出现,但这次听到的不是渐渐变小的松风声,而是如同倾泻一般。为什么?因为儋州太安静了,无边的寂寞之中,一点点声音在诗人的世界里都格外清晰。
苏轼的学生黄庭坚尤其喜欢松风的意象,在这两位顶级文豪的推动下,“松风”几乎成了饮茶的代名词。
没有松风,宋代的茶道将失去一半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