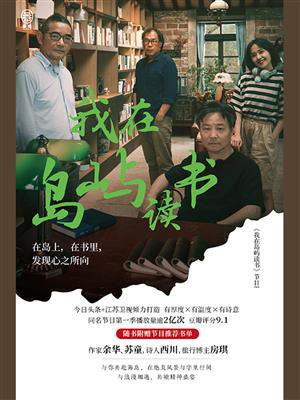良师

益友
苏童说:“《收获》杂志的主编程永新老师,是我跟余华创作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伯乐。我从1985年开始在《收获》发表作品。余华,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发表的?”
余华说:“我是1987年开始发表的。你1985年就在《收获》发了?”
苏童笑着“炫耀”道:“不知道了吧,我是1985年发表的。”
“发表的是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程永新说道。

“当年我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跟程永新说,我一年发六个短篇,一期一个。程永新说,《收获》没有这样的规矩呀。我说,创建一个规矩不就行了嘛。他又去跟李小林
 商量,是不是一期发三个,然后分两期发。是吧,你还记得吗?”余华笑着对苏童打趣道,“那待遇比你高多了。”
商量,是不是一期发三个,然后分两期发。是吧,你还记得吗?”余华笑着对苏童打趣道,“那待遇比你高多了。”
众人大笑起来。
苏童笑对余华道:“问题是你没有发六篇啊!还是我开创了先例啊——一期发两个短篇
 嘛。”
嘛。”
余华表示“不服”:“确实是在你后面发表的。但是,我当时如果不把《许三观卖血记》写成长篇的话,就能在《收获》一年发六个短篇,那肯定更有开创性了,是吧?哈……”
西川评余华道:“你简直就是个‘获霸’”。
余华回忆道:“1995年,《收获》第1期发了我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第2期发了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程永新也看过,还跟我说写得不错。到了第3期就该是《许三观卖血记》了。结果到了第3期发稿的时候,程永新打电话问:‘要发稿了,写得怎么样了?’我说,这个由短篇改成中篇小说了。程永新说,好好好,中篇小说好。后来,到《收获》第4期要发稿时,他又来问我:‘余华,写得怎么样了?’我说,中篇又变长篇了。他说,哦,长篇好长篇好。后来,《许三观卖血记》是在《收获》第6期刊发的。《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样出来的。”
苏童点头说:“对,我跟余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
程永新回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初,我们北京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肖元敏两篇余华的作品,一篇是《四月三日事件》,另外一篇是《一九八六年》。我一看,确实很震惊。《四月三日事件》整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年轻人,他预感到要发生一个事件——四月三日事件。但这个事件是虚幻的,并不存在,它有一种哲学上的意义在里面,跟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太一样。苏童是我的大学同学黄小初推荐的。当初黄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他就很欣赏苏童,就推荐了苏童的一个短篇,叫《青石与河流》。我看了《青石与河流》,几乎没改一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都没改过。你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年轻作家写的。于是,我就约稿。苏童就写了一个《1934年的逃亡》。我们那期出来以后,文坛就整个炸了,大家都去读这一期的《收获》,觉得很奇怪,怎么来了这样一群陌生的年轻人,写法跟前面的作家完全不同,各有特点。我希望能够找不同风格的人——余华的风格的、苏童的风格的,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作家的。于是,全国就有一种轰动的效应。”

房琪拿出两本《活着》,一本是黑色封面,另一本是白底淡色山水封面,问道:“我刚才在书屋里拿了几本书,像余华老师的《活着》,有两个版本,内容一样,序言也一样,但装帧封面都有改变,这是怎么回事?”
余华指着书本答道:“这是两个出版公司出版的。黑色的这本,作家出版社不再印了。另外一本,是新经典的版本。”
房琪又问:“像这种不同版本的书,编辑在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程永新指着余华道:“余华的书不是畅销书,他是常销书作家,因为他一直在出,需要一些新的面貌。”
“我们这个年纪的读者可能对于作家认知得多一点,但对于编辑的认知就弱一点,不太知道编辑们具体会负责哪些工作。”房琪追问道。

“编辑最重要的工作是欣赏。作家写出好东西,要有一双眼睛去欣赏它。这个,最重要。”程永新详细介绍说,“编辑流程先是登记,给作品编号——几月几号到的,登记地址和通讯方式。而后,将作品分到每个编辑手中。一个编辑初审,初审完后给二审编辑,两个人看完后,最后才由主编来定,这是终审。终审后,才能签字发稿。然后,我们才会通知作者。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编辑,每一篇作品都要简洁写出审稿意见,如果初审跟二审的意见比较一致,就会让作者去修改。当然,编辑会跟作者沟通,看作者认可不认可修改意见,这是编辑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编辑是作家和作品的一面镜子,所提的修改意见是在深度理解作品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对头的修改可能就会改出一个好作品。但作家也有不修改的,他有不修改的道理,那我们第一还是尊重作家;第二呢,我们也会去倾听读者的意见,这个对于我们编稿子以及稿件的规划安排也是会有影响的。”
在程永新娓娓道来中,书屋内一时间变得安静下来,回忆与现实交织着,似乎也在此刻被编辑成一部作品,定格在时光的纸面上。
程永新又笑着指了指余华:“那像余华,他也曾疑惑当年《一九八六年》为什么不先发出来。其实我是有点私心的,他那篇较长,我想等一下再发,那时候希望阵容大一点,作者多一点。那个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作者冒出来,诗人其实也是这样子,西川老师肯定最有发言权,所以当时就是想把这一批人搞在一块儿,集中发表一下。”
房琪说:“所以编辑跟作家其实也是互相成就的。”
“当然。”程永新说道。
余华说:“我们那个时代啊,好编辑多,比如说像《人民文学》有崔道怡,年轻的有朱伟,还有向前。张承志就是向前发现的。可能是一个什么会上,张承志就讲了当年在内蒙古的一个故事。向前就追着他,要他把故事写出来。张承志说‘我不会写小说’,向前告诉他‘你把故事写出来就行了’。结果,那篇就拿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
。”
苏童、程永新、西川都点头称是。
“编辑多认真啊!”余华说道,“我们遇到了一群很好的编辑。像我在《北京文学》最早的编辑是王洁,她就是从自由来稿里面发现我的。那时候我在一个小镇上工作,也不会认识什么编辑。当年的编辑都坐在办公桌旁,认真看自由来稿的,他们是想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新的作家,以发现新作家为荣,一旦他们看到一篇好的小说,整个编辑部传阅。当所有的编辑一致认为这个小说写得好的情况下,这个作者就会受到整个杂志社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现在我知道,《收获》还保留着这个传统。”
苏童深有感慨地说:“编辑与作家的关系,亦师亦友——这个作家很年轻,有前途,编辑看出了他的才华,同时也看出了他的问题。所以,当编辑想要抹掉这个宝石之上的灰尘时,必然会指出问题所在,告诉他灰尘在什么地方。 抹去宝石上的灰尘,这就是编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