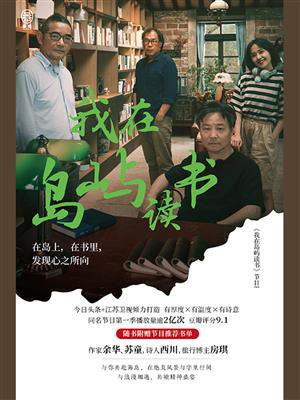摇篮

殿堂
程永新这次过来,还带来了1957年《收获》创刊号的合订本,红底白字,朴素、厚重,大家连呼“珍贵”。
程永新介绍道:“1957年,巴金先生跟靳以先生创办了《收获》杂志,这是中国第一本大型的文学双月刊,它发表的主要是原创作品,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一直到新时期,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在这里诞生了几代作家。《收获》是作家的摇篮。”

翻开《收获》创刊号,第一篇便是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
。
程永新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是我们大学里面的必读篇目,这个非常牛。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的历史进行了一次梳理,读它,你就知道了中国当代小说跟历史、传统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因为鲁迅先生非常深刻,这篇文章也就梳理得非常清晰。”

随着纸张的翻动,众人在杂志上看到了老舍的《茶馆》,看到了康濯的《水滴石穿》,看到了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
苏童指点着说道:“《水滴石穿》,当代文学史上也讲过的。严文井的儿童文学也有传统哦,《收获》创刊号就有个童话。”
在《收获》第2期上,大家看到了李劼人的《大波》。在《收获》第3期上,赵树理、巴金、靳以赫然在列,引得大家一阵品评。
程永新指着封面上“收获”两个宋体字道:“那个时候还是美术字。”
西川说:“我喜欢这个字体,50年代那个字体好看。”
“后来封面上‘收获’两个字,用了鲁迅的书法。”程永新介绍说,“字是从鲁迅的文章手稿里挑出来的。”
西川说:“集字。”
程永新说:“对。”
余华说道:“因为巴老,《收获》一创刊就是中国最牛的杂志,没办法。”
程永新:“对呀。创刊号上老舍的《茶馆》非常重要,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话剧剧本里面经久不衰、经常上演的这么一个剧本。老舍先生既是小说家也是剧作家,他写‘京味’小说,就是北京味道,带着特别浓烈的地域文化。《茶馆》就是描写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然后通过一个小茶馆的变化来展现大时代的变迁。它的艺术特点就是京味儿,喝茶的习惯、对话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在这个茶馆里面表现得非常生动。《茶馆》已经成为当代经典。”
余华说道:“1987年我们那个专号,还有张献的一个剧本。”
“《屋里的猫头鹰》
 。”程永新答道。
。”程永新答道。
苏童说:“剧本在《收获》一直发到80年代。”
程永新说:“对的。”
西川指着《收获》杂志上的作者手写体署名:“你们说的把作者的名字剪下来就是这个意思?”
程永新:“剪取作者手写签名刊印发表,是《收获》的一个传统。”
苏童说道:“手写体,从创刊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程永新道:“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就是稿子的签名。因为作者署名剪下来了嘛,所以它第一页上面总是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洞。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只有纸质稿,作者只能寄过来,寄过来之后,我们把署名抠下来,贴到稿子上。印刷的时候,就会把作者的签名印到杂志上。它有一种趣味性在里面,因为文学是人学,从办刊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杂志呈现一种生动性,带着人文气息。”
余华说:“我第一次看到《收获》是上初中时,读了一部长篇小说——《大学春秋》
 ,这是我读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是我读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兴之所至,程永新干脆从书架上抱来一摞《收获》杂志:“这是你们来之前我在书屋发现的,这里有不少。有苏童的、余华的……”

“这是张洁的《方舟》
 ,我一下就找到了。”苏童举起旧杂志,兴奋地指着目录说道,“这个孙芸夫就是孙犁,那时候他老夫聊发少年狂,突然要把自己叫‘芸夫’。《芸斋小说》
,我一下就找到了。”苏童举起旧杂志,兴奋地指着目录说道,“这个孙芸夫就是孙犁,那时候他老夫聊发少年狂,突然要把自己叫‘芸夫’。《芸斋小说》
 ,估计是孙犁最后一批作品。”
,估计是孙犁最后一批作品。”
“这是那个马原的《虚构》
 ,发在1986年。”余华突然眼睛一亮,对苏童道,“《青石与河流》,1986年。刚才还说1985年发的,你虚构的,都往前提了一年。”
,发在1986年。”余华突然眼睛一亮,对苏童道,“《青石与河流》,1986年。刚才还说1985年发的,你虚构的,都往前提了一年。”
众人一阵大笑。接着,苏童翻到了铁凝的《麦秸垛》
 ,不由得感叹:“这么早!”紧接着,他又翻到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不由得感叹:“这么早!”紧接着,他又翻到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说道,“《活动变人形》是王蒙那个时代最好的一部长篇,我也认为是他至今最好的一部长篇。”
,说道,“《活动变人形》是王蒙那个时代最好的一部长篇,我也认为是他至今最好的一部长篇。”
余华找到了自己的作品:“你看我的《一九八六年》,是发在《收获》三十周年纪念号的,这是1987年的。”
苏童说:“不光我自己,还有朋友们,比如马原、余华、格非、叶兆言等这些文坛好友,《收获》也是他们的阵地。我从《收获》上也可以读到他们最近在干什么、写了什么,比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我个人很幸运,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因为在《收获》上发表,我的同行们或者我想象当中的心仪的那些读者,他们会看到这些作品,所以他们也帮忙完成了、塑造了我这个作家的角色。这是《收获》对于我的意义。”
“还有路遥。”程永新谈到,“我们《收获》发过他一部比较重要的小说《人生》。当初我在《收获》还看过他的手稿,钢笔字,方格纸,誊抄的字迹特别清楚,没有一个修改的符号,这种稿子看上去赏心悦目。路遥是很苦的,他就是一个文学的苦行僧,用真情感来写作。他是燃烧自己的生命,来化成他小说当中的文字。”
苏童接着程永新的话题:“那时候是手写时代,如果一页稿子出现五个以上的改动,我必须把它撕掉,再重新抄一遍。后来大家都说,他们很喜欢苏童,因为稿子太干净了,他们容易看进去。这是我很聪明的地方。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本人是编辑,我看到写得很清秀的字,哪怕内容差一点,我也觉得可以看下去。可看到写得不好又字迹潦草的作品,就会有种说不清楚的抵触,总不能用狂草来写小说吧,对不对?”



西川好奇地问程永新道:“发表了以后,手稿还要还给作者吗?”
“还啊,《收获》是唯一一个归还作者手稿的杂志。”苏童说。
余华强调:“《收获》是唯一一个还手稿的。”
程永新说:“这是老巴金留下的这个传统。”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留存下来的手稿都是《收获》的,都是收获的发排稿。”苏童对西川道。
余华突然想到一件趣事:“有一次,你们有个编务寄错了,把曹禺的手稿寄到我这儿来了。”
众人大笑。西川语气里带着惊奇:“你留下来了吗?”
余华说:“没有,我给他退回去了,寄错了嘛。那一期好像也有我一个小说,我一看还有曹禺的。”
“《收获》编稿子遵循的所有细节,其实都跟老巴金他们有一种传承关系。当初我还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手稿还给作家。现在看,我们退掉的稿子对研究这个作家提供了实质性的资料,既是对作者的尊重,也是一种交流。我们在上面改了什么,他都看到了。《收获》能有今天这样一种地位,跟这些细节都是有关系的。”程永新颇有感触地说道。
余华道:“我印象中很深是1987年,就是我在《收获》发第一个中篇小说那年。《四月三日事件》发表前,我去了《收获》编辑部。那天下着小雨,我到了上海巨鹿路675号的那个院子里边,一切都那么朴素。顺着环形的楼梯走上去,看到有一个门上贴了一张《收获》杂志早期的封面。我想,这肯定就是编辑部了。然后敲门进去。果然就是。”
“几乎每一个中国作家在《收获》上发表作品,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脚印,这一步是一定要迈出去的。投稿时,你的信封上会写下‘巨鹿路675号《收获》杂志社’,这么一个地址,每个人都很熟悉这个地址,因为《收获》在那儿。在中国所有文学人口中,它就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殿堂。”苏童动情地说。
苏童又补充道:“《收获》还有一个作者平台结构,它是一直很注意的。比如说笛安,笛安二十岁出头就在《收获》发了处女作《姐姐的丛林》
 。班宇也是,刚写了几篇,就上《收获》了。双雪涛很早就在《收获》发了作品。所以说,《收获》有一个这样的作者平台结构。”
。班宇也是,刚写了几篇,就上《收获》了。双雪涛很早就在《收获》发了作品。所以说,《收获》有一个这样的作者平台结构。”
“现在有的编辑只知道谁有名,不知道谁写得好,这是一个大问题,都盯着那些有名的人去,他宁愿发名作家的烂稿子,也不愿意发无名作者的好稿子。”余华说,“《收获》现在就还继续发那些无名作者的稿子。”
程永新说:“对,我第一次看双雪涛,就是那个《跛人》
 。”
。”
余华很认可:“《跛人》写得好。小说一开始,那个梦做得好。”
程永新说道:“对,这篇小说有点《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味道,虽然比较短,但让人眼睛一亮……”
西川问程永新:“你那时候不知道这个作者?”
程永新摇头,“不知道,完全不认识。我说,这个小说是我今年看见的最好的。双雪涛几乎跟余华、苏童一样的,他其他刊物不给,先给《收获》看再说。”
苏童道:“《收获》的宗旨就是‘耕种,丰收’。”
程永新说:“出人,出作品。”
窗外半轮明月,月光透过椰林,与书屋里的灯光相辉映,疏疏如春雪。
余华深情道:“我想,巴老他们当年,肯定是考虑到了文学创作的‘收获’。为什么只有《收获》对我们重视呢?就是因为这个。可以说,巴金荫庇了我们一代人。所以巴老去世的时候,我记得那么清楚——”
西川问:“巴金是哪年去世的?”

火车站到处都是人。许多人背着大包,包的体积基本上和人相当。有的人除了背着大包手里还抱着孩子,孩子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肆无忌惮地大哭,像指南针一样挥舞着小手。
(双雪涛《跛人》选段)
“2005年,就是我女儿出生的前几天,我女儿是22号出生,他是17号去世的。”程永新说,“我当时在医院里,本来是准备喜事的,结果变得特别难过。巴金是2005年10月17号去世,那天我整个儿觉得崩溃了,天就塌下来了。从我大学毕业到了那里,《收获》有这么一个传统跟习惯,就是每年要给巴金过生日。我们每年秋天就开始准备鲜花,准备蛋糕。过生日时,吃过蛋糕,他家人还会给他擦一下嘴。因为我是年轻人,刚去《收获》,家人会问他:‘你认识小程吗?’‘认识。’他话特别少。就是这样的一位前辈、一棵大树,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余华回忆道:“我记得我当时给李小林发了个短信,里面有一句话:‘是巴金的长寿,让我们这一代作家有足够时间自由成长。’李小林后来告诉我,看到这句话以后,她掉眼泪了。确实是,巴金的长寿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自由成长起来。”
苏童道:“就是一把伞,是一把遮阳伞。”
程永新道:“老巴金几乎塑造了我的人生。上大学之前,他的作品,比如《家》《春》《秋》《憩园》《寒夜》,我都读过,觉得很熟悉他了。但是到了《收获》以后,你才真正发觉他的那种人格魅力。我目睹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作家在他那种强大精神感召力下的成长。巴金先生不仅对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的作家,而且对当代文学、当代作者,都秉持着支持和包容。他就是真诚待人,我觉得一步步走到今天,巴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理解文学是什么,就是要表现人的精神,表现人的善良,表现人性的微妙。所以,他才有那么宽阔的胸怀。在老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身上,我也学到为人、为文的一种气息、一种品质,或者说一种人格的力量。所以说,《收获》原意是大海,要海纳百川,要有大海一样的宽阔的胸怀。我们要像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好文学的成果。”
苏童道:“听完这个,感触很深。我们的初衷,一定是希望大家多来读书。”
“确实是,但是因为忙碌的工作,大家读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房琪说道。
程永新说:“当时社会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去看小说去了。文学因为反映了老百姓、读者的诉求,又与反省历史等都结合在了一起,它是思考生活的。”
苏童说:“ 任何时代,精神都需要有出口。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有种狂热的热潮,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它是所有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人的精神出口,不光是有作家梦的人,不光是有远大文学理想的人,所有的这些精神出口就像是千军万马走过了文学这座独木桥,所以就显示出那样一种辉煌。”
余华道:“我们幸运的是经历了那个时代。当年我印象很深的是邮政局,只有邮政局有文学刊物。再后来,开始出现报刊亭了,报刊亭里也只有文学刊物。”
苏童回忆道:“我也是,我第一次买《收获》是在苏州察院场。我高中时候开始都到报刊亭里面去买,往往没有可买的文学刊物,连《雨花》都买不到,《收获》从来买不到,因为都被别人买走了。所以4号出版,你得差不多7号、8号左右便要去看看杂志来没来。那时候,我们苏州的小城文学青年不计其数。”
程永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就不可能有文学的繁荣。当初文学杂志的发行量是巨大的,我们最多时到过一百万册,因为那时候全中国的人民都在读文学。全世界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地级市、县级市都有文学刊物。文学疆域被拓宽了,中国人对人的精神的方方面面的思考,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一点点地探索,一点点往前推进。中国正因为有了时代的变化,才有了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才有了文学的今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没有中国大环境的改变,没有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没有今天的文学成就。中国文学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站起来了。中国文学的巅峰,一定是沿着这条路,走到一个殿堂里面。当然,文学只是一个方面,只是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