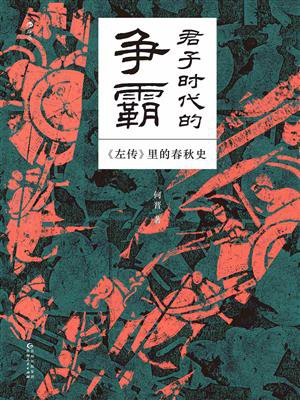郑庄小霸(一)
●《春秋》鲁隐公元年: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也就是《春秋》的第一年里,记载了这样一句话: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对史家来说最为重要的时间、人物、地点、事件这几个关键因素,虽然在这句话中都有了,但仅凭此我们仍然不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详情。还好,《左传》对此做了详尽的解释。
●《左传》鲁隐公元年: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这要从郑伯,也就是郑庄公的出生说起。当初,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他的夫人是从申国娶来的,叫作武姜。武姜生了郑庄公和共叔段,但在生郑庄公的时候,出现了异常,《左传》记载: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
一般生孩子,都是头先出来,脚后出来,即头下脚上。但武姜生庄公时却是脚下头上,反过来了,所以就给郑庄公取名叫“寤生”。郑庄公的出生让姜氏大受惊吓,她也就不喜欢这孩子了。姜氏很爱庄公的弟弟共叔段,甚至想把共叔段立为太子,多次向郑武公请求,但郑武公不同意。
等到郑庄公即位以后,他的母亲姜氏请求把制这个地方作为封邑给共叔段。郑庄公说:“制是一个地势险要的地方,从前虢叔就死在制。这里不行,但其他的城邑都可以给他。”姜氏就要了京这个地方,共叔段到了京,称为京城太叔。
郑庄公有一个臣下叫祭仲,他对庄公说:“一个城邑,若是城墙超过了一百雉(一百雉为300丈,国都的城墙为三百雉,也就是900丈),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最大的城邑,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也就是300丈);中等的城邑,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180丈),小的城邑,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100丈)。而现在共叔段居住的京这个城邑,其规模已经不符合制度的规定了,您以后将很难受。”
为什么城墙的大小会引起祭仲的警惕呢?因为城墙大,就意味着这个城邑很大,城邑大就意味着人口多、势力大。春秋时代,受封的人在自己的封邑里有很大的自主权,拥有自己独立的赋役税收和军队,俨然一个独立的小国王。难怪祭仲要为国君担忧。郑庄公回应说:“姜氏要如此,我能怎么样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处置您的弟弟,别让他的势力蔓延,一旦蔓延开了,您就难以图谋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除,更何况您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您就等着看吧。”
●《左传》隐公元年:
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义的事情做多了,自己一定就会垮掉。
不久,太叔让西部和北部边境一带要同时听候他的调遣。这时候又有一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忍受同时听命于两个人的情况,您现在是如何打算的呢?要是想把国君的位置让给太叔,那我就去为他做事了;若是不想给,那我就请您赶紧除掉他,别让老百姓有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取其祸。”
太叔又把那些原来两属的地方完全作为自己的封邑,地盘一直扩张到廪延这个地方。公子吕着急了,说:“可以行动了,他的势力再大一点就会得到民心了。”但庄公还是说:“他做事不义,没人会拥护他,即使势力大了也会垮掉的。”
这边太叔把城墙修坚固了,粮食也准备够了,武器也修整好了,步兵车兵也招集全了,就准备偷袭郑国的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到时打开城门。郑庄公知道了他们进攻的日期,这才说:“现在可以了。”于是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兵车去攻打京这个地方,京地的人也起来反对太叔段。太叔段就逃到了鄢这个地方。庄公又带兵攻打鄢,五月辛丑这一天,太叔段只好又逃到了共这个地方。
●《左传》隐公元年: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这一整个事情,在《春秋》里就只被浓缩为这样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不过《春秋》中的这句话,《左传》认为大有讲头:这句话里面没有说太叔段是庄公的弟弟,是因为太叔段做得不像一个弟弟;庄公和太叔段之间就好像敌我两国,所以《春秋》用了“克”这个字;这里把郑庄公称为“郑伯”,则是借此批评郑庄公也不像一个哥哥该有的样子,不仅没有好好教诲自己的弟弟,还故意让他弟弟在反叛之路上越走越远而不加拦阻,简直就是养成其恶,欲擒故纵,有失做哥哥的厚道。这是《左传》对《春秋》的解读。
后世也有学者认为《左传》对《春秋》的这个解读不对。例如清代有一位专门研究《春秋》的学者顾栋高,他就写了好几篇论郑庄公的文章,认为郑庄公的做法无论是对他的弟弟,还是对郑国的政治来说,都是值得称赞的。
这次反叛事件,大概让郑庄公对他的母亲姜氏十分气愤,于是就把姜氏安置到城颍这个地方,还对她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就别见面了。)之后不久,庄公又后悔了。但在那个时代,一旦发了誓,是不能随便不遵守的。
一个叫颍考叔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就拿了一些东西来献给庄公,随后庄公赏赐他吃饭。颍考叔吃饭时却把肉搁在一边,庄公问他原因,颍考叔回答说:“小人有母亲,吃过我为她准备的所有东西,但还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请允许我带回去给她尝一尝。”庄公感叹说:“你有母亲可送,我却没有啊!”颍考叔明知故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告诉了他其中的缘故,并且说自己现在后悔了。颍考叔说:“君王不用担心,如果派人挖地一直挖到泉水出现,然后两个人就在隧道中相见,谁说不可以呢?”
●《左传》隐公元年: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主意。进到了隧道里,庄公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出了隧道,也赋诗说:“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于是母子二人的关系又恢复如初。《左传》用“君子曰”的形式对这件事进行了评论——《左传》里的“君子曰”或是作者自己的评论,或是其他贤人的看法:“颍考叔真是纯孝,爱自己的母亲,而且还影响到庄公。这正是《诗经》里所说的‘只要孝子还存在,他的孝心就会影响到别人’。”
郑庄公在国内消除了弟弟共叔段对自己的威胁,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共叔段的反叛残余势力逃到了卫国,因为卫国和郑国是世仇。敌人的敌人,就成了卫国的朋友,《左传》记载,共叔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卫国就替他攻打郑国,攻取了廪延这个地方。郑国毫不示弱,立即带领周王的军队、虢国的军队一起进攻卫国的南部边邑。
郑国之所以能调动周王的军队,是因为郑庄公此时是周天子的卿士,也就是当时周平王的执政大臣。其实此前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就已经是周王室的卿士了。西周末年,周人遭到西方犬戎的攻击,西周的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下,家国已破,后来即位的周平王无奈只好东迁洛邑,而在这次护驾东迁过程中功劳最大的就是郑国的郑武公和晋国的晋文侯。所以《左传》中说:“周之东迁,晋、郑焉依。”
●《左传》隐公三年: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郑国就在洛邑之东,郑武公、郑庄公父子先后都做了周王的卿士,长期把持着王朝的政事,这自然引起了周平王的不满。后来,周平王暗地里把一些政事又交付给当时西虢的国君虢公,想削弱郑庄公的权力。这下郑庄公也不高兴了,责怨周平王,平王又得罪不起郑在公,只好否认说:“没这一回事。”双方为了让彼此相信,就互相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王子狐到了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到周做人质。这一事件,彻底表明了春秋时代的周王室势力已大大衰落,地位远不如从前了。这时的王室,不仅政治地位大大降低,在经济上有时也陷入困窘的处境,时不时还要向诸侯们要钱、要粮、要车。
郑伯克段两年后,也就是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在位长达五十一年的周平王去世了,周桓王即位。此时周王室想趁机在平王死后把王朝的政事交给虢公。郑国于是派军队割取了周王王畿内温地的麦子。这年秋天,郑国军队又抢割了周王首都成周的禾物。周与郑的关系由此恶化。也许是郑庄公做得太过火了,这年的冬天,他的车翻在了济水里。
●《左传》隐公三年:
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
一直到三年之后,也就是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郑庄公才首次到成周去朝见即位已经三年多的周桓王,周桓王没有礼遇他。两年后,周桓王终于让虢公当上了王朝的卿士,这时,周王朝有了两位卿士,郑庄公为左卿士,虢公为右卿士,王朝政事不再由郑庄公一人把持。
●《左传》桓公五年:
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即便如此,周桓王仍然没有消除对郑庄公的不满。在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最终全部剥夺了郑庄公在王朝的执政权,并在这一年的秋天,周桓王亲自率领军队和陈、蔡、卫三国一起攻打郑国。郑庄公也亲自带着军队,布下“鱼丽”阵法,在繻葛这个地方迎击周王的军队。不料陈、蔡、卫的军队是乌合之众,一打就先跑了,于是周王的军队也就乱了,郑国左、右、中三面趁机合攻王师,周王的军队大败而逃,周桓王的肩膀也中了一箭。有人建议追击,但郑庄公说:“君子不会逼人太甚,更何况哪敢欺凌天子呢?我们也就是卫国战争而已,只要自己的国家免于危亡,也就够了。”到了晚上,郑庄公还派人去慰问周桓王和他的随从们。
这次战役,是整个春秋时代唯一的一次天子亲征。作为周天子,周桓王的这一仗可以说打得威风丧尽。周王的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周桓王没有认清当时的“国际”形势。郑庄公自克段消除了国内的隐患之后,借助自己作为周王卿士之便,经常挟天子以命诸侯,率领王师,纠集其他一些诸侯国,攻打那些不服于自己的诸侯国。在繻葛这次战争中,陈、蔡、卫的军队一打就逃,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早已吃过郑国军队的苦头了。
前面讲过,郑伯克段之后,共叔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卫国替他攻打郑国,郑国不仅立即攻击了卫国的南部边邑,而且在第二年的冬天,也就是鲁隐公二年(公元前721年),又再次攻打了卫国。
●《左传》隐公四年: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秋,诸侯复伐郑。……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两年后,在卫国的怂恿下,宋、陈、蔡、卫四国的军队合起来进攻郑国,这是春秋时期首次诸侯国联合起来攻打他国。四国的军队包围了郑国的东门,五天后才撤退。此年秋天,诸侯联军又攻打郑国,并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割走了郑国的麦子,这一次联军除了宋、陈、蔡、卫四国外,还有鲁国的军队参加,不过鲁国这次出兵,鲁隐公并不同意,而他下面的公子翚不听话,执意带兵去参加。正是这个公子翚,七年之后杀死了隐公。
紧接着第二年(鲁隐公五年),郑国为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开始一一复仇还击:首先攻打卫国,虽然卫国后来又带着燕国的军队攻郑,但结果郑国大败燕国的军队;随后郑国又率领周王的军队等进攻宋国,一直打到宋国国都的外城;下一年郑国又侵入陈国,获得了很多俘虏和财物。
郑庄公由于做了周王的卿士,掌握着话语权,因此能以周天子的名义,调遣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去讨伐那些不服的国家。宋、蔡、卫、郕等国,先后都被他以“不服王命”作为由头征伐过。
●《左传》隐公十一年:
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
就在鲁隐公被杀的当年(鲁隐公十一年),郑国还在和鲁国商量攻打许国。这一年五月,为攻打许国,郑国在祖庙内发放武器车辆,不料以前给郑庄公建议掘地见母的颍考叔和春秋时期有名的美男子子都,为抢夺兵车而起了争执,颍考叔抱起车辕就跑,子都拔出长戟在后面追,一直追到大路上也没追上,气得子都怒火中烧。
这一年的秋天,郑、鲁、齐三国军队进攻许国,在攻城时,颍考叔扛着郑庄公的旗子抢先登城,结果子都在下面用箭射他,颍考叔中箭坠亡。另外一人又扛起旗子,登上了城,边挥旗子边喊:“国君登城了!”许国的军队闻声溃退,郑国的军队悉数登城进入了城内。许国的国君仓皇逃到了卫国。
●《左传》隐公十一年:
郑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
战争结束后,郑庄公让士兵们拿出猪、狗和鸡,来诅咒背后射死颍考叔的那个人,要让神降祸给他。《左传》在此事上批评了郑庄公。因为郑庄公大概知道是子都射死了颍考叔,却假装不知道,但又不能不对众人有所交代,就设诅来做表面文章。郑庄公袒护子都,大概是因为子都相貌俊美,是郑庄公的男朋友。
郑、齐、鲁三国军队攻下许国后,齐僖公把许国让给鲁隐公,隐公推辞不受而又让给郑国。郑庄公并没有就此灭了许国,只是把一些军队驻扎在许国,还让许国国君的弟弟居住在许国东部以安抚许国百姓。郑庄公说,这是“天祸许国”,只不过是借我之手来讨伐许国而已,因此自己不敢占有许国。对此,《左传》称赞郑庄公“可谓知礼矣”。这一年冬天,郑国又带着虢国的军队攻打宋国,大败宋军。
●《左传》桓公六年:
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
郑庄公不仅在与中原诸国的征战中多次战胜他国,他的军队在和北方戎族的战争中也多获胜利。隐公九年(公元前714年),北戎入侵郑国,结果大败。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北戎又入侵齐国,齐国向郑国求救,郑国派太子忽率领军队去救援,结果又大败戎人的军队,俘获了北戎的两个首领,斩首披甲之士三百人,向齐国展示了雄风。
可以说,在《春秋》前期的这头二十年里的历史舞台上,郑庄公确实显山露水,出了不少风头,在当时的中原诸侯国中,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