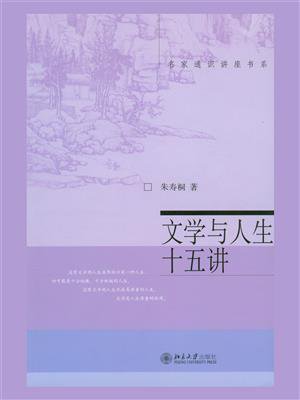一
原生态文学的追寻
原生态的人生情状已经在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共同描摹下得到了呈现,原生态的文学虽然也曾被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描述过,但终究难得征信。因为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的作品,要得以流传下来,无非两种途径。一是通过代代相传的口述和风俗化呈现,例如民歌民谣、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以及传统巫术、民俗仪式等等。这种途径必然使文学在不断的流动、更新中大量地淘洗原创的质素,呈现出的总是经过一定的时代和地域处理过的形态。另一途径自然是文字的记载。而文字是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产物,很难与人类最早可能的文学创作同步,因而最早的文学记载也都是对于若干时代以前的文学的追忆。
这就是说,我们谈论文学的原生态都只能在假定性和虚拟性意义上展开。
远古时代当然没有“文学”一说。而且越是往古,现今所谓的文学与其他文类相混杂的情形越是复杂。但即使从现有的一些将信将疑的文字记载中,也能隐约寻绎出远古人类文学的大致状态。
在中国,传说中最古老的文字集成的典籍有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文学史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这些“当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古老的上古经典是《尚书》,传说为孔子所编,其中的篇什有很多都是伪作。《尚书》收录了初民时代的征伐誓辞、文诰书札、往古纪事等内容,自然含有相当多的文学成分。如《甘誓》篇,是夏启在甘之野对有扈氏作战前的誓词,宣布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声言现在已经到了“天用剿绝其命”的时候,他们对于有扈氏的武装行动乃是“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是被古籍研究专家认为比较靠得住的一篇文字,后人伪作的痕迹也还是相当明显;不过从其声腔和意旨来看,可以理解为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的前驱。相传为夏禹时伯益所作的《山海经》,文学意味更其浓厚,是中国最古老神话记录的集成,夸父逐日的故事,西王母的神话,还有“刑天舞干戚”的神话,等等,都出自这部集远古地理学、风俗学和神话于一体的大书。《山海经》里的许多篇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学最可靠的资源,如刑天的神话便为陶渊明、鲁迅所十分欣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说的是一个叫做刑天的神祇与上帝争夺帝位,上帝砍断了他的头,并把他的头葬到了常羊之山;可没有头的刑天并没有死,而且还十分威猛,他从两个乳头中长出了眼睛,并以肚脐为嘴,拿起干戚当作武器挥舞个不停。陶渊明从中看到了一种精神,并深深为之感动:“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鲁迅也常引用陶渊明的诗句,对刑天精神表现出深挚的赞赏。由此可见,包括《山海经》在内的典籍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神话和想象,体现着远古和上古时代中国人祖先文学思维的结晶,而且也构成了后世文学的基本资源。
这些为后人所传承的远古文学,其与远古人类的人生之关系,仍与我们今天所看到和体验到的相类似。文学是人生斗争的工具,是人类精神想象的写照,是人生非常态体验的精彩描绘。文学诉诸于人们的情感,能够调动和调节人们的情绪,于是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的种种人生争斗都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学副产品,这些文学副产品或用于提高本阵士气,统一己方意志,或用于涣散敌方阵势,瓦解对方斗志,体现着典型的“为人生”的价值功能。历史上著名的“四面楚歌”事件,还有庾信的《哀江南赋》等传说,都是在后一方面发挥文学作品人生斗争作用的例证。
人常被视为宇宙的精魂、万物的灵长,其与一般动物的最大区别,便是在人生中充满着精神的成分、情感的活动和想象的内容。人类不满足于形而下的人生体验,总是企求着突破这种人生体验的有限性,而试图通过精神的、理念的和情感的想象作弥补和充实。于是,对于天空的想象,对于地府的想象,对于山中仙窟和水泽龙宫的想象,成了人生体验的一种自然延伸,成了人生体验的一种想象性补充,成了人生体验中最富于美感的对象。这便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神话,被马克思称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的最初的文学。中国古老的神话应该非常丰富,《山海经》等典籍收集的诸如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之类仅仅是其中有限的例证。不过从这有限的例证中我们依旧能体悟到,文学作为人生体验的一种想象性补充,作为人生体验有限性的一种审美延伸,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文学不仅直接反映着人类远古时代的精神生活,而且体现着远古人类的精神祈望。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之类的神话表达的是人类对于自身克服强大的大自然并试图与之取得一种平衡的精神祈望,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神话表达的则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命力的强大与坚韧的精神祈望。这样的精神祈望对于鼓舞人类的生活意志,提高人类生存的自信力,引领人类精神的奋发向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体现着这样的人生功能,远古时代的文学雏形总是从精彩、宏伟、博大、崇高、壮美的角度反映人生和人生的想象,这既是神话的特征,也是文学与人生最初关系的特色。
这就是说,在原生态意义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异常紧密,可以说文学实际上就是人生的一种形式,是早期人类对于人生作精神、情感处理的必然结果。越是早期的文学传说越能说明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至为密切。古人所记载的最古老的歌诗,传说是涂山之女等待大禹时登高望远所吟唱的:“候人兮猗!”《吕氏春秋》载:“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1 据《吴越春秋》,这涂山之女名唤“女娇”:
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云:“吾之娶也,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於是涂山之人歌之。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照这样推测,《涂山女歌》乃是女娇作于与大禹婚后长别的一段时日。
沈德潜以及许多古史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这首《涂山女歌》不可靠,沈氏主张“帝尧之世”出现的《击壤歌》为古诗之始。该歌吟曰: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四言变体的诗歌,已大有《诗经》的格调与格局,显然不可能产生于沈德潜所说的“近于荒渺” 2 的帝尧之时,郑振铎判定其为“不必辩解的伪作” 3 ,显然很有道理。倒是上述《涂山女歌》“候人兮猗”的歌叹,只有两个实字,短促而简约,情浓而意深,感喟而唏嘘,很有古风,作伪的可能相比之下要小得多。
人类在远古时代,虽有人生感叹、情感表现,奈何语言简单、传达精约,诉诸歌诗则往往每句字数由少渐多,概成规律。《诗经》以四字句诗为主,一般认为多是周平王时代以后的作品。在此之前,诗句若在四字以上,往往存疑。沈德潜在《古诗源》中同样列为伪作的《白帝子歌》(见王子年《拾遗记》,又谓《诗纪》首录之)便是这样的伪作,这首被传为帝尧之时的诗歌竟有“天清地旷浩茫茫”、“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的七字句,诚如郑振铎所批判的那样:“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同样的道理,吟唱出“登彼箕山兮瞻天下”这样比较复杂句式的《箕山歌》也不可能是炎夏时代的作品。 4
依此推测,传说中的涂山之女祈望大禹的“候人兮猗”倒可能是比上述《击壤歌》早得多的歌唱。《诗苑》一书认定为黄帝所作的《弹歌》,虽然未必那么古远,但从两字一句的格局看,可以理解为我国祖先最早的诗存之一。这首在《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中有记的诗是:“断竹,续竹,飞土,逐
 。”又有传为虞帝与皋陶诸臣唱和之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郑振铎认为“比较的可靠”,但他没有论证
5
,其实从诗句实字字数判断,这首诗可能产生于两言诗之后、四言体之前,显然是一首相当古老的诗篇。既然郑振铎认为上述虞帝与皋陶诸臣唱和之歌比较可靠,则没有太多的理由认定《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不可信”。该歌传为舜将禅位于禹,与群臣一起所唱,“卿云”即为“庆云”,瑞祥的云彩。此歌道:
。”又有传为虞帝与皋陶诸臣唱和之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郑振铎认为“比较的可靠”,但他没有论证
5
,其实从诗句实字字数判断,这首诗可能产生于两言诗之后、四言体之前,显然是一首相当古老的诗篇。既然郑振铎认为上述虞帝与皋陶诸臣唱和之歌比较可靠,则没有太多的理由认定《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不可信”。该歌传为舜将禅位于禹,与群臣一起所唱,“卿云”即为“庆云”,瑞祥的云彩。此歌道:
卿云烂兮。
 缦缦兮。
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何等精蓄、优美而豪壮,难怪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和民国先贤对之那般激赏:民国九年,章太炎建议采用此歌为国歌歌词,次年经萧友梅谱曲,民国十一年正式公布为国歌。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之后才被废止。
诗中的“
 ”字形容丝带缠绕,通“纠”。不少古书依照字形改为“礼”字,作“礼漫漫兮”,显系杜撰。作为古诗,特别是“歌”,总是以具体的形象吟诵为主,不可能在“卿云烂兮”这样的具体环境烘染中立即夹上“礼漫漫”之类抽象化的形容。越是早期的文学在创作上越是会遵循形象化的原则,“
”字形容丝带缠绕,通“纠”。不少古书依照字形改为“礼”字,作“礼漫漫兮”,显系杜撰。作为古诗,特别是“歌”,总是以具体的形象吟诵为主,不可能在“卿云烂兮”这样的具体环境烘染中立即夹上“礼漫漫”之类抽象化的形容。越是早期的文学在创作上越是会遵循形象化的原则,“
 ”是形象的描绘,而“礼”是抽象的概念,以“礼”入歌,此时显然不大可能。
”是形象的描绘,而“礼”是抽象的概念,以“礼”入歌,此时显然不大可能。
此诗基本上是三言体,从其质朴的造境和复沓的语势看,应与前引三言体歌时代相当。有的古书传述此《卿云歌》为:“卿云烂兮。
 缦缦兮。明明天上。烂然星陈。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迁于贤圣。莫不咸听。
缦缦兮。明明天上。烂然星陈。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迁于贤圣。莫不咸听。
 乎鼓之。轩乎舞之。日月光华。弘于一人。于予论乐。配天之灵。精华已竭。褰裳去之。”从其以四字句为基本体格来判断,也可知是后人改造的伪作。
乎鼓之。轩乎舞之。日月光华。弘于一人。于予论乐。配天之灵。精华已竭。褰裳去之。”从其以四字句为基本体格来判断,也可知是后人改造的伪作。
当然,诗句字数的多少并不是判断诗歌产生年代久远程度的唯一依据。但面对荒渺的远古,面对湮滞无可考的远古人生,面对用语言作传载的文学,后人的推断除了根据诗歌的语体习惯而外,再寻找可靠的途径便显得特别困难。
1 杜文澜:《古谣谚》卷四十三,第56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2 沈德潜:《古诗源》,第1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3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第3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4 同上书,第35—36页。
5 同上书,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