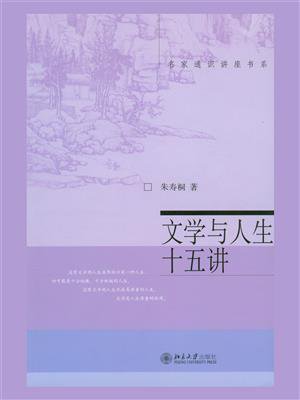二
原生态的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如果我们可以将《弹歌》和《涂山女歌》理解为现存中国古代文明遗存中最早的诗歌,最古老的文学标本,则从中可以窥见,原生态的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原本是那么紧密。
《弹歌》反映的是狩猎情景,或者说是一种狩猎的过程,或者可能是一次成功的狩猎之后的不无夸耀的庆祝性吟唱,甚至可能是长者对于幼者的教学训练词。无论怎样,它是当时人生活动的实写,至少是与人生活动密切相关的歌吟;它是古代人类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人生余裕的一种表现。那种关于狩猎的过程性的简单描述,是最古老的叙事诗,是叙事文学的雏形。
《涂山女歌》则是抒情文学的雏形,是最古老的抒情诗。它是人生企盼和感叹的记录,是人生情感的质直而优美的抒发,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心灵郁积的宣泄。与上述《弹歌》相比较,可以看出最早的抒情诗与最早的叙事诗之间很有趣的分别。
首先,叙事诗要求一种传述性,用今天的话说,需要反映一定的公共空间,需要一定范围的公共认同。《弹歌》无论作为狩猎过程的描述,还是作为欢庆时候的歌吟,抑或是作为一定范围的教学训练词,都要求这样的一种空间和认同。抒情诗则反映的是个人化的话语,对这种空间和认同的要求并不那么明显。《涂山女歌》的语气和语序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它是诗作主体——那个涂山之女的自我表述,她不指望有结果,不指望有听众,不指望被欣赏,当然也从来没指望被我们拿来在这里作为话题。从这些方面来看,它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功利作用的。但它对于主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抒情文学可能就是这样:它在功利意义上对于一般人也许可有可无,与一般人的人生的关联并不密切,可对于主体则是凝结了人生的全部意义,体现了人生的最高意义。
其次,正因为这样,叙事诗往往找不出明确的主语,它属于一种公共叙事,而抒情诗则有明确的主语。《涂山女歌》的主语,用现代汉语表示,无非是“我”,这个“我”便是作歌的涂山之女。《弹歌》的主语则无法这样认定,它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甚至是当时的整个人类。于是,从最古老的文学考察来说,叙事文学往往属于公共叙事,抒情文学则属于个人话语。
再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叙事文学反映的常常是人生的外在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抒情文学反映的则是人类的内心活动,是精神层面的抒写。
这样的分别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文学走向复杂态势之后,这样的分别往往趋向于模糊。但总体来说,从文学原生态形成的这种分别毕竟是典型的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之间的分野,它们分别反映着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在相对意义上的典型状态。
无论是最早的叙事文学还是抒情文学,都反映出原生态的文学与远古人生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弹歌》代表的最早的叙事文学是人生活动的直接写照并且可能直接服务于人生活动,是文学最原始最质直的历史样态,也体现了文学与人生最直接的联系。《涂山女歌》所代表的最早的抒情文学反映的是远古时代人生活动的高级形态——精神的诉求,是超越了基本的人生活动——如狩猎、生产之类,而进入人生余裕的精神生活状态的心灵表现。不离开具体的人生活动,同时又超越于具体的人生活动,而进入人生余裕的精神生活状态的心灵表现,应该被理解为文学与人生最本质关系的体现。
作为人类原始艺术组成部分的原生态文学,其在起源意义上与人生的紧密关系早已为美学家所注意。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认同的劳动说(即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最为科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的生产劳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生活动 1 ,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审美属性;文学艺术的起源,显然就意味着人类与对象审美关系的确立,体现着人类独特的劳动的成果与意义。对于这种劳动说贡献最大的是普列汉诺夫。这位杰出的俄罗斯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在其名著《没有地址的信》中,列举了大量的原始人生材料,论证“劳动先于艺术”的观点:“艺术发展是和生产力发展有着因果联系的,虽然并非总是直接的联系。”
其实,劳动说这种较为深奥的原理已经为我们所列举的《弹歌》所证实。更能直接证实这种劳动说的是《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所谓:
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已成而示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说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此之谓也。
翟煎讲的是治国立法之道,后人每每引用他的“举大木”说解释文学艺术的起源,并且与西方的劳动说相印证,而且也得到历代不少中国文学家的认同。至少现代作家鲁迅是认同这种文学起源的“举大木”说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门外文谈》中这样叙说文学的起源: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相对于劳动说,有关文学艺术的起源尚有模仿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神示说、神话原型说以及巫术说等等。
模仿说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同意此说,在《诗学》中认为诗歌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古罗马时代的卢克莱修、贺拉斯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中国古人也有自己的模仿说,晋代阮籍在《乐论》中就曾指出过,原始歌谣有“体万物之生”的性质,也就是说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游戏说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马佐尼对模仿说的改造与发展,他在继承和倡导模仿说的同时,提出了“文艺是游戏”的观点。康德则沿此思路把诗歌当作“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后在席勒的阐述中正式形成了艺术起源的“游戏说”。席勒认为,原始人意识到人生受到来自于物质与精神的束缚,于是希望运用余裕的精力去表达对于自由的渴望,这便是游戏;文学艺术便在这种游戏中形成。雪莱将模仿说和游戏说结合起来,指出:“在世界的青年时代里,人们舞蹈、唱歌、摹仿自然事物,并在这些行动中,犹如在其它的行动中,遵守着某种节奏和秩序……这些通过摹仿所作的再现,各有属于它自己的某种秩序或节奏,听者和观者从这中间所感觉到的快乐,比从任何其它秩序中所感觉到的更为强烈、更为纯粹:近代作家们把接近这一秩序的感觉,称为美的鉴赏。” 2 心灵表现说也产生于古希腊哲学,不过到了19世纪才为浪漫主义文艺家所明确倡导。雪莱在《诗辩》中总结出诗歌是“野蛮人表达周围事物所感发他的感情”,因而是“想象的表现”和心灵的外化。柯勒律治、布拉德雷、王尔德等都有过这类表述。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表现”、“直觉即艺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用精神分析学观点解释文学艺术的起源,认为艺术实质上是以性本能为核心的无意识表现。中国古代心灵表现说也很发达。《礼记·乐记》即已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中国古代极为流行的“诗言志”说其实正是中国式的心灵表现说。《尚书·舜典》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明确指出了诗歌产生于心灵的现象。“志”就是心灵,这在《毛诗序》中有更明确的说法:“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还有一些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学说将这个论题引向了更为神秘的境地。例如神示说。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曾把诗歌的产生神秘地描述为神的灵感在诗人身上的依附。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承认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但坚持认为心灵是上帝的形象和创造物。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家蒲迦丘认为诗来源于上帝的胸怀。又如巫术说。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等著作中,已经涉及到了原始文学与原始宗教的关系。19世纪以后,泰勒、弗雷泽等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现存原始部族的巫术的研究,奠定了文学艺术起源的“巫术说”的基本框架。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正是在这些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观念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艺术起源于原始人交感巫术的论点。巫术说往往还有原始生活考古材料作依据。考古学家曾通过放射性同位素碳的测定,确认绘有巫术仪式图像的马格德林期洞画约出现于公元前18000年至11000年之间。此外还有神话原型说。该学说集成于加拿大文学评论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理论,他认为文学都是具有一定原型的,批评者应将文学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关系和文学传统中去考察,甚至上溯到神话意象中去。有些研究者曾根据现今少数民族和原始部落的神话体系推证文学起源,其结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中国古代也不乏这种从神巫角度解释文学艺术起源的观点。《周易》上经《豫》(卦十六)有这样的话:“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表明音乐歌诗之事与古人敬天神的联系。这也就是“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魏书·志第十四 乐五》)的原始情形。
除此之外,近代以来各种文学艺术起源说出现了很多。如有人将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提出的著名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的论述理解为一种艺术起源说,达尔文提出的音乐和艺术的起源来自于性的吸引的“性爱说”,美国考古学家马沙克提出的最早艺术为原始人类记录季节变化之符号的“符号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往往也都有一定的材料支撑,但每一种说法又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包括为人们认同较多的劳动说。面对种种学说的歧异纷繁,至少必须明确以下三个基本点。其一,所有的文学艺术起源说都通向对于文学与人生紧密关系的确认,它们都可以用来论证文学艺术在其早期与人生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二,所有的这些学说不过都是假说。既然都是假说,它们之间可能有科学性程度上的差异,但其中任何一说都没有否定另外一说的资本。稍一分析便知,之所以涌现出这么多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假说,是因为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侧重点去考察了文学、艺术与原始人生的关系,他们的结论都带有各个角度、各个方面以及各个侧重点的特有内容。其三,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假说都不可能是唯一正确的文学艺术起源说。或许所有这些来自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各个侧重点的假说综合起来,才能够迫近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正解,才能够解开原生态文学与原始人生关系之谜。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3页。
2 雪莱:《诗辩》,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5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