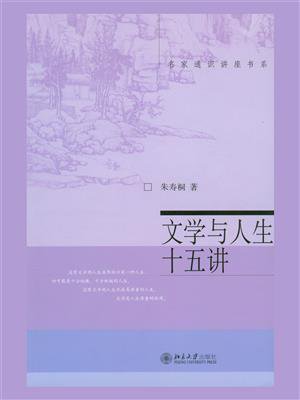一
综合理论中的人生余裕
文学是人生的余裕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综合了各家文学起源理论的结果。
构成这种“综合说”的核心命题是,文学艺术的原始雏形固然来自于人类最基本的人生活动——生产劳动,但并不像劳动说所描述的那么直接,似乎一旦产生了劳动便同时产生了文学艺术的雏形;在人类生产劳动达到一定的层次,劳动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即人类产生了一定的人生余裕感之后,原始的文学艺术才会以各种形态出现。
19世纪后期,有关文学艺术起源的劳动说曾热闹一时。欧洲民族学家、艺术史家们为此展开过热烈的论争。德国经济史学家毕歇尔(K.Bücher,1847—1930)在《劳动与节奏》一书中认为,劳动、音乐和诗歌最初是三位一体地联系着的,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同时产生的。这种说法受到了德国美学家德索(M.Dessoir)的质疑,他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认为,原始诗歌的出现是为了使劳动变得更轻松。他的这种说法否定了那种认为原始劳动诗歌的产生是为加强劳动效率的假说,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过他论述的劳动与诗歌产生的先后次序倒是相当可信。人类最初的生产劳动充满着紧张,完全受着本能求生愿望的支配,或渔猎,或抢夺,全都为了维持自身以及族群生存的最基本的温饱需要。当这种温饱需要时时处在威胁之中时,原始文学艺术的产生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劳动智慧的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和成果不断增加,原始人类不仅在低层次上基本满足了维持生存的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且获得了克服自然困难的优越感及心理上的满足,这就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产生了人生的余裕感。由这种余裕感自然派生出各种原始的娱乐活动和精神愉悦活动,从而构成了各种原始文学艺术的雏形。
原始人类自觉地把握了自己的生产活动,自觉到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有了一种与之相处的自信与余裕感,同时也由于生产活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时间过剩和精力过剩,对于自然的模仿就成了填补这种时间空白、发泄这种余裕精力的基本途径。更重要的是,用鲁迅的话说“一味要好”(也即希求文明、发展)的原始人类又从这种对于自然的模仿中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快感和精神享受,慢慢地他们会在紧张的人生中设法挤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重复乃至改进这样的模仿活动,这又形成了原始的游戏。特别是当原始人在生产活动中取得巨大收获,有一种庆祝的冲动以后,他们往往还会通过再现劳动场景、模仿劳动过程的方式进行这种游戏。前引《弹歌》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游戏的产物。
原始人对他们所面对的大自然既充满着模仿的欲望,也充满着解释的热忱。解释自然是人类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余裕之感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余裕将自然当成一个审视和解读的对象。原始人对于自然质朴而烂漫的解释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十分灿烂的神话文明。原始人或为了劳动间歇的游戏,或为了劳动之前的祈福,对这种神话境界也经常作模仿或再现,这便是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神示说、神话原型说以及巫术说等假说的基本依据。
其他有关文学艺术起源的假说,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原始人类人生余裕感的描述。如季节记录符号说,反映了原始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注意并运用季候规律,这实际上是人类在与大自然相处的一种余裕的表现。再如性爱说,虽然是对两性相悦这样一个自然的本能的阐释,似乎与人生的余裕关系不大,然而,通过歌吟乃至舞蹈等展示自身性别魅力的方式表达性爱,并由此开启了文学艺术最初的空,则应在人类拥有了相当的物质余裕之时。性爱的表达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灵表现,这样的心灵表现要求主体有相当余裕的心态。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原始人表达这种性爱的各种装饰也都与人类当时最基本的人生活动——生产劳动密切相关,而季节的记录也是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可见从符号说或性爱说所推证的“余裕”都是原始人基本人生活动的余裕。
或许所有上述这些方面都加起来也还是没有充分说明文学艺术起源问题。富于想象力的人类文化学者和艺术哲学家还可以作更多方面的推证、假想。但是,即使再来一打以上的推证和假想,也还是无法越出原始人生之余裕的表现这样一种综合性的概括。
这种综合肯定各种文学起源说的人生余裕观与古今中外得到较为普遍认同的劳动说起了某种龃龉。或许有人会用《淮南子·道应训》中的“举大木”故事证明:文学艺术只产生于劳动,与人生的“余裕”看不出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未举过大木的人的妄断。但凡有过类似于“举大木”或干力气活经验的人都能体会,在重体力劳动中确有打劳动号子唱“举重劝力”之歌的人,但绝不是那种干起活来十分吃力的人,而是对他们所承受的重力能够胜任的人。比如说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是100公斤,他承受了60公斤,只是他承受能力的60%,那么,他就有足够的余裕打号子或者想些别的什么事情,这样的“劳动”才可能产生类似于文学艺术的东西;如果他承受了95公斤以上的重量,那他就连喘气的功夫也没有了,何来打号子的力气?又怎能产生文艺?劳动者为自己能够胜任应承担的重力感到一种余裕的快感,这种快感的发泄导致了嘹亮的号子和劳动的欢歌。这种号子和欢歌又能调节劳动气氛,统一劳动节奏,感染其他人的情绪,于是得到更多的认同进而造成流行。这样的例子依然说明,文学艺术与其说来源于劳动,不如说来源于劳动中产生的人生的余裕感。
其实,中国古书里记载的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的故事,都可以用来说明原始的文学艺术产生于劳动中的人生的余裕感。《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关于上古时代“葛天氏之乐”的记录,其中《奋五谷》、《总禽兽之极》等篇分别是歌吟农业耕作和狩猎生活的;《史记》索隐所引《三皇本纪》,《古今图书集成》所引《辨乐论》,还引述了据说产生于伏羲时代的“网罟之歌”,显然是早期渔事的歌吟。这些直接与人类早期最基本的人生活动密切相联的歌乐,与其说是上古时代人们对相关劳动本身的歌唱,还不如说是人们由这些劳动所产生快感(由物质、力量、精神、智慧等方面产生的余裕感)的一种夸耀的表现。上古时代的人们并不是如有些后人想象的那么无聊或那么浪漫,像汉代学者何休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煞有介事描述的那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如果不是食有余而事可已,不是从这种求食和做事中体尝到了某种余裕之感,那歌是无从作起的。
“余裕”一词最初是从《孟子·公孙丑下》那里来的:“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余裕与“绰绰然”连在一起,形容做任何事情,想任何问题,都在心理上有相当大的可供自由支配的余地。
“余裕”的文学观应该说是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这篇著名讲演中提出来的。鲁迅说:“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除了在民族文化的总体上体现文学的余裕品性而外,鲁迅还从文学的欣赏和接受过程论证了文学的余裕属性,他对黄埔军校的将士们如是说:
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因此,他认为文学是革命成功以后,大家的人生有了余裕之感以后的事情:“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
当然,鲁迅的余裕说主要考察的是文学功能而不是文学起源,不过它同样对于我们思考文学起源问题有启发意义。本书所持文学艺术起源的综合说充分借取了各家假说,并以认同面较广的劳动说和鲁迅提出的余裕说为基础。与鲁迅不同的是,我们更多侧重于文学艺术起源意义上的人生余裕感,并强调这种余裕感与人生的基本活动——生产劳动之间的密切联系。
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对文学的余裕和人生的余裕有过相当精辟和从容的论述,他是从书的设计说起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我之所以要将鲁迅这么长的一段文字悉数引出来,是因为鲁迅在这里漫不经心地讲述了一个异常深刻的道理,这道理不仅在“文学与人生”的话题上有用,实际上在民族的精神构造这样的宏大话语上也很有用。更充分的理由是,偏偏鲁迅这样重要的观点,却常常并不为人所熟知,因为鲁迅给人们留下来的印象,鲁迅给那些哪怕是研究鲁迅的人留下的精神遗产,可能什么都有,恰恰是没有“余裕”的。
鲁迅从读书的感觉引申到人生的普遍心理:在“不留余地”的空气里,人的精神会受到局促感的压迫,那样精神就得不到舒展,当然极不利于精神的创造。
接着鲁迅又讲到外国文学作品的一般情形: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穿插着有时显得相当冗长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原来这些都是调动读者在阅读中的“余裕心”的!这是一番了不起的发现,是引领我们读书的一种精彩的理论,一种足以震撼我们心灵的心得。我们读外国小说时,往往也常以其中过多的描写和穿插为非,如果不是抱着研究的眼光去阅读,我们就会很自然地略去那些描写与穿插,直接寻找主要人物的行踪和他们的会话,以便尽快地进入故事情节。这样的阅读都不是优雅的、妥当的阅读,因为不够从容,因为不能显现出余裕的心态;这样的文学接受显得过于匆促。
鲁迅的这番见解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很有意义也很严肃的教训,甚至对于鲁迅本人也不例外。鲁迅年幼的时候不喜欢中国旧戏,尤其不能忍受戏里老旦小生们一字一板的演唱,——这只要读一下他的小说《社戏》就清楚了,另外他忍受不了的还有剧场里锣鼓的喧闹以及人声鼎沸的喝彩和嗑瓜子的声音。确实,中国旧戏有其不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和现代人生休闲方式的一面,但它的特殊的剧场效果明显地与中国老百姓传统的休闲方式联系在一起,反映的正是中国人传统的享受余裕的心态。今天的青年人如果本着这样的观念去看传统戏剧,就自然会有另一番观感与心得。
中国传统的文学与艺术往往比较多地注意在“余裕心”上培养人们的情趣。中国文学,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小说戏剧,一方面强调人生的实写,强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但另一方面又讲究一定的套路,特别是小说、戏剧,还需要一定的套语和过场形式,这些内容在阅读和欣赏效果上,都是为了调动人生的余裕感。写诗也是如此。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意思是写诗吟诗未必一定要将自己逼得、苦得像孟郊和贾岛那样,完全可以在悠闲的阅读中得到灵感和诗趣。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将中国诗学中的余裕因素道得更为明白: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为赋新词强说愁”,不必自己有愁再去写诗读诗,这里就是一种写实的余裕哲学的表述;等到所有的愁滋味都领略过了,再来做诗写词的时候,也不必完全说干净,“却道天凉好个秋”,神来一笔,还是给自己同时也给别人的心灵留下清爽的余裕。
鲁迅从文学艺术的余裕心态说起,论述到民族的余裕心的培养问题,认为如果没有余裕心,民族的前途便堪焦虑。这是一个沉重得不容有一点余裕的话题,可惜我们在“文学与人生”的课堂上才能讲到它。一般来说,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国民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无论是政治教育还是公德教育,都是将余裕放置在否定的抑或是极其边缘的位置上,一般不提倡余裕心的培养,什么事情、什么时候都要求竭尽全力,都要求全力以赴,都要求达到努力的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效益的最大化;“人生能有几回搏?”作为一种意志和精神象征的表述,常常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样的教育当然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成熟、成就,并尽可能使之在成长、成熟、成就的道路上少受挫折,少走弯路。但这样往往很难调动和激发他们的审美之心,人的灵魂会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越来越粗糙。人生的过程的体味往往被忽略,人生的各个阶段的结果常常成为人们竞相追求的目标。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如果都是这样,而不讲求任何余裕心,不讲求优雅和诗性,那么这个民族的前途确实会有些问题。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体验人生、认知人生的时候,不妨读读文学,讲讲文学,谈谈文学和艺术,这也是人生余裕的体现。
说到民族与余裕心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还是有相当深厚的传统的。在我们的印象中,日本这个民族似乎就缺少这种余裕心。前些年企业文化界不断热衷介绍的日本企业精神,还有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日本人的人生境况,好像到处充满着“加油”、“好好干”的勉励,没有一点余裕的感觉,日本人好像整天都在玩命。近些年我看到一些资料,好像日本现在对青少年比较注重“余裕教育”,就是在鼓励他们学习之外,培养他们的余裕心。据说热爱生命是“余裕教育”的重要主题,说是教育青少年热爱生命,能帮助抵制邪教的诱惑,同时使他们在挫折面前变得坚强。热爱生命的余裕教育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热爱其他生命。因此,此项“余裕教育”的组织者经常带领学生到牧场体验生活,包括到牧放的牛马当中去,要求学生学会与这些还具有野性的动物相处,通过喂养它们,彼此成为朋友。“余裕教育”的另一项内容据说是利用周末让青少年到所谓农业学校体验农村生活,通过农业学校的生活,学生可以体会到衣食来之不易,同时,学生自己动手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探索精神,练就吃苦耐劳的本领和健康的体魄,这对学生今后走上社会应付各种困难大有益处。这样的报道我觉得即使可信,也只是说明日本的教育理念中引进了“余裕教育”的概念,这是值得赞赏的;至于具体的做法,我倒觉得缺乏很明显的创意。我们国家有关关爱生命的教育并不弱,一到抗灾救灾的时候,学校里要求学生捐赠衣物钱财的布置可能比哪里都快,至于到农业学校去锻炼,我们早就有学工学农的教育实践了。
要进行余裕教育,我觉得不如教学生学会唱歌,比如这样的歌:
不能这样活
东边有山,
西边有河;
前边有车,
后面有辙。
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
究竟你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
呦嗬嗬!
春夏秋冬忙忙活活,
急急匆匆赶路搭车,
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
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
闭上眼睛就睡呀,
张开嘴巴就喝;
迷迷登登上山,
稀里糊涂过河。
再也不能这样活,
再也不能那样过,
生活就得前思后想,
想好了你再做。
生活就像爬大山,
生活就像趟大河,
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
一个脚窝一首歌!
好一个“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人确实不能这样活。人应该有充分的余裕心领略大自然,领略自己身边的一切,并咂味出大自然和周围的一切所包含的可能意义,这才是活着,这才是人生,这才谈得上诗意地栖居!
美国著名的盲聋作家海伦·凯勒写有一部题目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自述,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天,她的好朋友乘着早晨清爽的空气来看她,她问她一路上看到了什么没有,朋友说什么也没有看到。她很气愤,激动地说,你应该看到太阳,看到大地,看到大地上的青草和草上的露珠,看到树在晨风中的摇动,看到小鸟在树上歌唱的样子,甚至可以感受到小鸟歌唱时树枝微微的颤动。这一切都是大自然最美好的赐予,可是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大意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感悟到这种心情。
有了这样的心情,就是有了余裕心,才可以真正领略文学的真意。领略了文学的真意,也就领略了人生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