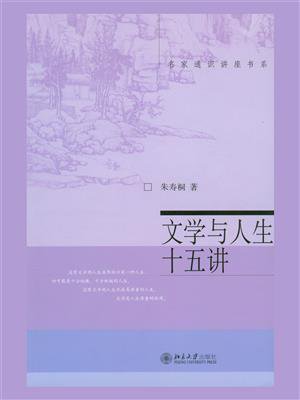二
从人生的余裕到余裕的人生
文学艺术作为人生的余裕的结果,其诞生以后便沿着余裕的人生的轨道走上了发展的长途。这便是文学与人生关系所必然发生的变异,也是原始生活意义上的文学与人生关系面临必然改变的关键。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分工密切相联,但在文学与人生这一特定的关系上,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的则不完全是进步。一方面,社会分工使得一部分人有可能比较专业地从事文学艺术活动,促进文学艺术迅速向高水平发展;另一方面,文学艺术成为一种专业以后,从创作过程到欣赏活动都开始脱离广大民众最一般的人生,从而由作为人生余裕的产物一变而为少数人余裕的人生的体现。这是文学与人生关系的一种悲剧性转折,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所必须偿付的代价。
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生产劳动,围绕着统治者做一些形而上的工作,于是早期的文学艺术就派上了用场;不过这种为少数人所创制同时也为少数人所利用的文学艺术势必疏离广大民众的日常人生,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或专擅。
作为人类早期统治者余裕的人生的基本活动内容,神灵崇拜、祖先祭祀和庆典宴乐等都需要文学艺术。前面所举的《卿云歌》正是人类早期统治者阶层庆典宴乐情形的写照。最古老的音乐歌舞、歌谣诗曲,一般都是为适应统治者祭祀崇拜或歌功颂德的需要,由巫师、司仪之类的“专职人员”设计、营造甚至付诸表演的,因而与广大民众的人生很难发生直接的关系。据说成汤时代就涌现了“大攫”、“晨露”、“九招”、“六列”、“桑林”等乐歌乐舞,《尚书·伊训》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之记,可见那时宫廷里巫风与歌风相应相和,且已相当炽盛。一直到商朝末年的纣王时代,此风更甚,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而且还“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1 这确实太过分了。于是周武王灭殷商时历数商纣王的种种罪状,其中就包括这类酒池肉林式的骄奢淫逸。在宴乐方面,周武王还指责纣王“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史记·周本纪》),可见他也同纣王一样,将歌舞音乐之事看得非常重要,不过他比纣王看得更加神圣,认为先祖之乐是不应随便改篡的。
周代果然十分重视音乐歌舞,而且因为将音乐看成先祖之制,遂在典章制度建设的意义上构造音乐歌舞体系,如音乐分“风”、“雅”、“颂”,歌舞分“大武”、“勺”、“象”等等。《诗经》三百篇保存了这一时代音乐文化和诗歌文化发达的印记,因而孔子对周朝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冯梦龙在《白话笑史》中曾说过一个白字先生的笑话,他将“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一位高明的先生知道念错了,按照正确的予以纠正,谁知学童们惧怕他,一个也不来上学了。时人讥讽这种现象说:“都都平丈我,学生都来坐;郁郁乎文哉,一个都不来。”这则笑话说明,《论语》中所形容的周朝文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常识,而这种历史情形毕竟远离一般人的人生,为人们所耳熟但心不能详。
是的,社会分工出现以后的文学艺术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或专擅,离开了一般的普通的人生,许多人对于这样的文学艺术都是耳熟不能详,大有隔膜之感。由于与自己体验的人生拉开了距离,大多数人对文学艺术心存隔膜,这无异于鼓励了少数人将其神秘化、复杂化、神圣化,反过来以更加令人隔膜的疏解教谕或教化民众。
例如,对于《诗经》第一首《关雎》的疏解,就典型地显露出这种教谕和教化的迹象。诗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分明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在《风诗类钞》中形容这首诗的情景:“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译》中形容得更加纤细:“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苗条形象使他寤寐不忘,他整天地想;要是能热热闹闹地娶她到家,那是多好!”但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解释。从汉儒开始,对这首明显产生于民间的爱情诗就有了让人亲近不得的玄乎解释。《毛诗序》这样认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并解释说:“《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好家伙,一首先民田塍间或小河边男女相悦的情歌,竟成了周文王后宫里的后妃之德的颂歌!说是文王妃太姒不仅不专宠,而且每每愿意将所见到的窈窕淑女求来配文王,并且这种为丈夫“求佳偶”的心思还非常迫切,以至于夜里都睡不着觉。
不必怀疑文王贤妃是否有这么贤明得可笑的圣德。问题是即或有之,她自己会编成这样的诗来歌唱吗?这么私人化的深闺隐事即使事关美德似乎也不宜大肆宣扬。如果不是她编的而是别人编的,则别人怎么知道她为夫君选美人“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事情呢?宋代大儒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这首诗是别人写来颂太姒本人的。朱熹解释说:“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这样的说法比毛诗的那一套教谕理论似乎更贴近男女之情,尽管是王者与后妃之间的男女之情,但毕竟不再像毛诗序所讲的,连男女之私都没有了,完全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一套。
今有些博学之士在类似于《诗经赏析》之类的论著中则认为,如果将诗中的“君子”释为“人君”,则汉儒和宋儒的解释就有他们的道理了。不过他们引用了《论语》、《荀子》、《礼记》等文献,说明君子乃是有才德的人,并不一定是指人君,并且他们倾向于《关雎》中的所指确实并不是“人君”。 2 这些先生将这首诗的主旨往“一个公子哥在思念一个乡间姑娘”的意义上论证,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无须用那么大的力、绕那么多的弯,其实《诗经》其他诗中的“君子”一般都不是指人君:如《伐檀》中的“不稼不穑”的“彼君子”也不过“取禾三百廛”而已,相当于一个坐地收租的人,哪里是什么人君!《草虫》的“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中的“君子”怎么解也不会是人君,因为人君再有情有义且罗曼蒂克,也不可能到南山来与采薇的人儿会面。这里的君子其富贵程度甚至可能连《伐檀》中的“素餐”君子也不如。
总而言之,《诗经》开篇的《关雎》,本来是乡野之间青年男女相悦相爱的爱情表达,是平凡人生中一种真挚的情感表现;可由于文学成了少数人的教化工具,他们便觉得有必要赋予这样的诗以比较“纯正”的解释,以至于纯正到“无邪”的地步。这种文学处理正是少数人利用他们的社会分工的便利使文学脱离普通人生的明证。
少数人为了将文学变成自己的专利或专擅,不仅在文学作品的阐释和应用上作如此深奥、“正经八百”的处理,使之完全疏离广大民众的人生活动,而且在文学作品的载体和文学创作的工具上也一度存在着专利化和专擅化的处理迹象,使之成为一般人所难以把握的东西,成为余裕的人生才能够掌握和使用的东西。例如文字,传说文字是古圣仓颉奉黄帝之命而广集禽鸟兽类的足迹以及龟背纹路等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可信。汉字最早的当然是象形文字,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陶器口的外沿上,刻画着很多图象符号,被认为是汉字初期的雏形,属于距今约有六千多年的仰韶文化。这些最初的文字形体比较简单,缺少规格感,应属易于为普通人所把握的那一类。后来的甲骨文一方面字形比较固定,结构有了章法,另一方面,笔势趋于复杂,表意功能增加,离“画画”越来越远,开始脱离大多数人的使用了。据说到了周宣王时代,出了一个太史叫做籀的人,创造了形体极其复杂、结构相当繁复、书写相当困难的“籀文”,也就是大篆 3 ,将汉字书写和应用完全纳入了专业化、精英化的轨道,脱离了广大民众的普遍人生。此后的文字有六国(齐、楚、燕、韩、赵、魏)所使用的“六国古文”,形体虽然比籀文简化一些,但是结构仍然显得非常奇诡。秦国已开始使用大篆,统一中国后拟定“书同文”,因而出现了小篆,这种字体与大篆相比略有简化,但讲求结构匀称、笔意圆转、典雅舒徐,故而还是不适合民众掌握和使用,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之类。
此后,汉文字出现了隶书、魏碑、草书等等,结构定型,笔划趋简,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有识之士提倡拉丁化,以及不断简化汉字,总体趋势都是让文字这一抒情、记事、写意的工具能够早日回到最广大的民众生活当中去,回到最普遍的人生之中去。只有当文字——文学表现的基本工具为最广大的民众所熟练地掌握,文学才可能真正回归到最普通的人生。
除了文字工具向最普遍的人生回归而外,文学与人生的最密切的连接还必须有待于文学创作仪式感的消除。
文学本来是人生的审美反映,体现着一定时代、一定人群的人生精华。但文学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或专擅之后,它便充任了少数人的另一人生形式,——相对于普通人生来说是一种余裕的人生形式。这种余裕的人生形式总是力图建构和强化文学创作和文学运作的仪式感。中国古人传说,据《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是何等的动天地泣鬼神的圣事!中国人自古就有敬惜字纸的传统道德,认为“字纸乃圣人之血脉”,不可不惜。古人将读书写字看得极为神圣,同时也理解得相当浪漫,相当有吸引力,有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写诗作文则更不必说。神圣感和仪式感的结果就形成了制度,现今仍在延续的图书出版之类的制度便是这种神圣感和仪式感的结晶。图书出版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文学创作的高水准和专业化,但同时对于普遍人生与文学的直接关系则是一种有效的制约。
自古就有的文学传播途径,无论是经过古代的书肆还是经过现代的杂志社报社出版社,都是从维护文学写作的仪式感和文学运作的神圣感出发的,本质上体现为一种余裕的人生,一种使得文学与最普通的人生相疏离的社会分工体制。这种体制正如社会分工一样,保证了文学在高水准和规范化的意义上得到迅速发展,但它同时也限制了文学与普遍人生的直接联系,甚至也抹煞了很多文学创新的可能成就。文学本应是广大民众普遍人生的直接的审美表现,以传播途径为中介的分工体制长期以来严重地干扰了这样的关系。
随着电子写作和电子阅读的普及,随着这样的写作和阅读对于原有传播途径和体制的挣脱,文学有可能重新回到最普遍的人生表现上,有可能摆脱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少数人专利或专擅的局面。也许,到那时,文学事业作为少数人的一种特殊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而言,确实是一种余裕的人生形式——将可能不复存在;它仍将回复到最广大的民众所普遍掌握和普遍运用的状态,成为最普遍的人生之余裕的一种表现。
哲学家海德格尔充满诗意地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并成功地把它推向了全世界:
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
这当然是一个既具有哲学意味更具有美学意味的人生境况。如何获得这种人生境况?答案很多,途径也很多,但我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样的一个答案,是这样的一条途径:让我们的人生多一点余裕感!让那种余裕感帮助我们驱除内心的紧张、筋骨的疲劳,减轻俗事的困扰、琐务的繁杂,摆脱无谓的烦恼、无尽的凄惶,远离精神的焦虑、命运的怅惘,使人生多一些审美的乐趣,多一些自由的想象,多一些浪漫的希冀,多一些潇洒的徜徉,那样的感觉可能就是诗意地栖居。
说到这里,我愿意告诉大家我所领略过的一种情景,它所给予我的便是诗意的感动。我有一次在一个风景区散步,看到一个游客背着很大体积的、看上去很沉重的行李,一边步履匆匆地走路,一边不失时机地观赏着路边的景致。相对于其他游人,应该说他是一个很匆忙很没有余裕条件的角色,是一个负荷着沉重包袱的苦行者。他看上去是那样地疲惫,以至于我觉得他在匆匆的行走中有所张望,与其说是在欣赏美丽的景致倒不如说是在寻找栖息的草地。果然,当一片草地沿着一个缓坡突然辅展在我们的面前——不,铺展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急速地向它走去,侧身躺倒在草地上,倚着他背后庞大的行李,但是他没有像我所设想的那样急于解开行李的束缚,让自己舒畅地喘一口气,只是就那样倚着他的行李,眼睛快乐地扫视着面前的美景,一边从容地从口袋中掏出香烟,熟练地燃起,满足地吐出一口青青的烟雾,然后目视着这团烟雾升滕,升滕,升滕为飘忽的一缕,然后散开,散开,散开在山岚的吹拂之中。令我有点感动的,就是他在如此匆忙和如此负重的情形下能够为自己找出一点闲暇的空间,为自己找出一点余裕的感觉,并不失时机地享受着这种余裕感。这时候,相信他对于这行旅的理解,对于这人生的理解,就是充满诗意的,就是富有余裕的。
也许大家会觉得我刚才的描述有些文学化,这正是我的目的。对于余裕的人生的描述,就应该是文学的任务,文学是人生余裕的一个很自然也很理想的结果。
注释
1 参见http://www.china10k.com/simp/history/1/13/13c/13c08/13c0801.htm。
2 http://www.yrcc.gov.cn/lib/hhwh/2002-12-20/jj_19494424861.html.
3 http://www.sivs.chc.edu.tw/www2root/ox_view/WORD_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