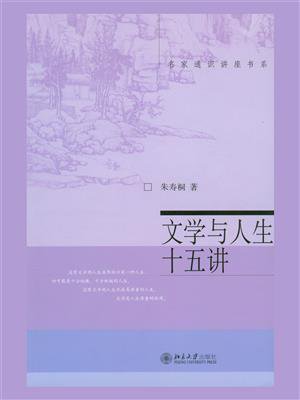第五讲
“为人生”与“为艺术”之争
对于西方的论争:想象性阐解
两个概念的自明性应用
殊途同归的理论
提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人们马上会想到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讼,即“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之间的争讼,也可以简称为“人生派”与“艺术派”之争。但随即而来的问题是,人们往往只可以准确地说出这场争讼的一方,对另一方却一直语焉不详。谁都知道这场所谓的论争初起于19世纪的欧洲,由布拉德雷、戈蒂耶、佩特、王尔德等一群唯美主义文学家发动,他们大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与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那一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可究竟谁倡导了“为人生而艺术”?谁代表“人生派”以“为人生而艺术”为盾牌抵御了来自于“艺术派”的理论挑衅?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没有具体对手的争讼类似于没有具体被告的诉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至少带有很多虚拟成分。于是,将欧洲文学史上客观存在过的这两种文学观念理解为曾经针锋相对的一场论讼,显然依据不足。
有人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一“莫须有”的争讼可以推知,作为这种“当代史”的历史还更多地带有当代人想当然的因素。“为人生而艺术”实际上是在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积之既久的理论表述,是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最一般性的阐解,属于一种具有无限开放性内涵的理论,属于一种具有多重解释性可能的包容性理论。通过这样的一番理论论争去解决文学与人生关系的问题显然并不现实,但通过对这种论争的理论辨析,通过对这种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反响的剖析,至少可以了解到,文学家们是如何思考这样的问题,以及他们作各种各样思考的依据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