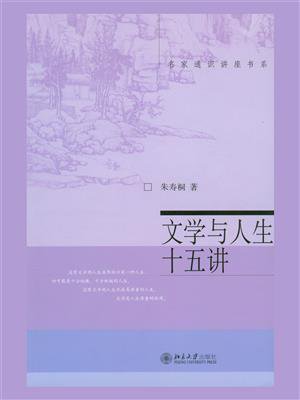一
对于西方的论争:想象性阐解
中国现代文学在“推倒”旧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在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强劲“西风”中催生,其所选择和运用的理论批评话语自然不可能属于中国传统话语系统。然而,正像一场运动不可能真正推倒具有几千年根柢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一样,一阵风潮也不可能使中国文论界尽得西方文化和文学某些概念之精髓。既然传统文学和文化之于现代中国已被证明很难被轻易“推倒”,并非废墟一堆,则西方文学观念、美学理论和文化学话语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应用,也难免带有想象的性质。这从几十年来对“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观念的接受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便能清楚地看出。
对于“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这两个西方文学观念命题,中国文学界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因为从“五四”时代起,新文学家们就对这两个命题及其相互关系津津乐道。不过,纵观这么长时间的译述和讨论,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被凸现出来:尽管新潮社、文学研究会等作家团体将“为人生的艺术”概念挪借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可他们一向缺乏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兴趣。他们似乎将一种不明就里的概念把握当作一种观念的标榜,即在尚未澄清其“所指”的前提下发挥其各种“能指”意义。
“为艺术的艺术”确实是来源于19世纪欧洲一批文学艺术家的倡导和鼓吹。法国文学家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明确地提出过“为艺术的艺术”的观点,更多叛逆精神的波德莱尔(Charle P.Baudelaire,1821—1867)则提出了“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它自己” 1 的见解,这一见解为英国批评家布拉德雷(Andrew C.Bradley,1851—1935)“为诗而诗”的观念所印证,更受到从精神到行为都趋向于反叛的王尔德(Oscar Wilde,1856—1900)的积极响应。这一派的文学观虽然在现代中国基本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但还是得到了比较系统的介绍,甚至在诸如创造社、弥洒社、浅草社、沉钟社等文学社团那里,还得到了一定程度、一定时段的标榜。 2 但就“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更加普遍、更加稳妥的文学观而言,其来路既不那么清晰,其内涵也被中国新文学家当作一种无须阐论的自明性命题加以模糊运用,以至于外延漫漶,发展到无所不包。
正如沈雁冰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所表示的,中国新文学家只是模糊地知道,“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 3 ,至于这句“标语”的主倡者是谁,则无人能够明确。按照沈雁冰当时的一些见解,这种“为人生的艺术”观似乎出自于托尔斯泰:“我自然不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但是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的唯美的文学作品……” 4 周作人最先联想到的文学家似乎是莫泊桑,他认为“为人生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例如莫泊桑的《人生》(Une Vie)之类。 5 当时又有人以为可以追朔到福楼拜,这就是表示坚信“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观点的李开中,他举例说“伟大的文学家”都注意考察人生,福楼拜“常教他的学生去实地考查车夫生活然后用文字把他描写出来”。 6 樊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观点则认为 20世纪当代法国的写实主义是“人生派”,罗曼罗兰(Romain Roeland)“是一个法国人生派最显著的人物”。 7 鲁迅则认为俄国19世纪后期的文学,即“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就是“为人生”的,代表人物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 8
或许西方文学史上确实存在过“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 9 两两对举的理论现象,直至今天,特别是在美术和诗歌领域里,国外的理论界仍在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文学艺术中的相关理论问题,认为“‘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是长期以来不断重提却难以解决的问题” 10 ;在有些理论家看来,这些有了相当长时间和理论积累的命题具备了相当经典的性质,故而用“AFLS”这样的带有约定俗成色彩的缩略语代替“为人生的艺术”(art for life’s sake)概念。 11 沈雁冰当年也曾把这两个概念只是当作“问题”,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说:“虽则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 12
不过包括沈雁冰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家,在更多的时候并非将这两种观念仅仅看作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更愿意将其夸大为两个流派的对垒,两种思潮的抗衡。周作人甚至认为这是由来已久的两派争讼:“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他想综合历史上这纷争着的两派,提出“人生的艺术派”主张。 13 傅斯年不仅认为“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他称之为“美术派”)进行过有声有色的争讼,而且判定“美术派的主张,早经失败了,现代文学上的正宗是为人生的缘故的文学”。 14 文学研究会作家无论是否明确表示倾向于“为人生的艺术”观,都确信这两派文学观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状态。庐隐虽表明自己“对于两者亦正无偏向”的态度,但对于“艺术有两种:就是人生的艺术(Arts for life's sake),和艺术的艺术(Arts for art's sake)这两者的争论,纷纷莫衷一是” 15 的情形还是深信不疑的。创造社的理论喉舌成仿吾则认为,这两种文学观念的对垒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即在一样肯定文学的人,都有人生的艺术L'art pour la vie与艺术的艺术L'art pour l'art之别”。 16
支撑他们这种想象性阐解的还有中国新文学家自己掌握的国外文学史现象。鲁迅用“为人生的艺术”概括尼古拉斯二世以来的俄罗斯文学,不过他没有机械地想象出事实上可能就并不存在的另外一派,即与之相对应的“为艺术的艺术”派。周作人在解说日本文学史时就比较注意寻求均衡的判断了:他阐述了由二叶亭从俄国文学绍介进来“人生的艺术派”,又介绍了“同二叶亭的人生的艺术派相对”的“砚友社的‘艺术的艺术派’”。 17 其实,就在周作人的同一篇文章中,砚友社也是“对于社会的问题,渐渐觉得切紧”的时代产物,属于“渐同现实生活接近”的“写实派” 18 ,将这一社团定性为“艺术的艺术派”,更多地带有想象的成分。在周作人及那时候的大多数新文学家看来,这一想象是需要的,有了它才能描述出文学史上“人生派”与“艺术派”相争持的局面,才能达到理论批评话语上的均衡。
本来,“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在西方文论史上只是两个有内涵差异的命题,是可以对举的两个概念。中国各路背景的新文学家则将它们夸张地理解成,或者说是想象成尖锐对立的两大流派。外国文艺家对此自然也不乏这种夸张的想象,而中国的新文学家显然更愿意认同这样的想象,因为他们要借助这些命题和概念表述自己的文学倾向,并让自己的文学观念在西方文学流派意义上寻找到归宿性的支撑。
1 波德莱尔:《随笔》,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2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明确认为这三个文学社团属于“为文学的文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群体,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第4—7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3 茅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50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4 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周报》第103期,1923年12月24日。
5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
6 李开中:《文学家的责任》,《文学旬刊》第8号,1921年7月20日。
7 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16),樊仲云译,《文学》第120期,1924年5月5日。
8 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4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英文为“art for life’s sake”和“art for art’s sake”,法文为“L’art pour la vie”与“L’art pour l’art”,翻译成“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比较准确,虽然通常中国文论界更愿意表述为“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
10 Hideki Nakazawa:Art Fundamentalist’s Rule of Life, Method ,No.11.Published on November 3,2001 in Japan.
11 Zan Dubin:A Failure to Communicate:Few Attend O.C.Forum on How the Arts Can Help in AIDS Crisis, Los Angeles Times(LT)-WEDNESDAY May 5,1993.
12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46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3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晨报》1920年1月8日。
14 傅斯年:《白话与文学心理的改革》,《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05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5 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
16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期。
17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85—286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8 同上,第286、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