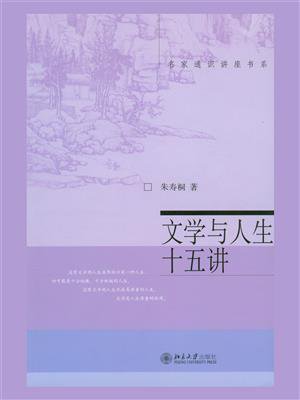三
殊途同归的理论
其实,世界上和历史上是否真正有过排斥“为人生的艺术”的所谓“为艺术的艺术”派,这是一个问题。倡导“为人生的艺术”的文艺家固然立足于文学的人生功能,而那些被理解为强调“为艺术的艺术”的文艺家何尝真正离开过人生讲论文学和艺术?他们除了在口号上的标新立异和姿态上的反叛争持之外,对文学与人生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承认并不比所谓的“人生派”消极多少。王尔德曾提出过著名的“人生对于艺术的模仿远远超过艺术对于人生的模仿”的命题;在郁达夫等人看来,古来没有一种文学是与人生没有关系的,即使那些所谓的纯艺术,也无一不是人生的范畴。这就是说,所谓的“艺术派”其实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并强化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一是认定文学艺术可以从超越于人生的角度为人生服务,作人生的先导;二是认定所有的艺术行为,哪怕是纯之又纯的艺术,都还是属于人生的现象,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特别的人生形式而已。
中国新文学家从西方文学理论中非常顺当地接受了“人生”这一概念,并将它在最广泛的文学思考中加以应用。一份代表文学研究会集体所作的声明中将“人生”理解为一切世相万物,进而确认文学对这种无边的“人生”的成像功能:“文学……他是人生的镜子。能够以慈祥和蔼的光明,把人们的一切阶级,一切国种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里面,用深沉的人道的心灵,轻轻的把一切隔阂扫除掉。” 1 将“人生”理解成融合人与人、国与国乃至于人与自然、物质与心灵的博大关系,可以说无所不包。具有宗教倾向的许地山将“人生”概念引进他的宗教思考,提出了文学创作的“三宝说”:智慧宝、人生宝、美丽宝。 2 当然也有比较狭隘地理解“人生”概念的。耿济之主张将那些以艺术本身为目的的文学排斥在人生的文学之外,认为“艺术——文学——如果只有他本身的目的,那也只是没有用的艺术——文学。人生的艺术——文学,才能算做真艺术——真文学”,将艺术行为本身无情地排拒在人生之外。这样狭隘地理解人生自然会带来结论的褊狭,于是他说“这种‘人生’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很少的”。 3
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理解应尽量避免偏激和狭窄,这也几乎是“五四”时代所谓“人生派”和“艺术派”作家的一个基本共识。周作人虽然是“人生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在对这两种艺术观念作价值评判时所秉持的态度却相当辩证。他承认“人生派”的观点也有相当的缺陷,如“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他觉得“人生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 4 文学研究会女作家庐隐作为“人生派”阵营里的一个干将,照样对于这两种观点之争表现出异常从容和十分公允的心态。她说:“创作家的作品,完全是艺术的表现。但是艺术有两种:就是人生的艺术(Art for life's sake),和艺术的艺术(Art for art's sake)这两者的争论,纷纷莫衷一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于两者亦正无偏向。” 5 作为“艺术派”代表人物的成仿吾也认为“所谓艺术的艺术派”主张亦“不必皆对”,并说“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这种争论也不是决不可以避开的”:“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而且这种争论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我们没头去斗争,则我们将永无创作之一日。” 6 他主张这两种观点的斗争应该偃旗息鼓,因为斗争不出实质性的效果,甚至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
就“五四”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界而言,“人生派”和“艺术派”确实能够在表现内在要求上达到对于文学的一般性理解,从而泯熄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之争。主张不偏不倚地对待“人生”与“艺术”之争的庐隐,就倾向于承认感情冲动这样的内心要求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创作者当时的感情的冲动,异常神秘,此时即就其本色描写出来,因感情的节调,而成一种和谐的美,这种作品,虽说是为艺术的艺术,但其价值是万不容否认的了。” 7 与此相仿佛,文学研究会作家郑振铎在谈到叶圣陶的《不快之感》时指出,这篇确实是“关于人生问题的创作”,但“他像恶草一样,蕃殖在许多略有生气的青年的心中,使他觉得凄凉,孤寂;觉得人世的恐怖,淡泊与无兴趣” 8 ,这正是与创造社的情绪表现和内心要求的传达相呼应的理论阐释。
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就“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之争,对新文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的接触”,两者调和为“人生的艺术派”。这实际上就在理论上探讨了两种艺术观殊途同归的可能性。对于这种可能性,文学研究会作家认为可以确认:“要具有艺术的美并深深刻刻的描写人生的作品”,就像许地山、冰心那样,“他们创作的时候,满含着极深挚强烈的情感要将现代人生之苦痛表现出来;或者自己有极深刻的印象与激刺,要写出来以发抒他的情感,表现他自己的苦痛”。 9
其实,如果超越于理论的论辩,从文学风格意义上作考察,也不难看出这两种文学观念殊途同归的可能性。通过厨川白村,中国新文学家特别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已见识到“人生派壮烈的主张的宣言”的文风在法国克劳特尔(Paul Claudel,1868—1955)《祝新世纪的五大颂诗》(Cinq Grandes Odes Suivl-la d' un Procleasional Pouresalues le Stecle Nouvean)中的显示:“啊,我的粗野的精神呀,使我自由,使我健全!……啊,我性急的精神呀,好如毫无智巧的大鹫!为着想做诗,我们应怎样呢?像毫无所知的大鹫般,只自营其巢!……”厨川白村形容道,这气势“像横行天空的猛鹫般,迸发其自由的生命力在诗中,破坏了向来的典型,而一本艺术的本能与直觉以行动,这种大胆的宣言,真显然的表示着人生派制作的中心动力”。 10 其实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些基本了解的读者都能产生这样的印象:被称为“为艺术的艺术”派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在《女神》中正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诗兴风采:“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凤凰涅槃》)“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天狗》)
已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即使将创造社等文学社团计算在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没有真正出现过实质性地标榜“为艺术的艺术”的派别。创造社等在一定情形下表述过对于“艺术派”观念的认同愿望,那只不过是表明他们反抗主流文坛的一种姿态,事实上差不多同时他们又对所谓“艺术派”的观点表示怀疑或加以质询。纵览创造社的文学,特别是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开辟的“自我小说”,自我的人生遭际、人生感怀和人生思考的表现无时无刻不在构成作品的主体。他们在理论上放弃自己并不曾真正坚持过的“艺术派”观念,从而归向“人生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周作人、沈雁冰等所谓“人生派”作家对“人生派”理论也并没有过多的钻研,同时也不见得有多明确的原则坚守。周作人的“人生的艺术派”命题可以说表达了他融合这两派理念的一种理想愿望。沈雁冰对于“为人生的文学”观念的倡扬,多半也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一种反对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态度。他有一篇文章题为《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所企盼的“大转变”就是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变。他觉得中国过去的文学“全然脱离人生”,他认同巴比塞的现代文学观:“巴比塞说:和现实人生脱离关系的悬空的文学,现在已经成为死的东西;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了。国内文艺的青年呀,我请你们再三地思忖巴比塞这句话!我希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人生派”文学家中确实有人指望文学能够指导人生:“文学最大的作用,在能描写现代的社会,指导现代的人生。”“文学之对于人生,与食物同。” 11 不过沈雁冰等人却没有这样考虑问题,他们只是将“人生”因素纳入文学现代化转型的考量之中。沈雁冰认为,与“人生”联系的紧密程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现代化程度,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再到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进化序列中,“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 12 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一些片面认识,如有人认为文学的有价值与否可以按新旧划分:“中国文学,非专有旧的:过去的文学,固是旧的;现代的文学,即有新的了。”而“外国文学,非专有新的:过去的文学,亦是旧的;现代的文学,乃是新的……严格讲起来,文学并无中外的国界,只有新旧的时代”。 13 对此,沈雁冰的头脑可以说格外清醒,而他清醒的原则依据便是“为人生”的观点:“西洋最好的文学其属于古代者,现代本也很少有人介绍,姑置不论;便是那属于近代的,如英国唯美派王尔德(Oscar Wilde)的‘人生装饰观’的著作,也不是篇篇可以介绍的。” 14
这就是说,沈雁冰与其说倡导了“为人生的文学”这样一种现成的理念,还不如说是注重了文学中的“人生”因素,将文学中的“人生”因素的轻重看成是文学新素质的多少。这同包括创造社作家在内的新文学家注重人生表现的思路相当接近。注重文学中的“人生”因素同倡导西方文学流派意义上的“人生派”观念是有原则区别的。正因如此,后来的沈雁冰并不承认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有过一个时候,文学研究会被目为提倡着‘为人生的艺术’。特别是在创造社成立以后,许多人把创造社看作‘艺术派’,和‘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对立。创造社当时确曾提倡过‘艺术至上主义’,而且是一种集团的活动”,但文学研究会却“并没有什么‘集团’的主张”。 15 不承认文学研究会有一种“集团”的主张,显然说不过去;但否认文学研究会倡导过“为人生的艺术”,否认文学研究会属于“人生派”,却显然有他的道理。
作为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确实强调过文学的“人生”因素,但他们只是从文学现代化的素质和基本功能出发,肯定“为人生”的文学价值,而不是自觉地将自己归结为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人生派”。严格地说,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艺术”的鼓吹者、阐释者和执行者。
1 参见《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文学研究会资料》中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
3 耿济之:《<前夜>序》,《文学研究会资料》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晨报》1920年1月8日。
5 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
6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期。
7 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
8 西谛:《杂谭(18)·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生问题》,《文学旬刊》第5号,1921年6月20日。
9 世农:《现在中国创作界的两件病》,《文学旬刊》第6号,1921年6月30日。
10 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16),樊仲云译,《文学》第120期,1924年5月5日。
11 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号。
12 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45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3 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新青年》第6卷第4号。
14 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46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5 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现代》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