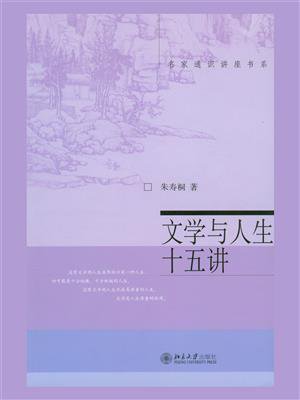一
一个轻松的话题
当人们设定一个“**与人生”的论题模型以后,“**”部分填上任何概念、任何范畴,甚至任何词语,例如“政治”、“经济”、“科学”、“哲学”、“历史”、“社会”、“家庭”、“性别”、“言论”之类,都显得非常严肃而沉重,唯独填上了“文学”、“艺术”之类,相对来说会显得轻松一些。
文学与人生的话题之所以会比其他关涉到人生的话题轻松一些,是因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原本就比较松散,说得更通俗一点:在广泛意义上,人们并不是离开了文学艺术就没有饭吃或者就吃不成饭。如果你是一个文艺家,是一个靠文学艺术吃饭的人,或许是离开了文学艺术就没有饭吃,但对于更广大的人群而言,对于人类总体而言,有文学艺术固然很好,它美化我们的人生,丰富我们的人生,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精致更优美,可如果真的没有了那些东西,相信人们照样可以活着,而且也可能活得很好。
与人生关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是社会生产,包括一切生产力因素和相应的生产关系。最直接的生产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经济、科学、技术等等,还有与生产力的培养和促进有直接关系的教育,都是社会生产所离不开的,也是总体意义上的人生所离不开的。与社会生产力构成紧密关系的是所谓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这些都与人生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然而文学艺术却离这一些都比较远。
文学艺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这样的对待使得文学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获得了相当崇高的地位。回顾一下作家曾经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拥有的巨大公信力,以及他们的组织作家协会在过去的苏联以及中国享有的巨大权力和稳固地位,就能明白文学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在任何一个从未将文学当作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度里是不可想象的。在这样一种至今仍然留有深刻痕迹的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得到了官方和舆论的高度重视,文学被同时赋予了相当了不起的价值、意义和使命,于是乎也成了与社会人生关系至为密切的东西。
当然相当多的地方并不承认至少并不强调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但身处其中的文学家有时却觉得有时候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可能不可避免。台湾小说家钟肇政像许多文学家一样看不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不过也同样和许多文学家一样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无可奈何:
文学有这样意识形态的问题吗?有的。这是我们台湾文学非常特别的地方。欧美、日本的文学并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个人还认为在文学作品或其它的艺术,意识形态并不是需要的东西,假使有,也是泡沫,终究是要破灭、消失的。唯独台湾的文学在这方面非常特殊,统独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探讨清楚,这是因为台湾过去有五十年间被殖民的历史,战后虽然说是光复了,事实上也等于被殖民的状况,跟日据时代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1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命题。一方面钟肇政为台湾文学染上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感到奇怪,感到特别,感到不可理解,另一方面他的论述又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意味,包括认为光复以后也还等于被殖民的状况。无论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至少可以说明,在一个号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并不需要的作家的嘴里,有时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难于避免,可见文学之于意识形态的联系本质上可能还相当紧密,至少是相当复杂,不是说剥离就能剥离开来的。
钟肇政认为意识形态的纠结是台湾文学的特殊现象,可能也不尽然。相比之下,更加重视文学意识形态的地方实在很多,只不过人们常常处在检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之中而已。
确实,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理论已经或正在受到文学批评界的怀疑、反思乃至谴责,有的理论家仍将文学定位在“审美意识形态” 2 的意义上,正如钱中文在所著《文学原理——发展论》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与以前理解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功能和性质的偏差,社会价值感自然无法与同政治密切联姻的社会意识形态相比,更不用说对主体提出“使命”的要求了。
将文学定位为社会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说是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使得文学在社会人生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不过从客观效果上看,对文学的发展和自身建设并非十分有益。文学艺术是人类生活中精神创造的奇葩,它的产生,它的发展,它的繁荣,都需要一定的适宜的生态条件。它需要天才,需要灵感,需要许多偶然得之的心理触动,当然还需要独特的艺术手段或技术方法的创新,这一切都不是靠社会重视所能够获得的。一定的文学艺术犹如特定的花朵,它的绚烂的绽放除了必须具有的自身条件之外,还需要它所适宜的土壤,它所适宜的气候,它所适宜的水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应有的生态。这种生态不是行政手段、人为重视乃至理论强调所能建立起来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工程,不如说是一种自然生长的过程,任何意义上的重视、提倡乃至奖励、惩戒等等都不足以对之形成相当效用的影响。
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说,它的繁荣往往都不是社会重视的结果。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的总体繁荣,很难说都是当时社会重视的结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一著名命题,揭示出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文学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也就是说,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很可能是在社会一般发展比较低迷的时候。“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 3 这就是说,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有时是任何外在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无法决定乃至左右的。
就文学创作的个体经验而言,伟大作家和诗人的不朽作品也都不是社会重视或行政扶持的结果。文学的历史有时恰好提供了反面的教训:过分的行政扶持或过于集中的社会重视,往往不利于巨大文学成就的形成,甚至对文学发展有害。外国的所谓“桂冠诗人”,中国历史上相当多的宫廷诗人,其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常常是少之又少,浅而且浅;哪怕是非常杰出的文学家,一旦“桂冠诗人”或宫廷诗人的“黄袍加身”,往往就难以创作出与其才华相匹的作品来,曾经有过这种经历的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现代中国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一段时间内,文学被当作社会意识形态,当作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求几乎每个人都能写诗,要求村村都有文艺创作、大演大唱,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当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之后,文学就必然会担负起自己所无法负担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这种“过多负重”现象对于文学的正常发展和繁荣并不有利。在素来重视意识形态的社会体制里,文学的宣传教化作用一向都得到强化,结果却往往不能因此留下传之后世的杰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应该说有着比较深刻的教训。有时候,文学的意识形态化被强调到极点,文学不仅为政治服务,还要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求的那样,“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是在特定的革命时代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的特定立场所提出的要求,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则被视为文学艺术应有的素质,甚至是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具备的品质,于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政治工具化倾向特别严重,所产生的作品往往更多地体现着历史的认识价值。
我要说的是,我们以前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重视意识形态的共产党才这么“功利”地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工具性,其实只要“政治”需要,任何“政治”家都会对文学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上个世纪60年代,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了《当前文艺政策》,也明确提出提倡“积极推进三民主义新文艺建设”,“促进文艺与武艺合一,军中与社会一家,以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扩大文艺的战斗力量,适应国防民生的需要”。要求文艺家“强化文艺的敌情观念,坚持文艺的反共立场”,“汇合自由世界光明正大的文艺力量,力挽偏激、淫靡、颓废的文艺逆流,导向三民主义新文艺的主流”,如此等等。 4 其结果,固然是造成了相当的声势,但以此为指导思想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有多少被人提起或是被人记起?
当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被夸大以后,当文学之于社会和政治所可能负担的责任增大以后,文学相应的厄运也就可能增多。历史的教训已经作了这样的证明,政治家完全可以凭借他的判断认定某一部作品犯了滔天的错误,进而追究作者甚至整个文艺界的责任。毛泽东当年要发动某种政治清算运动,往往就先从读文学作品开始,他能够从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中看出了某种“反党”的意味,并不无嘲讽地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
中国20世纪中期的政治运动,常常总是从文学批判着手。建国初期,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以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文学学术著作《红楼梦研究》打响了开场之锣;批判“胡风集团”的斗争与“镇反运动”紧相呼应,文艺界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又以对《洞箫横吹》、《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的批判,以及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为前奏和内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署名“三家村”的几则小品文的声讨拉开序幕。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那个时代社会过分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过分重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关。当文学的作用在这种观念下被夸大以后,一般来说给文学带来好处的可能不是太大。而且,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是高度精细的精神创造活动,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学创作是卓越的灵感、特异的天才在一定的情感世界里自由呼吸、自然发生的结果;寂寞应是文学的常态,孤独是文学的伴侣,普遍的社会重视、热闹的群体关注,往往并不利于这种高层次的文学作品的出炉。
文学艺术本质上是人生的余裕的体现,其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应该颇为松散。特别是在不寻常的年代,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与社会人生之间关系的紧密,往往并不明智。鲁迅就曾对这个问题作了形象的解剖。他1927年4月8日到黄埔军校去演讲,语出惊人,认为在革命的时代,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这篇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鲁迅批评当时的革命文学家:“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鲁迅对此不能同意,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言下之意,即是认定文学其实应该与社会的倡导拉开一定的距离,其之于革命的关系也不见得就那么紧密。据此,他认为在那个时代“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他自己表示倒是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而不是文学的声音,因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鲁迅的讲演是面对黄埔军官学校的广大学生,面对即将肩负起中国国民革命责任的军官们而发的,语气中对于革命军人含有更多的激励,同时对于文学作用的论述也相应地带有某种揶揄的成分。但是,鲁迅所表达的意思相当准确。文学之于社会人生,并不像我们日常宣传中,或是文学教授开始一堂文学课所讲绪论中强调的那么重要,那么严肃,它应是人生沃土上自然生长的一种奇葩,而不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须臾不可离之的果食。
既然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本应如此松散,文学与人生就应该属于比较轻松的话题。人生的范围很大。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中,对于人生的思考就难免出现分工:有的人重点考虑人生的沉重话题,有的人重点考虑人生的轻松话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他们的思考自然偏重于沉重的方面,文学艺术家的思考相比之下就偏重于轻松的方面。只不过,有很多文学家不愿意、不甘心甚至不懂得轻松地思考文学与人生的话题,有些杰出的文学家则处于特殊的历史位势,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无法轻松地进入这样的话题,譬如鲁迅。比较擅长于以轻松的姿态进入文学话题的现代文学家,当推周作人和林语堂。周作人留给现代文坛的话题很多,有时他也检讨自己曾经作为一个道德家将文学推向了严肃。这位提出“人的文学”概念的文学家在《自己的园地》自序之二中说:
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
但是他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草木虫鱼、听雨品茶之类的所谓“闲适人生”的书写。林语堂善于从“悠闲”、“艺术”的角度思考人生和看待人生,他著有一书题为《生活的艺术》,在这本书里,有一篇叫《悠闲的重要》的文章,特别强调“悠闲的重要”:“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空闲的艺术。”
并不是说我们谈论文学的时候就应该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闲适或者悠闲,而是说作为文学家当以文学人定位的时候,不妨这样说一些闲适的或悠闲的话。但文学家也是人,是一种具有普通身份的社会人,特别是在文学家作为社会人应该担负起某种社会使命和责任的时候,如果他依然凭借着文学的余裕性而故作悠闲,那就可能被理解为一种麻木甚至冷酷。鲁迅那么坚定地相信文学是“不中用的”,但同时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利用文学向专制的统治,向愚弱的国民,向种种腐败的社会相进行严肃的斗争。
我们所谈论的“文学与人生”的话题,是在平常年景和日常状态下展开的,它要求我们立在文学的基点上,本着人生常态和文学常态发言。这时候我们理应基本上把它当作一个轻松的话题。
文学话题的沉重让我们长期以来养成了受压抑的习惯。现在终于有机会让我们摆脱这种额外的沉重,从而在轻松的气氛中说说文学,说说人生,说说一些与文学和人生相关的事情。
1 钟肇政:《台湾文学十讲》,第15页,台湾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
2 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第11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
4 参见尹雪曼等著:《中华民国文艺史》,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