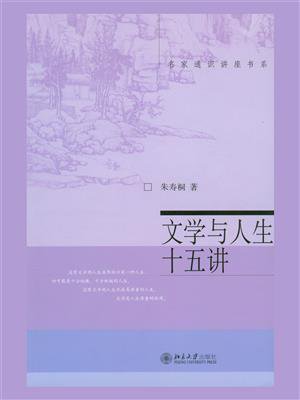二
一个严肃的话题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与人生这两个关键词的组合也并不完全轻松,其间也包含着相当严肃的理论成分。这样说既不是玩文字游戏,也不是为了证明法朗士的观点:“在文学的问题上没有一条意见是不能很容易地被一条跟它恰恰相反的意见反对掉的。” 1 理论的证明将符合文学与人生的历史实际,它本质上是一个既轻松又不轻松、轻松而严肃的话题。
让我们再从虽不沉重但又相当严肃的意义上认知这一话题。
尽管我在以下的论述中会一直坚持文学是人生的余裕的观点,主张在比较轻松的心态下讲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不提倡给文学赋予太多的使命和责任,但绝不会同意那种将文学当作某种玩物的观点和态度。避开历史上曾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消解文学严肃性的言论、观念不说,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让“玩文学”的口号几成时髦,似乎人生要得潇洒就需将文学当作把玩的对象,否则就不够倜傥。这样的观点如果不属于病态的玩世不恭,便是错误地理解了文学话题的轻松。不沉重,轻松,并不意味着玩世不恭,轻松的话题并不都是玩的对象,一场精彩的球赛,一台美轮美奂的音乐会,一次遥远的国际旅行,甚至是一番令人神往的爱情,作为话题讲论起来都可能很轻松,可我们能理解成那是一种毫无作为的“玩”吗?
在总体上看,文学虽然是人生活动余裕的产物,但一经产生,其对于人生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了。人生的许多经验都能证明,人们所作的余裕性很强的选择,经过一定程序的人生运作,便可能迅速成为人们再也无法离开的人生需要,甚至在许多情形下成为人生的必然选择。一个小女生也许是在学习压力不大、经济条件不差的前提下爱上了音乐,买上了Walkman,还有一大摞的CD盘,经过一段时间的习惯,她有可能变成了一个音乐迷,一个带着随身听吃饭也听,走路也听,睡觉也听,甚至做作业也听的音乐迷,从此她可能丢下任何别的东西,哪怕是学习,可就是无法丢下音乐。这样的现象即使有当然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可以用来模拟这样的道理:文学作为人生余裕的产物,经过人类相当一段时间的“习惯”之后,会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我们无法丢弃且也不可能丢弃的对象。
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在不断地走向文明,人类走向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将人生的物质需要逐步降低,而将精神需求的地位逐步抬高。文学作为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精品,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精华,是人类思维的神奇的结晶。一经产生并且进入到人类精神享受活动的较高层次,就成为人生活动的一个必然成分,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当然因素。于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虽然比较松散,却又并非可以随便脱钩的,文学与人生的话题虽然比较轻松,却又并不是可讲可不讲、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的玩意儿。
中外文学史上的理论家和作家们对于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人生功用问题有过旷日持久的探讨,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争辩和异常激烈的交锋。有的认为文学对于社会人生具有莫大的功用,有的则认为基本上没什么用处。不过倘若我们可以避开那些争辩与交锋,根据人类文明史的基本事实以及个人精神生活的个体体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则无论争辩或交锋的哪一方面可能都不会有太多的意见:没有文学的人生虽然依旧是一种人生,但可能是十分枯燥、十分粗糙的人生。没有文学的人生不是高质量的人生。文学是人生质量的体现。
启蒙文学家、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文学家总愿意从“新民”或宣传革命、鼓动革命的功利立场理解文学,定位文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梁启超、严复等就是这样看待文学的。他们认为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开化”,“往往得小说之助”很多 2 ,因此,“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为什么改良这么多东西都必须依靠小说和文学的改良呢?梁启超是这样总结的:“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3
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也是如此,当时革命文学社团创造社曾受日本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推出著名的“组织生活”论,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有一些唯美主义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念,同样是创造社作家的郁达夫就曾经坦言,文学艺术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如果从对人生有用的角度来考虑,那么想到的就不应该是文学,而是稻粱之类。不过,即使是彻底的唯美主义者也并不否认文学艺术对于提升人生的应有作用。唯美主义文学大师王尔德就曾提出,文学艺术固然不能“为”人生社会服务,不能以人生社会的功利性为目的,但艺术可以为人生提供可资摹仿的模板:“生活对于艺术的摹仿远远多过艺术对于生活的摹仿。” 4 既然艺术可以供生活来摹仿,其对于人生的提升意义自是不言而喻。于是,文学艺术是提升人生质量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偏激的革命文学家和偏执的唯美主义者在文学艺术的人生功用问题上即使都各执一词,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统一到对于文学与人生的基本认识上来:文学对于人生是有相当意义的,这种意义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以不够严肃的态度和语式谈论这样一个话题。
文学能够以一种高贵、典雅的质地服务于人生,服务于社会、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利益。在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看来,文学艺术对于人生的意义虽然不至于像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许多革命文学家所强调的那样重大而关键,虽然在相当的情形下“艺术利益本身,不得不让位于对人类更重要的别的利益”,艺术只能“高贵地为这些利益服务,做它们的喉舌”,“可是,它毫不因此而终止其为艺术,却只是获得了新的特质”。 5 这种获得了新质的艺术和文学对于人类的意义就变得不是可有可无的了:“社会的最崇高、最神圣的利益,就是那同等遍及于其各成员的社会本身的福祉。引向这福祉的道路便是自觉,而艺术能促进自觉,并不下于科学。” 6
艺术作品本质上是人类思维开发的结晶,是人类精神创造的成果,它的基本特性、基本功能和基本价值都与人的思维活动密切相联。文学是艺术的一种,是以语言为载体的艺术。同时,由于文学载体——语言文字自身的符号性与其他所有艺术的物质性载体——如雕塑的青铜、石膏、木头,绘画的颜料、有相当质地要求的纸张,音乐的动感极强的旋律等等——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学在艺术中是与人的思维联系最为直接,其代表的艺术品性也最为典型的一个种类。“语言符号拥有着比任何物质材料或视听觉信号更为健全、更为强盛的情绪表现力”,由此“可见文学之于其它艺术所处的优势”。 7 因此,当我们像别林斯基那样谈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时,有充分的理由把文学当作其中最典型的艺术甚至是最本质化的艺术来对待。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创造物,当它作为艺术作品出世以后,在一定意义上就获得了人类文化形态和文明资源的意义。人类文化和文明是总体人生观念和价值中非常严肃的课题,自然文学也就成了人生中的一个严肃的话题。何况,文学中有闲情逸致,有风花雪月,可也有激动人心的人生飞扬,有慷慨悲烈的生命豪壮。许多伟大的仁人志士不仅在其人生的开始阶段通过文学接受了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的精神滋养,而且也以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高尚,甚至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重铸了新的文学形象,重谱了新的文学乐章。以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为例,许多英雄都曾从古典文学和古典戏曲中接触到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领略了他们的品德和精神,以此陶冶自己的灵魂,磨砺自己的斗志。苏联文学中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高尔基的一系列作品,以神采飞扬的英雄主义气概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其中的人物常常成为他们的人生偶像。诸如《青春之歌》、《红岩》乃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样板戏”等,都曾以文学的力量敲击过不止一代中国人的心扉,让他们感动,让他们耳熟能详。其他如林纾的翻译小说,对鲁迅那时代的读书人走上文学启蒙的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鲁迅等“五四”新文学家的创作又影响了20年代以后走上文坛、走上社会的一代新人,这从巴金的《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家》的原题是《激流》,那就是指“五四”发动的时代的激流;小说中的人物觉慧就是一个在《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影响下迅速觉醒的青年,他们秘密办报的行为,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和效仿。
对于上述文学作品所产生影响的社会历史评价和价值评价可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对人的精神、性格的影响到底是否都体现在积极方面,可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历史无可避讳,这些作品在相应的时代对于一代人的人格铸成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容低估的。
既然文学影响人的精神,参与人的灵魂的构筑,作用于人的人格的养成,我们怎么可能以一种完全轻松的态度去谈论它?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话题,需要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去思考、去对待。
1 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7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光绪二十三年10月16日天津《国闻报》。
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卷第1期。
4 王尔德:《谎言的衰朽》,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5 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38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6 同上,第390页。
7 参见拙著《酒神的灵光》,第28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