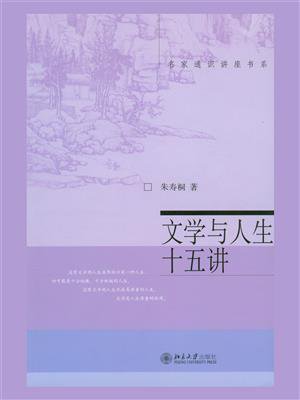三
关于话题的展开
“文学与人生”是一个严肃而轻松的话题,它与日常人生的联系相当广泛,因而许多人都愿意探讨。许多文学巨匠对这一话题都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并且也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思想成果和学术成果。又因为这一话题包含的内容相当庞杂,包含的层次相当丰富,它的展开也就可以有多种方式。我对这一话题的展开立足于学理层面,试图通过对某些文学理论、人生观念乃至某些社会心理的探讨,解析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辨清文学的现象与人生的现象之间种种的差异与联系,从而在这种较为广泛和复杂的关系与联系中得出较为新颖同时也比较符合文学实际与人生实际的理论观念。
“文学与人生”话题所寓含的内容的广泛性是可以想象的:文学所涉及的一切都是人生的形态,人生所凸显的一切也几乎都是文学的对象。于是,几乎一切与社会人生相关的各种现象都可以在这一话题中得到反映。至少伟大的文学家康拉德就是这样理解的。这位英国小说家在1920年编过一部叫做《文学与人生札记》的文集,第一部分固然讲的是文学,论述了亨利·詹姆斯、莫泊桑、都德、法朗士、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业绩;第二部分标题为“人生”,所讲述的虽然据他自己说就是“真挚的感情”,其实涉及到文学的东西极少,与第一部分的“文学”不构成起码的有机联系,更多的意义上只是社会政治批判和文化批评的文章,有些甚至是社会时评,包括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关注。这些文章固然留驻着康拉德可羡的智慧、敏感和才情,但如果读者指望它像它的题目所暗示的那样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有什么理论贡献,一定会失望而返。如果人们关心这一话题,一定会对类似的文章题目或书名较为敏感,而通过康拉德这本书的例子可以说明,人们即使没有展开这一话题的意思,也无妨使用类似的题目和书名。可见这一话题包含的内容何其广泛。
一般来说,中国人处理这样的题目比较审慎。如果以这样的题目加给自己的文章或书,总是会从这两者的关系进入话题。中国新文学开创之初,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都打出了文学“为人生”的旗号,偶尔也直接切入“文学与人生”这一专题进行理论探讨。沈雁冰就写过《文学与人生》的专题文章。较早做这项工作的还有现代诗人徐志摩,他在那时候发表过一篇英文文章,题目是“艺术与人生”,刊载于《创造季刊》第2卷第1号 1 。这篇文章确实是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的角度切入的,理论显得比较浅泛,主要强调文学与人生的紧密联系。不过难得的是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对于现实的人生和文学情形的反思和批判,认为“我们现在没有艺术,是因为我们没有象样的人生”,“人生的贫乏必然导致艺术的贫乏”。徐志摩觉得丰富的像样的人生应该充满着爱。这样的观念对于解答人生问题也许显得有些幼稚,但对于文学来说却显得非常中肯。
作为杰出的美学家和文艺心理学家,朱光潜撰写过《文学与人生》,其话题展开的角度也在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可以想象他的观念会比许多作家和诗人的感受深刻得多,也准确得多。有些说法既通俗易懂又十分精辟,但有时也存在着些偏颇。关键是他的话题展开方式过于偏重于文学方面,谈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着重于文学层面,对人生的分析相对薄弱,即使对人生有所涉及,也基本上是从文学和美学出发去谈论。他认为文学与其他艺术一样,“作者对于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观感,而这种观感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表现;这观感与表现即内容与形式,必须打成一片,融合无间,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和谐的整体,能使观者由玩索而生欣喜。达到这种境界,作品才算是‘美’”。看得出来,他的立足点就是文学,就是处在创作过程中的文学,他在这里与其说是谈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毋宁说是在讲述文学的创作方法论。
由于这位东方美学大师的立足点在于文学,他在论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时就更多地显示出文学家的拘谨甚至是文学家的想当然。他认为既然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而语言人人能通,则“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这样的推论在逻辑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作为一种理论判断就显得有些匆忙。文学与读书人的人生可能关系最为密切,与那些不读书的人的关系是否就最为密切呢?不读书的人可能通过音乐、通过戏剧形式接触艺术的机会更多,也更普遍,他们的人生恐怕就不能说与文学最为密切。重要的是,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读书人长期以来都是少数人,少数人的生活终究不能取代甚至代表一般的人生。
朱光潜为了证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文学起源和人类文明的源头上寻找依据,说:“远在文字未产生以前,人类就有语言,有了语言就有文学,文学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种艺术。在原始民族中,人人都喜欢唱歌,都喜欢讲故事,都喜欢戏拟人物的动作和姿态。这就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的起源。”这还是典型的文学本位观念的体现,而远不是一种符合历史情形的判断。也许在语言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文学还没有机会产生的时候,属于原始巫术的舞蹈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文学是不是最原始最普遍的艺术确实很难说。何况,作为文学形态的小说、戏剧是中古以后至近古时代才发展起来的,将它们直接与原始民族的生活联系起来,依据很难充分。
偏向于从文学的角度讲论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著作在同题作品中应不占少数。李辰东的《文学与生活》 2 也是这样的书。该书作为教材还出版了第一至二辑,目的似乎是在弥补“我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只重西洋文学的吸收,新文学的创造,似未注意作家人格的培养”这一缺陷。该书内容相当通俗,切入的子题目也比较容易引人入胜,如“理想、生活与文学”,“江郎为什么才尽”,“什么叫美感”之类;有些材料运用得也很机巧而充分,如在讲美感的时候,运用古代诗话的相关材料,将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推敲过程,特别是“绿”先后曾考虑用“到”、“过”、“入”、“满”等等加以置换,也介绍过福楼拜的“一字”理论(one word theory),贾岛、韩愈的“推”“敲”故事,等等,这些材料确实适合于文学与人生的话题。
作为通俗性讲话或教材,这本书内容相当广泛,尤其是第二辑,涉及到什么叫文学,意识与灵感,意识与想象,意识与美感,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经济、政治、历史等等,可以说将文学与人生的方方面面都细密地扫视一过。但编排得过于琐碎,各个子题目之间缺少必要的逻辑联系,文学史实和文学家逸闻轶事的举例也显得比较随便,理论含量较浅,这些缺陷决定了它还是没有能很好地完成这一话题的讨论。
讲论这一话题形成比较大影响的当推吴宓的《文学与人生》。吴宓此书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清华开设的选修课讲义,1993年他的学生根据其讲稿翻译整理出版。吴宓的这门课内容比较充实,按每周两小时计,准备了一整年的授课笔记。他在讲论文学与人生课题时务求理论的深入,追求内容的学理化,并且不是偏重于文学一端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因此很见深度和力度。随之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他热衷于从白璧德人文主义立场阐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对于白璧德主义的兴趣往往溢出了文学与人生的话题,使得讲述的内容常常显得十分游离。据他在本书的课程说明中介绍:“本学程研究人生与文学之精义,及二者间之关系。以诗与哲理二方面为主。然亦讨论政治、道德、艺术、宗教中之重要问题。”事实上他所“兼及”讨论的东西每每喧宾夺主地冲淡了文学与人生的主题。
后面我们有机会就这一本专书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解读,这对于我们在学理层面思考“文学与人生”的问题很有帮助。
总之,“文学与人生”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话题,人们探讨的兴趣从来没有减弱过。上个世纪30年代柳无忌等曾在天津创办过《人生与文学》月刊,至今中国大陆仍在出版一本杂志题为《文学与人生》,南京大学、南京审计学院等多年来都曾将“文学与人生”列为大学生素质教育选修课程,教育部还将这门课程列入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课程规划之中。浙江大学也开设有这样的课程,作为这门课的教材,黄健、王东莉等也写出了《文学与人生》 3 ,该书的亮点是将文学审美与人生的审美,以及人的创造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讲述,自然难度很大,但颇能反映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当代性要求。不过黄健等在著作此书时似乎将吴宓的同题著作过于奉若神明,我却以为不必,原因我将在下面对吴宓专书的解读中道出。
另还有一些近题书籍,如张道一先生主编的《艺术与人生》和蒋孔阳先生所著《文艺与人生》 4 等,都是这一论题的展开所必须参考的重要著述。
台湾的许多大学,如“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逢甲大学、静宜大学、“国立新竹师范学院”、“国立台北师范学院”、中国科技学院等等,都将“文学与人生”列为通识课程。澳门科技大学为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也开始规划这一课程。这些都是相当有见地的课程设置。台湾彭镜禧教授还策划主持过“洪敏隆先生人文纪念讲座”的“文学与人生”专题,作为这一专题的成果,出版过《文学与人生》一书,由方瑜、陈幸蕙、张大春、彭镜禧分别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与人生的关系发表主题演讲稿,由财团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于2000年5月出版,虽然不能算专著,更不能称教材,但已是台湾在这一课题上进行通识教育的很好的纪念。
“文学与人生”这一话题寓含的理论相当深刻,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许多文学家和理论家都曾对这一话题用过功夫,从而有了相当的积累,但仍然留有许多供我们探讨和讲论的空间,包括理论的空间和材料的空间。我们可以吸取前人的经验,开发和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较为系统、较为深入同时又较为切近地谈论文学与人生的话题。
1 这篇文章其实是徐志摩被梁实秋等邀请到清华文学社讲演的讲稿,见《梁实秋怀人丛录》,第22—2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2 台湾水牛出版社1971年版。
3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