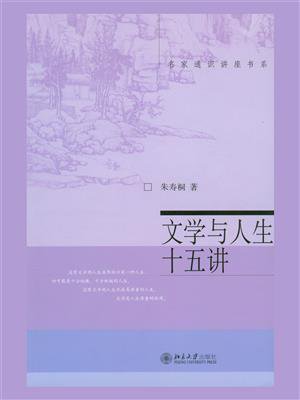一
融进自我的人生体认
吴宓在本书中所体现出来的理论个性与风格,最突出的是时时融进自我的人生体认。这是展开“文学与人生”话题时最适当也最为难能的态度。
“文学与人生”是一个人人都可能有心得的话题,因为每个人都处在人生过程之中,每个人都会在人生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接触文学,以人生的体认去体味文学,或者以文学的感悟去理解人生。也正因如此,学问家对于这一话题的介入就显得比较危险,因为他们不甘心于在人生体认的肤浅意义上讲论这一看起来比较通俗的题目,而希望端起一定的理论架势,或者搬出一种哲学理念高屋建瓴地展开论述,将这一本来与具体的人生和生命的体悟联系得比较紧密的话题谈论得异常玄奥而深妙。吴宓的《文学与人生》粗看起来就是这样一部专论性著作,里面不仅充满着概念、术语、外来词语、哲学范畴、逻辑推演公式等等,而且引进了白璧德相对深奥同时也相对保守的经典学术,从而体现出玄妙乃至深秘的学术风貌。
但是,热心整理和翻译吴宓这部书稿的吴门高足如王岷源等就不是这样看,他们从先生的这部讲稿中不仅得到了学理的教诲、思想的启迪,而且也感受到人格的熏陶、气质的感染。他们是怀着那样迷醉的情绪说起吴宓对这一课题的讲演,在诸多学术的收获中津津乐道着灵魂的吸引和情感的惑动。为什么吴宓的专书和他的讲课在表层效果上有如此大的差异?难道仅仅是因为吴宓先生擅长辞令,讲演生动?细读讲稿原文,密察字里行间,原因更主要在于,吴宓在讲论“文学与人生”这一话题时,经常与自己身上固有的以及从白璧德教授那里承传过来的学究气展开砥砺;在这样一个很容易滑向形而上的理念世界的论题上,倾注了他自己对于文学,对于人生,对于学术的多重热忱,这种热忱使得这部学术专论不单闪烁着理性的智光,还常常流溢出作者人生体验的灵性和生命搏动的汁液。
这位一向谨严持重的现代人文主义者向读者和听众推出“文学与人生”这一话题的时候,不仅毫不讳言这一点,而且公开标榜自己对这一话题投入的兴趣和热忱:我的工作和我的主要兴趣:文学与人生。 1 凭着这样的兴趣切入自己的工作,包括切入“文学与人生”的话题,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笼罩在这一论题之上的严肃与拘谨,将体验的鲜活与理性的萃思统一起来。把握这样的学术状态不仅使我们有可能准确地把握《文学与人生》学术风格,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于这部书中的一些令人迷惑的学术“矛盾”作出合理的阐释。
吴宓是“白璧德主义”的信徒,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导师正是这位当时名噪一时的学术大师,他在编辑《学衡》杂志时,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推介也最为用力。与有意同白璧德主义拉开一定距离的另一位哈佛留学生林语堂不一样,吴宓很少对“白璧德主义”采取商榷、规避甚至是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学术命题上,例如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对卢梭的声讨,对理性的推崇,对情感的贬抑,对儒学传统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白璧德的足迹。然而在《文学与人生》中,这样的亦步亦趋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
他曾正式地提出这样的命题:“人生与文学——必须自内发出;又必须以自我为征验。” 2 这样的命题如果由郁达夫、郭沫若这样的倡导“自我表现”论的作家提出,我们完全可以处之泰然;可由一个在价值观念上不同意“自我表现”说,执意反对浪漫主义、反对卢梭感伤主义的人文主义者阐述出来,则不由人不感到惊讶。在吴宓那里,这种命题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对于人文主义观念操守的某种悖反。造成这种悖反的原因显然是,他的人文主义观念操守与他的人生体悟和生命体验之间存在着龃龉。人文主义让他坚持反对一切浪漫化的倾向,反对自我情感的倚重,他曾把“我”字宣布为敌人,因为这个“我”可能成为所有其他人的暴君;他认为利己主义与人道主义同样错误。 3 但在人生体验的意义上关注文学、解析文学的热忱又使他不得不频频回顾自我的体验,“以自我为征验”。他对于文学与人生的思考有时候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的学术意识中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人文主义反对文学的浪漫化和情感性的趋势,主张“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 4 ,在相对意义上推崇古典主义文学精神。人文主义者赞赏古典主义所保持的对于“自然,模仿,适度和节制”的浓厚兴趣,虽然吴宓最崇敬的白璧德强调,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并不是模仿事物原来的样子,而是模仿它们应有的样子,因此这种模仿乃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5 。白璧德确实信奉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思想表述中常常显露出服膺古代圣贤的倾向,但从来反对拟古主义和泥古主义,在《论创作》一书中提倡“一种包容着真诚创造的模仿类型”,这被认为是对亚里士多德“不是根据事物的样子而是根据它应有的样子作模仿”的法则的发展 6 。但是在“创造”与“模仿”之间,他无疑倾向于模仿。另一位白璧德人文主义的信徒梁实秋曾对模仿理论作过整体性的阐释和推介。然而吴宓对于这一古典主义的同时也是人文主义的命题持明显的保留态度。他批评英国新古典主义批评家蒲柏所写的致蒙塔古夫人的情书,认为那是矫揉造作的,“摹仿”的,文字堆筑的,不真诚的,不令人愉快的文本。 7 有趣的是,同是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他们都引述了蒲柏,可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中将蒲柏(Pope)的批评理论当作提倡模仿自然、内心节制的经典文论,吴宓则将蒲柏的文学和理论现象当作他自己否定模仿观念、克服不真诚心理的一个对象。究竟什么使吴宓偏离了人文主义的思想轨道,甚至在一些关键性的命题上站到了人文主义立场的反面?仍然是自己人生体验的介入。在“文学与人生”这一课题的思考中,吴宓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乃至人生偏爱掺进了人文主义的理论追索,有时难免出现这样的情形。吴宓自己坦率地承认:“宓个人之才性,较近于Thackeray,亦以Thackeray为more Reflective and more Modern也。” 8 在主办《学衡》的时候他曾热衷于对萨克雷的翻译。原来他的本质属性倾向于睿思的和现代的方面,在走出人文主义理论语境的时候,他自然会偏向于创造的和真率的一路。
从作者这个角度谈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自然会涉及到所写作品与作者人生经历和情感状态的关系。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的信奉者,吴宓不会同意法朗士的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观点,文学写作的目的也不总是作者的自我表现,“因此,在所谓‘文学研究’上多费功夫是愚蠢的”。这里的“文学研究”是指从文学文本中寻求作者的传记性研究。作为这种“文学研究”例证的有巴特勒对《奥德赛》的作者是女性的推论,有《石头记索引》和《红楼梦考证》之类,与此同时他还提到了“我的《忏情诗》与陈慎言之《虚无夫人》”,认为这些都并不是自己的完全的呈现。 9 诚然,他的《忏情诗》不等于他的自叙传或人生忏悔录,即使他所批评的那些“文学研究”也不可能都言之凿凿地将文学作品与作者自我的行径、故事和心情完全等同起来。不过吴宓在论述到文学与人生的这种关系时,非常自然地将自己的创作体验和作品实际融了进去。他或许是借此推介自己的诗作,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他研究“文学与人生”这一课题时的那种不避自我体验的心态。
吴宓将人生体验融进他的人文主义思索和“文学与人生”的观念探讨,使得他在论述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时都能保持着生命感受的真切与鲜活。文学表现与人生体验中共有的悲剧与喜剧问题,是“文学与人生”话题很容易涉及到的内容。吴宓也这样认为:“泪与笑:人生之要素,文学之考验。”因而,悲剧与喜剧是文学与人生关系的一种凸显。
由亚里士多德等古代贤哲开创的关于悲剧和喜剧论辩的传统常常与严肃而古奥的理论命题如“卡塔西斯”(Katharsis)等联在一起。吴宓在这本书中探讨到这一问题时却没有这种理论沉陷现象,他引用英国散文家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书信集来这样解说悲剧与喜剧——人生的体悟远远多于理论的玄奥:我常说,也更常这样想,对那些惯用头脑思想的人说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喜剧,对那些惯用感觉的人则是一个悲剧——这也解答了德谟克利特为何而笑,赫拉克利特为何而哭。由此,他解释悲剧是激情与感情(emotion)的结果,偏于主观;而喜剧是智力与理性的结晶,偏于客观。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小说家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这样给小说定性的原因:“喜剧是充满了思想的欢笑。” 10
吴宓显然并不喜欢悲剧,虽然他有时不得不对悲剧给予很高的价值确认,认为悲剧必须是“宇宙性的”。不过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并不欣赏情感,特别是激情。然而人文主义所认同的古典主义,其经典作品往往偏重于悲剧,而且古典主义悲剧并非激情的展示或感情的无节制的流露,更多情形下充满着理性。这样的文学史实足以让吴宓对于悲剧的理解和判断陷入理论的困境。这样的理论尴尬仍然来自于作者赖以发挥的理念同自己的人生体认之间的差异性。作为一个恪守理性立场的人文主义信奉者,他愿意克制住冷僻而孤独的情感,人生的希冀带着他趋近生命的戏剧形态。他深信美国女诗人维尔库科斯(Ella W.Wilcox)所说“笑,世界跟你一起笑;哭,你只好一个人去哭”的道理 11 ,在生命的过程中,他愿意与世界一起微笑,愿意认同喜剧,为了这样的认同他可以牺牲对悲剧美的确认,甚至对古典主义悲剧精神的承认。他的真实的心态其实就是想与世界一起微笑,这是他的一种生命要求。这样的要求超越了悲剧、喜剧的审美判断,于是他可以在认同喜剧感的同时贬低讽刺文学和讽刺作品,例如拜伦的《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等,认为这样的讽刺文学属于文学之非常低级的形式。
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吴宓似乎已经让自己相信,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与文学和文学理论比较起来,人生毕竟重要得多,尤其是自我的人生。
沿着这样的话题探讨下去,很容易发现吴宓再将文学的谈论引向人生的教诲——这是这一话题的展开中最容易犯的毛病。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吴宓的《文学与人生》中包含的人文“礼教”的歧误。
1 吴宓:《文学与人生》,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同上书,第25页。
3 同上书,第113页。
4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新月月刊》第1卷第1期,第20页。
5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p.17,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
6 Stephen C.Brennan,Stephen R.Yarbrough: Irving Babbitt ,p.90,p.95,Twayne Pub-lishers,1987.
7 吴宓:《文学与人生》,第54页。
8 同上书,第58页。
9 同上书,第18页。
10 同上书,第26页。
11 同上书,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