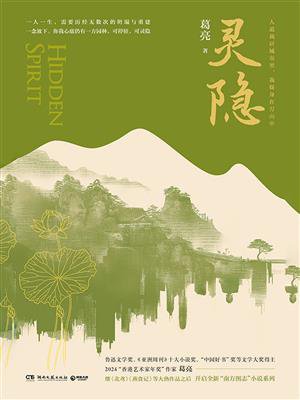一
警员走进来时,看到连粤名正给牛排浇上黑椒汁。他看到警员,并无意外,仍执刀叉慢慢切下一块肉,送到嘴里。
连粤名自认是个老饕。按常理,这刁钻的口味,多半是出自训练,而他却是浑然天成。他自幼在北角住着,那里先住着上海人,后来是闽南人排闼而来,便称为“小福建”。
他们住过的地方,叫作“春秧街”。据说是因为一个姓郭的福建籍富商命名。这富商是印尼华侨,以制糖起家,致富后想在香港拓展业务。本来是打算兴建炼糖厂。不料填海造地后,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劳工不足,经济萧条,郭氏唯有改作住宅发展,建成四十幢相连的楼房,人们就以“四十间”指称该地,后来政府将四十间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春秧街”。
连粤名搬出春秧街已很久。自打从南华大学毕业,他便想要离开这里。在澳洲读了博士,回到香港。娶了在西半山长大的袁美珍,在薄扶林道买了一个小单位。他才觉得是给自己洗了底,做了真正的香港人。可他一年里,总三不五时要做回福建人。多半是因了他九十多岁的阿嬷的召唤。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及各神佛圣诞。他阿嬷电话先打过来,要他回到乡会庵堂吃斋。这边稍有犹豫,便是劈头盖脸地一顿骂。有时他因有事情去不了,下次见面,得被他阿嬷念上十天半月。无非长房长孙、不肖不贤、愧对先祖之类。直至数到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回忆和女人跑掉的他阿公。眼睛一红,便是一把混浊老泪。连粤名心里慌得直叹气。袁美珍一边敷着面膜,在脸上拍打,一边幸灾乐祸地说:“你这才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这一天,袁美珍却也跟他来了。只因是大日子,观音诞。只见庵堂里热闹,人头涌涌,犹如置身岁晚的黄大仙祠。香火愈来愈鼎盛,乡会数年前终于凑够捐款,置下三个相邻单位,一千余呎
 ,有了小厅和厨房,安好佛像和坛位,让神明在这寸土寸金的香港宜居,夜深出窍施法,亦舒适安稳。
,有了小厅和厨房,安好佛像和坛位,让神明在这寸土寸金的香港宜居,夜深出窍施法,亦舒适安稳。
“名仔!”他阿嬷来了香港近五十年,仍然是一口坚硬的乡音。这口乡音被她从福建带来了香港。人人都说入乡随俗。这北角的人,都有这么一段相似故事。一九四〇年,连粤名的阿公和二叔公,跑到印尼讨生活,开理发店,每月寄钱回乡维持家计,和他阿嬷相见相会只能约在香港。那时中国内地与印尼还没建交,香港是个中转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阿嬷带了家当,携他父亲和他阿公团聚。他阿公却没出现过,听闻是和一个外侨女人去了新金山。好在有福建乡会帮衬,他阿嬷人又争气,在春秧街开了一爿成衣铺,竟然将几个子女都养大了。立业成家,各有所成。
可他阿嬷就偏偏改不了这一口乡音,早年被人讪笑,如今上年纪倒得了气壮,偌大的庵堂,对着连粤名呼呼喝喝。旁人就说:“连阿嬷,阿名好歹是个教授,不是‘青头仔
 ’啦。”他阿嬷便道:“教授又如何?还不是我的孙!”连粤名坐在乡会的小厅里,看他阿嬷一头稀疏的白发,露出了红色头皮,坐姿没有老态,竟是雄赳赳的,天然便是领袖模样。她手脚竟比一众中年妇人更为麻利,一边包着膶饼,一边和乡里谈笑。又因为耳朵有些背,说话声量就更大了些,洪钟似的。
’啦。”他阿嬷便道:“教授又如何?还不是我的孙!”连粤名坐在乡会的小厅里,看他阿嬷一头稀疏的白发,露出了红色头皮,坐姿没有老态,竟是雄赳赳的,天然便是领袖模样。她手脚竟比一众中年妇人更为麻利,一边包着膶饼,一边和乡里谈笑。又因为耳朵有些背,说话声量就更大了些,洪钟似的。
每到观音诞,这些福建女人在日出时分便来到庵堂,掀起大饭盖,准备下锅煮百人斋菜。太阳升起之时,乡里已穿起佛袍,与方丈住持一同赞佛诵文。中段休场,乡亲端上水果、甜汤。倒也有条不紊。
连粤名坐在缭绕的烟火里,看头顶悬着的“巍巍堂堂”和“慈航普渡”牌匾。功德箱上摆着贡果和闪烁不定的莲花佛灯。如今都要环保,那灯里装的是电池,是真正长明的。连粤名好像回到了儿时,跪在蒲团上被阿嬷摁下,纳头拜佛。那时的庵堂,没有现在的排场。袁美珍坐在他身边,埋着头,只是一径滑着手机,也不说话。她即使来了许多年,也并没有融入妇人的群体。不似连粤名的发小祥仔的老婆,早和老少查某
 打成一片,按说人家还是个茂名人。阿嬷和这个孙新抱
打成一片,按说人家还是个茂名人。阿嬷和这个孙新抱
 表面上客客气气,再也没有多的话讲。既然当自己是客人,便宾主自在好了。
表面上客客气气,再也没有多的话讲。既然当自己是客人,便宾主自在好了。
庵堂里竟也有一台电视,放着内地的电视剧,是个古装片。连粤名是不看电视的人,里头的女明星他竟然也认得,因为偷税漏税,上了八卦报纸和网站的头条。在这个宫斗剧里,演的是个委屈的角色。眼神里却是藏不住的凌厉,不消说,还是要赢到最后的。其实也没什么人看。乡里叔伯,木然对望、闲坐。呆呆地用眼神交流,以闽南语交谈,向对方借火,抽一口烟。
“莫再看喽,来啊,来啊,准备绕佛啦!”诵经后,阿嬷出来对连粤名呼唤,如同命令。倒没正眼看袁美珍。袁美珍将手机收起,站起来,面无表情,跟着连粤名。在场男女老少都要在庵堂绕佛数周,脸色端庄肃穆。这是旁人不甚理解的信仰和仪式,积年成俗。
连粤名走到了大街上,深深地呼了一口气。他的鼻腔里,残留着很浓重的香火味。自然,他手上还拎着阿嬷亲手制作的膶饼和芋粿。走到了春秧街上,他觉得轻松了一些。袁美珍约了旧同学喝茶,他便也不急着回家。先到“同福南货号”买上一斤年糕,顺便问一问大闸蟹上货的档期。眼下香港市面上的蟹,都说是阳澄湖的,自然不可尽信。这间老字号,总还是靠得住。然后呢,便是到隔壁“振南制面厂”,买新造的上海面。如今卖地道上海面的铺头越来越少。这街上,再有就是对面和“振南”打了数十年擂台的“双喜”,二者总不分高下。连粤名是吃惯了“振南”。上海面软滑弹牙,和香港盛行的广东面大相径庭;广东的碱水面硬而干,咬劲足,却不合北角人的口味。他和袁美珍便吃不到一起去。创办这“振南”的人叫李昆,其实呢,倒是个地道的广东人,传说青年时曾追随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唐绍仪,任侍从官,故熟悉其喜爱的面食。后来在坚拿道东开设“振南”,吸引了一班居港的上海人,便将面厂搬到有“小上海”之称的春秧街,也养刁了后来的福建人的胃口。福建呢,本不是美食之乡,可是有先前上海人的讲究,加上东南亚华侨的诡异的洋派。这春秧街上的味道,是断不会寂寞的。上海南货店内售的咸肉、火腿、咸菜、年糕,闽地有名的鱼丸、肉丸、蚵仔、芋粿、绿豆饼,也一应俱全。话说广东菜精致可观,连粤名在心里头,却另有自己的一番分庭抗礼。这是在春秧街几十年的生活给他锻造出来的。及至这里,他摇摇头,觉得是一条舌头阻挠自己成为地道的香港人。
这样想着,连粤名一路踱到了马宝道,这里的排档后方兼卖印尼香料杂货。自有一些南亚人的土产,像印尼虾片、千层糕、自家制咖喱、沙唛、辣椒酱、新鲜椰汁马豆糕等。掌铺的已是第三代,是个戴着苹果耳机的年轻人。看连粤名挑拣沙茶酱料,有些不耐烦,说:“这些货都是过年时进的,没什么新鲜的了。”从里间走出了一个妇人,认出了连粤名,说:“教授,多时没来了。”妇人是印尼本地人,嫁到了这华侨家族,还保留了传统的装束。她絮絮地说着。连粤名自然是识趣的人,便问她生意可好。她便说:“这种街坊生意,可谈得上好不好?有口饭吃就是了。”
这时候,天有些暗了。连粤名本来已经走到了地铁口,忽然想起了什么,就又折到了英皇道上,走到了一幢大厦前面。他抬头看到“丽宫”二字,晃一晃神,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