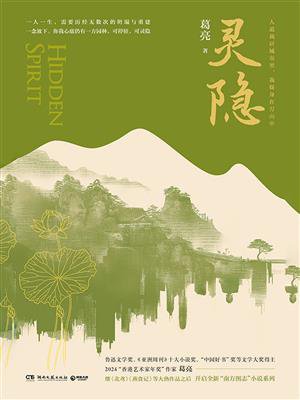二
南华大学,入了黄昏,另有一番热闹,是周末回校的学生们。又有各色的社团团员散落在校园里,派发着传单,招募新的团员。连粤名穿过黄克竞平台,看这些年轻人的脸上,一径是喜洋洋的,哪怕在一些门前寥落的社团。一个武术学会的男孩子,穿着咏春的练功服,向着他跑过来,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他并不认识。一问起来,才知是大一的新生,上过他的高分子物理大课。正寒暄,旁边一只毛茸茸的“金刚狼”,手里拎着一大袋外卖的饭盒,急匆匆地向cosplay
 学会摊位走过去。人潮涌动的,是电影学会的,原来正在招募临时演员。听说国际大导演要到“南华”来取景拍戏,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香港校园。自然要一班学生仔扮演大半个世纪前的好男好女。他想他读书的时候,也曾有过的临演的经历,是在香港的著名品牌“维他奶”广告里。那时青春无敌,他尚有一头茂盛的好头发。他禁不住摸摸自己的头顶,在心里苦笑一下。
学会摊位走过去。人潮涌动的,是电影学会的,原来正在招募临时演员。听说国际大导演要到“南华”来取景拍戏,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香港校园。自然要一班学生仔扮演大半个世纪前的好男好女。他想他读书的时候,也曾有过的临演的经历,是在香港的著名品牌“维他奶”广告里。那时青春无敌,他尚有一头茂盛的好头发。他禁不住摸摸自己的头顶,在心里苦笑一下。
到了明伦堂前,他对着门口的落地玻璃,整理了自己的仪容。他做这里的舍监已经一年有余。因学生出出入入,以身作则已近乎本能。这时候,一个男孩推开门,趿拉着人字拖,从里头出来,一边打了个悠长的哈欠,抬眼望他,有些措手不及。旁边看更
 的陈叔便道:“路仔,打游戏到成晚,刚刚困醒,这下好给教授撞到正。”男孩哈欠打到一半收不回,脸上便是个茫然惊讶的表情。连粤名心里想笑,便也宽宏地说:“唔好唔记得食饭。”
的陈叔便道:“路仔,打游戏到成晚,刚刚困醒,这下好给教授撞到正。”男孩哈欠打到一半收不回,脸上便是个茫然惊讶的表情。连粤名心里想笑,便也宽宏地说:“唔好唔记得食饭。”
他随电梯上到顶楼,掏了许久,找到钥匙,打开门。屋里响着叮叮咚咚的琴声,他知道是女儿回来了。是《水边的阿狄丽娜》,他站在门边,略阖上眼睛,听了一会儿,不觉地在心里打着拍子。他想,当年思睿赢得了全港钢琴大赛的青少年组亚军,就是弹了这支曲子啊。一个硬颈的细路女
 ,手指一触到琴键,就柔软下来了。她是有多久没弹过这支曲子了?是的,升了中五,忙于考学,思睿就不怎么碰钢琴,由它蒙尘。最近又捡起来了。她去年刚刚做上执牌牙医,连粤名托相熟的中介,为她在北角盘下了一个铺位开诊所。在渣华道,地段好,价钱也算公道。思睿说,做牙医的手势要灵活。便又开始练琴,锻炼手指关节。她说:“一样地轻重缓急,人口中的三十二颗牙齿,就是两排琴键。”
,手指一触到琴键,就柔软下来了。她是有多久没弹过这支曲子了?是的,升了中五,忙于考学,思睿就不怎么碰钢琴,由它蒙尘。最近又捡起来了。她去年刚刚做上执牌牙医,连粤名托相熟的中介,为她在北角盘下了一个铺位开诊所。在渣华道,地段好,价钱也算公道。思睿说,做牙医的手势要灵活。便又开始练琴,锻炼手指关节。她说:“一样地轻重缓急,人口中的三十二颗牙齿,就是两排琴键。”
“爸。”琴声停了,他睁开眼,思睿站在他面前。女儿眼窝淡淡的青,看上去有些疲惫。收拾得倒很利落,是准备出门的样子。
连粤名说:“晚饭不在家里吃?”
思睿躬下身,将短靴的拉锁使劲向上拉,一面轻轻应一声。
连粤名将手上的东西放在桌上,说:“和林昭?”
思睿说:“岳安琪回来了。”
连粤名说:“哪个岳安琪,是你那个中学同学?不是全家移民去加拿大了吗?”
思睿说:“回香港来了。”
连粤名愣一愣,说:“嗯,吃完饭早点回。对了,给你买了马拉糕,还热着。吃一口再走。”
思睿摇摇头,打开门,说:“不吃了,太甜。”
连粤名看着门被带上,把买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高丽菜,红萝卜,豆干,芽菜,芫荽,冬菇,猪肉,虾米,蚵仔。
这时候听到门一阵闷响,继而听见高跟鞋重重落地的声音。他从厨房里走出来,看见袁美珍一言不发,将手提袋扔到了沙发上。待她站起,又好像当他是隐形人,袁美珍径直走到房间,换了衣服就往浴室去。这时她倒看了连粤名一眼,说:“又整膶饼。”连粤名说:“系,观音诞,到底是个节。”
浴室里响起哗啦啦的水声。连粤名想一想,从环保袋里拿出那双拖鞋,摆到了擦脚垫上。水红色的鞋,上面镶着花形的水钻,在暗处也熠熠地发着光。
他满意地看一眼,叹口气,回身去厨房。
待浴室里的水声停了,厨房里正溢出馅料爆炒后的香气。因为后加了紫姜母,便有一丝清凛气,从满锅的膏腴中破茧而出,激得连粤名打了个喷嚏。他将馅料盛出来,摆到饭桌上。
“好大阵味。”袁美珍一边快步走过去,将客厅的窗户打开了,一边擦着湿漉漉的头发。她说:“风筒时好时坏,唔记得落去俾师傅整。”
连粤名说:“买个新的喇。”
袁美珍不睬他。他看见袁美珍走到鞋柜跟前,在里头翻找。这才发现她赤着脚。所经之处,地板上是一串浅浅脚印,水淋淋的。
他想一想,说:“我买给你新拖鞋啊。”
袁美珍回身看一眼,说:“几十岁人,着咁样嘅色,发乜姣。
 ”
”
连粤名愣一愣说:“我系在‘丽宫’买嘅。”
袁美珍的手停住,抬起头,眼神恍惚一下,说:“丽宫?仲未执笠
 ?”
?”
她重新翻找起来,翻出了一双旧年旅行时从酒店带回的拖鞋,穿上了。
连粤名坐下,将膶饼皮揭开,包上了馅料。递给袁美珍。袁美珍不接,问他:“你唔知我减紧肥?”
说完,便回房间去了。连粤名望着妻子略臃肿的体形,消失在走廊尽头。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一个女人陌生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他知道,袁美珍又开始直播了。
袁美珍走进房间时,没忘随手关掉客厅里的大灯。连粤名便坐在黑暗里头,只有房间四角射灯昏黄的光聚拢在他身上。像个光线诡异的小剧场的舞台,他坐在舞台中央,抬起手,开始吃那块膶饼。炒得时间长些,馅料气息渗透,五味杂陈。他看射灯的一束光,正照在那双新拖鞋上。方才鲜艳的红,也在暗中收敛了。小颗的水钻,到底是棱体,挣扎着将一些光芒折射出来,微弱而锋利。
连粤名想:丽宫,还没有执笠啊。
那年,他回到香港,给袁美珍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双丽宫的拖鞋。
说起来,也是少年任气。彼时,他在墨尔本大学已拿到博士学位,便被曼彻斯特的一家汽车公司录取,做了维修工程师。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唯有感情一无进展。连粤名是个内心坚定的人,可在男女的事情上,没什么主张。读研究生时,大约在域外的缘故,女人是不缺,澳洲的女子又豪放些。他的室友,是个内地富二代,风流子弟。带着他也算开了几次“洋荤”。然而,不知是否因家庭传统,他在感情上是没有投入的,总以为非我族类。他家境又很一般,对讲求现实的华裔女子也无甚吸引力。后来到了曼城——是个老牌的工业城市,人口众多,气息却阴冷。有破落的古堡和废弃的仓库。他所住的公寓,是个纺织厂的旧厂房改建的。他住得高,从窗内望出去,能看见默西河与广阔的荒野,河水流得慢,仿佛是凝滞的。这里的人便更冷漠些,日常也有着不必要的客气。让他本拘谨的性格,在南半球火热的锻造后,慢慢冷却。对女人,他也一样。性似乎亦无可无不可。他满足于精谨且无聊的工作,就这样过去了两年。若说平日里有什么亟盼,可能是从公司出门的第一个街角右转,进入一条后巷,那里有一间中餐厅。老板是成都人,餐厅牌匾上写的是“京川沪菜馆”。对贪新鲜的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各式菜系,并无太大分别。但大约是原乡的缘故,这家餐厅的菜的口味十分浓重。对讲究清淡的粤广人来说,原本是南辕北辙,但在这冷却的城市,尤其是冬日,这菜馆火热的气息,渐渐让连粤名爱上了。一碗酸辣汤先暖了胃,麻婆豆腐、回锅肉和口水鸡,每一样都是让味蕾有记忆的。吃惯了、久了,他索性懒得自己做,便将这间叫“蓉香”的中餐厅当了食堂。渐渐和魏姓老板熟了,老板便也知他不爱热闹的性格,在他下班前,提前在餐厅最靠里的两人桌上放上“留位”的牌子,等着他来。到了节假日,如圣诞,西方人举家团圆。因生意清淡,许多中餐厅便入乡随俗休了业。“蓉香”却还开着,连粤名婉拒了同事的邀请,没有其他地方去,仍来了。餐厅里只有两三位客,老板送他一个菜,又递给他一本书。书的装帧很粗糙。他翻开扉页,才看得出是本诗集。他抬起头,老板轻轻说:“是我写的。”他脸上还未露出恍然神情,去迎接这个满身油烟气的诗人的新身份,对方已满面羞赧,对他使劲摆摆手,让他不要声张。他翻开其中一页,上面有一句诗:“思乡的火车开远了,再看不见,我哭了/是被空气中的辣椒味,熏的。”
多年后,他对袁美珍提起魏老板的这句诗,她说她已经记不得了。
他和袁美珍,初识在这间中餐厅。照常是热闹的工作日夜晚,他收工,默默地坐在餐厅最里面的小台,吃一碗钟水饺。吃到一半,老板的太太走过来,抱歉地说:“连生,这位小姐等很久了,都没有桌子空出来。能不能和你搭个台?”他没说话,头也没有抬,只是将面前的碗盏向后撤了撤。就听见有人拉动椅子,然后坐下来。他闻到一种若有若无的香气,不禁仰一下脸。看对面的人,正将一条水红色的围巾取下,小心地叠起来。他听到一把女声,用广东话叫了红油抄手,临了轻轻说了“唔该”。声音明晰利落。这时候,他吃完了,一边叫老板埋单,一边将手绢拿出来,擦擦眼镜上的雾。站起来,余光看到对面客人。是个很年轻的女孩,眉目十分平淡,有粤广女生常有的黄脸色。留着这年纪的女生常有的长直发,将眉目又遮住了一些。
过几天的晚上,连粤名正吃着饭。听到有人用英文问:“先生,介不介意搭个台?”他抬起头看,原来又是前些天的女孩。她将头发束成了一束马尾状,戴了副金丝眼镜,穿身黑色套装,人看上去成熟干练一些。若有若无的气息——还是先前的。
连粤名没有说话,只是将面前碗盏向后撤了一撤。女孩坐下来,要了一碗宜宾燃面,加了个开水白菜。便开始叮叮当当地涮洗碗筷。连粤名在心里暗笑,他想:这多此一举的卫生行为,全世界大约只有老派的广东人才会认真。自己去国许久,早就忘了。没想到在异国他乡,会看到一个后生女这样做。女孩收拾好,给自己倒上一杯茶。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先生,你吃的是什么?”
连粤名愣一下,闷声道:“灯影牛肉。”
女孩又问:“好吃吗?”
没等他答,对面的人竟然伸出一双筷子,夹起了一块牛肉。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连粤名吓了一跳,他一抬眼,皱起眉头,看女孩正咀嚼着那块牛肉,嚼得很仔细。然后她用纸巾擦一擦嘴唇,喝口茶,说出了自己的结论。“还不错,就是辣了点。”
连粤名没来得及收回自己的目光。女孩说:“听先生的口音,是广东人。”
他正犹豫要不要答她。女孩却接口道:“我来猜一猜,你是香港人?”
连粤名的眼里的一丝光暴露了心事。女孩兴奋地说:“我猜对了吧。”
连粤名点点头。她说:“香港人的广东话,才有这样的懒音。我大学时读的应用语言学,算是行家呢。”
这一刻,她平淡的脸,忽而生动,泛起了红晕。就连脸上浅浅的雀斑也有了生气。然而,很快,她的神情又似乎暗淡下来。这时,她的面来了,她用筷子将面和肉臊子拌开,拌匀,拌了许久。却停下手,并没有吃。
连粤名吃完了,站起来去埋单。忽然听见女孩说:“我也是香港人。”
连粤名转过身,看一眼,对她说:“你点这个牛肉,可以交代厨师少辣。”
以后,连粤名再吃饭,便经常有这女孩和他搭台一起吃,即便是在客少的时候。有广东籍的老跑堂,打趣说:“袁小姐,又来同连生撑台脚
 ?”
?”
连粤名听到,脸上便使劲一红。倒是袁小姐,大大方方地答:“系呀!”
他便知道,女孩叫袁美珍。从香港到曼城大学读一年制语言教育的MA
 学位,读完了想要留下来,应聘却屡屡碰壁。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英国教人英语,是要关公门前耍大刀吗?”
学位,读完了想要留下来,应聘却屡屡碰壁。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英国教人英语,是要关公门前耍大刀吗?”
她第一次和连粤名说话,自作主张,吃了连粤名的菜,也知造次。那天她应聘了最后一家公司,做好了失败就回港的准备。却不晓得,第二天就收到了录取通知。她的工作是为来曼城读大学的预科学生培训英文。她说:“连生,你是我的福将。好彩我那天晚上吃了你的牛肉。”
连粤名也知道,这是无根据的恭维话。但不知为何,心里却也隐隐地高兴了。
因是两个人吃饭,大家可以多吃一个菜。花样也就多了,搭配上也就花一些心思。若一个叫了牛佛烘肘,另一个便叫白油豆腐,荤上托素;若一个叫了水煮鱼,另一个便叫樟茶鸭,浓淡总相宜。两个人收工的时间不同,若一个先到了,便等另一个,等来等去,总是时间不经济。便自然留下了联系方式,先到的先点,说了自己想点的,等对方搭上一个。连粤名有时先到了,电话里说了自己点的,估摸袁美珍要配上什么。等她说出来,跟自己想的一样,瞬间便生起孩童般的开心;若不一样,那刹那的失落,也是孩子般的。
再吃下去,便是默契了。一个可以帮另一个点。晚来的那个,多是工作上有牵绊,便会说给先来的听。一个说,一个听,就着一筷子菜,一口茶水,说说听听,一顿饭也就吃完了。
到了埋单时,连粤名有时仍不习惯西方人作风,心里大男子主义多些,觉得自己年长,又工作久些,推推让让自己给付了。女孩却坚持要和他AA制
 ,一两次后,竟然发了脾气,将自己的一份钱拍在桌上,扬长而去。一次走得急了,她留下了一副毛线手套。连粤名追出去时,人已不见了。
,一两次后,竟然发了脾气,将自己的一份钱拍在桌上,扬长而去。一次走得急了,她留下了一副毛线手套。连粤名追出去时,人已不见了。
晚上,连粤名就着光,看那副手套,已经很旧了,泛起了浅浅的毛球。他将右手伸进去,竟然能戴上,想袁美珍小小的个子,手却不小。只是在食指的指尖位置有一个小洞,是脱线了。他看着自己的指肚,因为工作磨出的老茧,从这洞里透出来,硬铮铮的。
再一年的除夕,“蓉香”总算歇业了一天。魏老板却将连粤名请到店里,说一起过个节。连粤名说:“唔好客气。我是一支公,你们两公婆团圆,我阻手阻脚。”
魏老板说:“我要回四川了,算给我们饯行吧。”电话那头静一静,他又笑笑说,“你又知道只有我们两公婆?”
连粤名走进店里,看见除了魏老板夫妻在,还有袁美珍。只在店中间摆了一台,袁美珍落手落脚,帮前帮后。倒显得只有连粤名一个人是客。四个人吃到一半,喝得也微醺。魏老板摇摇晃晃站起来,唱“一条大河波浪宽”,又唱《我的中国心》。叫连粤名唱,他推托说不会唱,魏老板举着酒杯,不放过他。他只好也站起来,唱《狮子山下》,可真的五音不全,唱得席上的人都笑起来。袁美珍接着他唱第二段,竟是清亮的嗓音,好像甄妮的原声。
魏老板忽然跑到厨房里,又跑出来,手里举着自己的那本诗集,上头都是油烟痕迹。翻到一页便念,恰好念到那句:
“思乡的火车开远了,再看不见,我哭了/是被空气中的辣椒味,熏的。”
这诗歌,被他用四川口音念出来,再加上几分醉意,其实有些滑稽。但忽然,就看见袁美珍的眼睛忽闪一下,伏在桌上哽咽起来,后来竟哭到失声。魏太太将手放在袁美珍的肩膀上。魏老板止住她,说:“别劝,哭出来,就舒服了。”
最后一道菜,是魏老板亲自端上来的,说:“这道菜是给我们——也是给你们做的。”
连粤名一看,是一盘“夫妻肺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