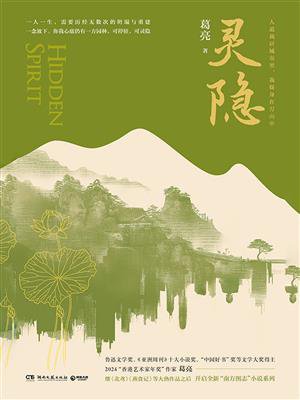三
这个除夕夜,袁美珍便随连粤名回了公寓。
在灯底下,连粤名看看女孩的脸,终于伸出手去。他先摘掉自己的眼镜,又摘掉女孩的眼镜。没有了眼镜,眼前人其实有些模糊了。他捧起了女孩的脸,终于吻上她,唇舌碰上的那一刻,忽然有些热辣的味道,从味蕾渗入。他愣一愣,想起是“夫妻肺片”的余味。
待事了了,连粤名坐在床上,才觉得赤裸的肩膀有凉意。怀里的女人仍是真实温热的。
他回想,对于床事,袁美珍并不陌生,且相当主动。她在身体交缠的细节间,往往知道自己努力争取快乐。待她高潮时,平淡的五官间,便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这让连粤名既惊且喜。他想:这个女孩好,懂得如何取悦自己,便省去了让别人取悦她的麻烦。
第二天清晨,他醒来,看见女孩穿着他宽大的睡衣,正坐在窗前翻看什么。他看了看,发现是他从家里带来的一本相册。带来了许久,他从未打开过,甚至不知放到哪里去了。但此时,他似乎并不怪袁美珍动了他的隐私,反而觉得她异乎寻常地亲近。他悄悄下了床,打开抽屉。将一副崭新的毛线手套递给了袁美珍。这副手套,上面绣着奔跑的麋鹿。每个指尖处,都有一颗圣诞果。其实他在圣诞前就买了,时常放在包里,却一直不知如何拿给她。袁美珍接过来,戴上,将将好。她大概也看见了圣诞果,故意用凉薄的语气说:“不知是哪个女人不要的,给了我。”连粤名未及辩白,她却“扑哧”一声笑了,说:“多谢。我这儿倒没有哪个男人不要的东西送给你。”
他们两个便依偎在床上,继续看那相册。袁美珍看到一张照片,是他大学时拍的“维他奶”广告。那时青春澄澈,尚有一头茂盛的好头发。她伸出手,摸摸连粤名开始稀疏的头顶,他避一下。袁美珍说:“怕什么?贵人不顶重发。”又看到了一张照片,她指着问连粤名。连粤名看着照片上面相严厉的老人,轻轻说:“这是我阿嬷。”
袁美珍仔细看了看,说:“阿嬷的鞋真好看。”
连粤名从未注意过阿嬷穿的是什么鞋。这时看看,是黑底的绣花拖鞋,上头镶着水钻。他看袁美珍看得目不转睛,笑笑,说:“你不嫌老土噢。”
袁美珍静静的,半晌才说:“老东西好,稳阵
 。”
。”
春节,连粤名第一次给袁美珍整了膶饼吃。
料自然是东挪西凑的。两人走了几家超市,又跑去了市中心皮卡迪利花园,在唐人街里转了两圈,才勉强凑齐了。只是石蚵唯有改用生蚝,桶笋则以佛手瓜勉强代替。
晚上,袁美珍看连粤名用面粉加水,使劲搅打,到了韧劲上来。这才烧上煤气炉,坐上一只小平锅。将那面团在锅底一旋,再一擦,便是一张薄如纸的饼皮。手势娴熟,变魔术似的。袁美珍眼睛亮一亮,把他的手拿过来,放在自己膝头,说:“没想到啊,连生,这手粗粗大大,倒巧得过女人。”
连粤名笑笑,说:“我跟阿嬷长大。我们福建人家寻常东西,自小眼观手做,哪儿有不会的。”
袁美珍便道:“坏了,那我要是学不会,将来怕要被你家里人怪罪。”
连粤名柔声说:“我们两个,一个会就行了,另一个负责吃。”
同居了一年后,连粤名才知道,袁美珍在西半山长大。待他知道时,她已经决定回香港了。
袁美珍是家中长女,母亲早逝,父亲再娶。但辛德瑞拉的古老的桥段不适用于她的人生。她早早从干德道搬离出来,从此靠自己。上学跟政府贷款,留学一路打工。在旁人眼里,有类似经历的,总代表对富有家庭的叛离,是所谓“作”。一番辗转,折腾够了,便是尘归尘,土归土。前面的种种,都是为最后的好日子做铺垫。可她并不是,她回到了香港,除了见了病危的父亲最后一面,还放弃了继承权。
她对连粤名说,她始终没恨过父亲,也不恨后母。只是,她不理解,她阿爸为什么在她母亲死后,会娶一个和她母亲性情截然不同的女人,并且安然走过这么多年。这是对她阿母的否定,也是对她人生的否定。
她有着和她父亲极其相类的面目,这使得她作为女性,在相貌上从未有过优势。她很确信,她出身寒微的母亲在这个家中已经了无痕迹。能证明她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唯有她自己。
她给连粤名看她母亲的遗物。其中有一枚景泰蓝香盒,外头镶着金丝绕成的枝叶,覆盖着莫可名状的月白花朵。打开来,是张圆形小照。照片很老了,上面印着一抹胭脂。黑白界线已不分明,灰扑扑。但辨得出,照片中的人不是闽粤女子的面相。脸很圆润,清秀,倒有几分江南女子的情致。眼里含笑,有主张。
连粤名又闻到香盒里荡漾出一丝气味,和袁美珍身上的竟一样。幽幽的花香。袁美珍说,这是素馨的气味。母亲一生只用这一种香,应时的花,插在鬓上。谢了,便攒起来,叫人焙干、磨粉,制成香。
如今用香的人、制香的人,都没有了。她要留着母亲的气味。好在Gucci
 推出A Chant for the Nymph
推出A Chant for the Nymph
 ,前调正是素馨。她便一直用这款香水,用了很多年。
,前调正是素馨。她便一直用这款香水,用了很多年。
她母亲是存在过的。她证明的方式也包括让自己独立艰辛地活着。她说,母亲一生所有,也都是凭一己之力挣来的。
连粤名说:“那你……愿意回香港了?”
袁美珍说:“以前,我不回去,是因为没有底。如今有了你,我就有了底。”
料理完后事,两个人便在北角租了个唐楼,在明园西街。房子是他阿嬷的一个同乡老姐妹的,几十年的牌搭子。她老伴儿是上海的工厂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香港。到老了两人整天吵架,不胜其烦。就买了两个相邻单位,除了吃饭,各安其是,省得相看两厌。三年前老先生寿终正寝,老太太隔壁房子便空着。如今租给连粤名,租金要得很便宜。说是住两个年轻人,壮一壮阳气。
两个人住下来。家具都是现成的,虽然老派,酸枝鸡翅木,看着却有说不出的砥实。连粤名看袁美珍不嫌,便放下心来。他的履历很好,又有留洋经历,未几在母校南华大学谋到助理教授的职位。拿到工资当天,心里也踏实,他陪着袁美珍好好走了一回北角,沿着电器道,一直走到英皇道。一路走,一路讲。哪里是他读过的小学,哪里是他常去的戏院,哪里是他爱吃的大排档。袁美珍望着皇都戏院斑驳的红墙和浮雕。她说:“要说这里也是香港,前许多年,我住过的那里,倒不像香港了。”
连粤名带她拐进一处暗巷。巷道幽长,走着走着,整个黑了下去。连粤名就牵上她的手,一片密实的黑暗里,辨认彼此呼吸的轮廓,向前走。走着走着,豁然开朗,竟是一片温黄的灯光。光里是一面墙,墙上五彩纷呈的一片。原来是个单边的横门铺,整面墙都是柜子,琳琅满目的都是鞋。高处四个字“丽宫绣鞋”。连粤名说:“阿嬷自打到了香港来,拖鞋都是在这里买的。”他拿出那张照片,给老板看。光头老板看一眼他,说:“阿名,好耐冇见。都话你读番书唔翻来喇。
 ”
”
连粤名笑笑,说:“老板替我挑一对。”
老板仔细辨认,说:“带水钻嘅,阿嬷呢款唔好搵,俾啲时间我。买多对?
 ”
”
连粤名又笑笑。老板看一眼袁美珍,醒目
 道:“得!稍等。”
道:“得!稍等。”
半晌,老板出来,捧着一双鞋说:“小姐好彩,仲有一对。阿嬷嗰对,鱼戏莲荷。呢对仲好意头,连理枝。”
袁美珍脱了鞋,将这双鞋穿上,尺码刚刚好。水红色的缎面上,绣了葱茏的枝叶。将两脚并拢,鞋上的枝条便彼此相连,浑然一体。
从“丽宫绣鞋”走出来,袁美珍说:“你好嘢
 ,先前送了我手套,如今又送鞋。我上下的手脚都被你捆住了。”
,先前送了我手套,如今又送鞋。我上下的手脚都被你捆住了。”
连粤名不说话,只是笑着望她。
回到家,两个人心生默契,一拥一抱,便向床上走去。大得不合情理的宁式床,原本在卧室里是突兀的,这时却让他们如鱼得水。翻转间,喘息都是炙热的。其间起伏与攀升,有些硬的床板,硌着他们的脊背与胸腹,倒有些凌虐的快意。将到高潮处,连粤名忽而抽出身体。袁美珍不情愿地坐起身,看见他急灼灼的,从包里拿出那双鞋,给袁美珍穿上。女人净白的身体,脚上是艳红的两点。他的欲望顿时膨胀,冲撞间,有些不管不顾。动作猛了,鞋便落到了地上,“啪嗒”一声。他没有停,将女人抱起来。却踩到了鞋上,只一滑,鞋飞了出去。琳琅水钻脱落,撒了一地。他怔住,心神一恍惚,泄了力气,用抱歉的眼神看袁美珍。女人没说话,伸出手臂,只管紧紧揽住他的颈。
因为孙子住在这里,阿嬷来得便勤。她来了,先去探老姐妹,手里捧着一颗柚子。
她到了连粤名的屋里,看尚算窗明几净、企企理理
 。这天连粤名去大学教课,只有袁美珍一个人。阿嬷含笑看她,温言软语。袁美珍看着这老太太,身腰朗直,样貌和照片很像,可又说不出,似乎是哪里不太像。阿嬷说了一句,便站起来。一低头,看见床底下的绣花拖鞋,莹莹地泛着水红的光。另有几星灿然,在最内的深暗处闪一下,又一下,是散落的碎钻。
。这天连粤名去大学教课,只有袁美珍一个人。阿嬷含笑看她,温言软语。袁美珍看着这老太太,身腰朗直,样貌和照片很像,可又说不出,似乎是哪里不太像。阿嬷说了一句,便站起来。一低头,看见床底下的绣花拖鞋,莹莹地泛着水红的光。另有几星灿然,在最内的深暗处闪一下,又一下,是散落的碎钻。
她便回过头,对自己的老姐妹说:“你就好喇。前些年牌桌上我输你的钱,几个月租金给你赚回了本。”
老姐妹刚想为自己辩白。却见阿嬷改用了莆仙话,说:“有手有脚,不出外做事,租金都是我孙一个辛苦挣来的。”
老姐妹愣住了,却看她脸上并无愠色,相反似是一种欣然神情,像在分享一桩可喜的事情。阿嬷满面含笑,继续说:“淡眉眼,高颧骨,是个男人相。名仔命硬,将来少不了苦头吃。”
老姐妹怔怔,偷眼望一下近旁的袁美珍——似乎并无反应。她便也以莆仙话悄然说:“不好这么说自己的孙媳妇啦。”
阿嬷挑挑眼,微笑道:“没过门,算得什么孙媳妇。”
老姐妹看袁美珍笑盈盈,便也大起胆子,一瞥卧室里的宁式大床,说:“过门有什么要紧。我可是听得见,这日日夜夜的,怕是你要先得一个曾孙呢。”
阿嬷回过身,用慈爱的神情看着袁美珍,说道:“我预备摆酒,怕是人家家里无人来。”
袁美珍笑着牵起他阿嬷的手,敬一杯茶。自己捧起另一杯,将一种东西在自己心底挤压,碾碎,然后就着茶水咽下去。
往后的几十年,阿嬷一直以为袁美珍听不懂她晦涩的家乡话,甚至当着袁美珍的面,和别人说些日常体己话。那日,袁美珍当真希望听不懂。连她都低估了自己的语言天分。回香港的第一个月,她有意无意,听连粤名和他阿嬷的几通电话。那天他阿嬷微笑看她,说出来的,她听得真金白银,一字一血。
两个月后,袁美珍在港大山下的坚尼地城,看定一个单位。面积很小,租金却贵上许多。二话不说,她便与连粤名搬了过去。阿嬷挽留,道:“何苦搬去那里。北角多好,一家人多个照应。”
袁美珍笑一笑,柔声说:“阿嬷放心,我会睇实你嘅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