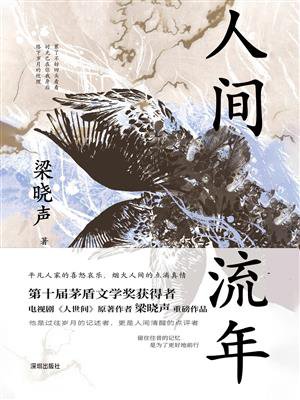评劳模那些事
从前,评劳模这件事,曾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象。
如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已甚少,评劳模便成了全世界的稀有现象。
“劳模”是个总概念。在从前,各级政府都经常从单位、企业、行业中评选劳模。评是民主程序,选是集中方式。选的权威性绝对大于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程序只不过是形式。事实是,在评选劳模这件事上,也许是中国将民主集中方法运用得相当之好的体现。
一般而言,全国评选劳模、三八红旗手,各地方评选先进生产者、模范劳动者、行业标兵人物。全国劳模和三八红旗手是劳动者所获得的最高荣誉,这两项评选发证书,还发奖章。而一个劳动者一旦被评选上了,往往会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对各省和直辖市一级的劳模和三八红旗手也发奖章,但对地县一级的则只发证书,不发奖章了。
如今,各行业、各系统也每进行评选,发奖杯可;不提倡、不鼓励甚至限制发奖章,以杜绝发奖章成风,保持五一劳动奖章和三八红旗手奖章的殊荣色彩。先有全国劳模,后有全国三八红旗手。因为,女性多是服务行业从业者,若与男性劳动者一并参与评选,其优秀性很容易受到轻视。另行评选三八红旗手,确实意味着中国对优秀女性劳动者的厚爱。在1980年代前,两项评选基本面向体力劳动者。1980年代后,开始面向脑力劳动者,许多知识分子亦能获得两项殊荣了,如教师、医生、护士、司法人员、公安人员甚至学术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科研工作者。
无须讳言,评选各级劳模,初衷是为了激发普通劳动者劳动积极性,树立榜样,号召学习,以使高涨的劳动热忱在全国蔚然成风。
但是,也不能仅仅将此法视为刺激生产力的手段——在物质和金钱奖励不能广泛实行的情况之下,荣誉的颁予,体现着一个国家对于普通劳动者社会贡献的肯定。
将中国这样有七十年社会主义历史的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比较一下,会发现在评选问题上的明显差异。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各行各业有影响的评选活动也很多,但面向普通劳动者的评选活动却少之又少。
这是为什么呢?
那些国家,根本漠视普通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吗?
我认为并不是那样。
差异与对劳动法的执行力度有关。
在那些国家,劳动法是极其具有法律神圣性的大法,其神圣性令社会各行各业不敢越雷池半步。也就是说,一名普通劳动者,除了不必是劳动模范,可以是其他任何方面的模范人物——如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模范,组织业余文艺或文化活动的模范,见义勇为的模范,发明创造的模范,包括是好儿女、好父母、好公民。倘他们在后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公认的模范性,可以成为电视新闻人物、杂志封面人物;他们的事迹会被报道,写成书,拍成电影;他们也将受到广泛尊敬。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竞选州长、议员甚至总统。
这是因为在那样一些国家,企业或单位大抵是私营性质,如果社会鼓励劳动者终日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埋头苦干,有一分热恨不得发十分光,劳动积极性超过对家庭的责任和热爱——那么将形同于使劳动者为各式各样的资产者卖命,以被剥削为荣。别国之文化绝对不进行此种引导和宣传,会将此种文化视为可耻的文化现象。
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一切单位、企业皆属国有,包括三人以上的理发馆、饭店。而从早期的制度逻辑上讲,一切劳动者都是国家主人,也是一切单位和企业的主人。劳动者不论将自己和劳动能力发挥到多么强的程度,都等于是为自己劳动。为自己劳动理应不计报酬,理应倍觉愉快,不存在剥削不剥削的问题,更不存在是否违反劳动法的问题——而在别国,由于人和单位、和企业的关系首先是劳资关系,资本家企图以奖金为诱饵操控劳动者为其超时超体能地劳动,属严重犯法行径,必将受到法办。劳动者一厢情愿也不可,若妻子儿女告其不顾家庭,一告一个准,并且受到的只有谴责,绝无同情。
但,社会主义国家也罢,非社会主义国家也罢,在尊崇和宣传爱岗敬业的模范人物方面,一致的方面也很多,远多于差异。如客机、客轮、公交车、出租车司机,警察、安保人员、消防队员,幼儿园、学校、医院、邮局、社保单位——总之在一切服务于大众的工作方面,凡有好人好事,媒体总是会第一时间予以宣传报道,政府总是会及时予以表彰。甚或,总统也会写信予以赞扬,甚至抽空接见。
这一种超越国家制度、文化差异的共性,说明在大多数国家之间,在基本价值观的取向方面,长期以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体系能脱离人类社会的文化进步而孤立存在。一时或可,长久,没门儿。
一个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各行各业的劳模人物,在民间大抵广受尊敬。对他们的评选,基本上是实至名归的。劳模劳模,一年三百六十几天,天天在劳动中,在劳动者群体中,许多双眼睛看着呢,能说不能干的人根本选不上,领导赏识,单方面拔苗助长不起作用——提干可以,评选劳模不行。
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早期中国劳模,无一不是在普通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计较任何个人利益的典型人物。
并且,大抵的,他们几乎全是不会说,只肯埋头苦干的人。一朝成为劳模,那么便终生成为只知奉献,甘愿远离一切个人利益,极其珍惜荣誉,无怨无悔之人了。
各级政府对劳模是爱护的,每年安排他们疗养,出席庆典活动。
略微分析一下中国民间早期对劳模的心理,有助于我们了解长期平均主义的社会分配原则下,民间百姓的思想演变过程。
如前所述,民间对劳模是尊敬的——但若一个人成为劳模后所获得的除了荣誉,还有物质方面的种种实惠,那么情况不久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当年民间对劳模的心理,很像古代对“孝廉”人物的心理——似乎一个人一旦成了“孝廉”,就不但必须成为没有什么个人利益考虑的人,而且必须成为方方面面的表率。即使在微不足道的方面被认为言行失节(姑且不论是否符合事实),其“孝廉”资格也会大受质疑甚至攻讦。一方面,许多人都想争当“孝廉”;另一方面,成了“孝廉”的人,便几乎完全丧失了隐私。专有一些人以长了钩子似的眼经常盯着他们,企图发现他们有问题的言行;一旦发现,就四处投书揭发,有时直接转到了皇帝那里。古代的“孝廉”,便都有几分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唯恐克己不严,对不起“孝廉”二字。他们中,有人终生贫寒,连有慈悲心的官员也怜悯的,却又不敢实行救济,怕坏了“孝廉”的名节。皇帝了解到此种情况,也没辙,每写给他们一封亲笔信,进行精神上的鼓励,物质奖赏是绝不赐予的。担心一旦开了口子,“孝廉”制度就偏了方向。
从前的劳模,不少人的家庭生活困难。各级政府即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往往在助济方面也很谨慎。民间对劳模的要求,接近于对劳动者中的圣人的要求。而圣人,在民间看来,应具有高僧大德般的无私无欲的境界。
所以从前的劳模,不少人的工资反而比同龄人还低。因为,若非工资普涨,而是有百分比的涨法,他们常会表态放弃,以符合劳模的境界。
他们社会活动较多。每次参加完活动,往往先不回家,直接回工地或厂里。他们往往比大禹还大禹,岂止三过家门而不入!
他们所获得的具有物质性的奖品,基本是笔记本、钢笔、毛巾、肥皂、劳保手套之类。
早年间发生过这样的事——单位或企业向劳模发了金星钢笔、香皂和一套工作服,于是受到劳动者群众强烈批评——金星钢笔是名牌笔,三元多一支;一套工作服起码价值五六元;发之,不是物质奖励又是什么?劳模的脸不也是劳动者的脸吗?有多少劳动者非用香皂洗脸呢?发块香皂不是小事;常用香皂洗脸的劳模,不脱离劳动者群众才怪了呢!
可以这么说,在从前,民间的极左思想也很厉害。
一个问题是——民间的极左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有些人习惯于将根源归于极左年代的影响,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
但原因不止于此。
我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人性方面的,即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大多数人对物质的反应必然十分敏感,于是形成了一种“物质获得资格论”的社会现象。当官之人换了一处住房又换了一处住房,换了一辆车又换了一辆车;住房越换越大,车越换越高级,对这类事,民间很能容忍。若官不够大,比如县级干部,民间往往尚敢说三道四。若官够大,比如省级干部,民间则往往这么认为——人家官做到那么大了嘛,资格在那儿,似乎一切便都应该了。
所以,官本位在民间有很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
后来越发膨胀的官特权也是民间惯出来的。
但民间的眼在望向民间时,特别是在望向同类时,特别是在事关物质利益时,则换了另一种心态——荣誉谁爱争谁争,反正不实惠。至于物质奖励,那可得坚决反对!劳模不也是劳动者吗?也是劳动者不就是和我一样的人吗?他们有什么资格啊?凭什么!
当然,这里说的是从前。
现在的民间,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
民间进步了。
民间的进步,才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