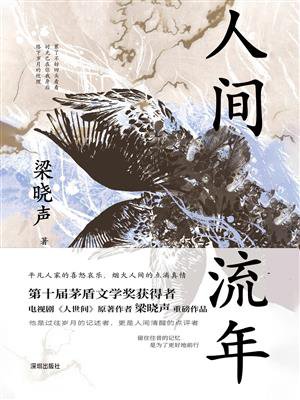当年修房子那些事
当年之中国,与现在一样——人们的住房无非三类:公有的、私有的、合法或不合法的自建房。
上自省市领导下至各政府部门、军队系统、公安系统、企事业单位分给员工的住房,皆属公房。包括某些大厂分给工人的宿舍在内,一般都比较好,起码是砖房。住公房的人基本都要交房租,大干部、高等知识分子、文艺界名流交不交并不统一,据说有特殊贡献者享受免交优待;生活特别困难的工人也可免交。
私有住房指某些人家解放前买下的住房。既然属于私有,解放后便可买卖,但须交房租,因为所占土地已归属国家。
合法的自建房指经有关部门批准而建的住房,多属于工人之家——老父母从农村到城里来投奔儿女并将依靠儿女养老的家庭;自己的大儿大女结婚了却无房可住;总之人口多了原有住房根本住不开了,厂里又无房可分给他们,不批准自建怎么办呢?不合法的是指为了住得宽松点,虽未经批准但偷偷盖起来了,既成事实了,谁敢拆就跟谁玩命,或自寻短见;往往也就任其不合法地存在着了。当年也是讲维稳的,逼出人命总归不好。自建房面积都不大,最大也就二十来平方米。有人在那样的房子里结婚、生儿育女,直至儿女上了中学、高中、参加了工作,而自己老去了。工厂大抵在城市的偏僻区域或郊区,毕竟有自建空间,所建基本是土坯房。市中心楼房多,除了一层,二层以上没有自建的可能。而一层又大抵临马路的人行道,有胆量乱搭乱建也搭建不成,所以市中心没自建房。
1949年后的哈尔滨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除了城市主要街道的改造和各级政府机关办公楼的兴建,在住宅楼的兴建方面并无大的举动。当年人口的增加尚不明显,最广大的市民从前的居住状况怎样,至1980年前后基本还怎样。当年没有“改善市民居住条件”这一提法。提了也白提,各级政府都没经济实力考虑此事。非但哈尔滨如此,包括“京上广津”等城市在内的一切中国城市,不分大小,概莫如此。东西南北中,绝大多数省会城市旧貌依然,县级城市破破烂烂。我是知青时的团部距黑河市十八里,去过的知青这样形容它——“两条街道三个岗亭,一处公园四个猴”。而黑河作为一级“地委”所在城市,那时已有二十余年历史了。
具体再说到哈尔滨,“文革”前盖了一幢八层的宾馆曰“北方大厦”,在当年是哈尔滨人最津津乐道的骄傲之一。
老处级及处以上干部住的基本是老楼或独门独院的俄式砖房、日式砖房。那些公房自然是定期维修的,却也只不过是刷刷外墙、门窗,检查一下水电管道、线路。好在那些公房原本质量一流,无须大费周章地进行维修或改造。科、教、文、卫系统的名流基本也住那类公房,但总人数毕竟是不多的。
私房的主人们也有所住条件很好的——他们大抵是1949年以前成功的或较成功的商企界人士或中医界名医。他们以前住的院子、房子肯定更大更多,后来一部分被充公了或自愿捐给政府了,但留给他们的家庭的部分,依然可算全哈尔滨市第二好的院子、房子。他们作为原房主不必交房租,维修便也是自家之事了。他们中某些人家住的房子,直至20世纪80年代,基本状况仍比较好。但另外一些私房,情况则甚不乐观——下沉了,门斗倾斜了,台阶木腐朽了,窗框损坏严重了,铁房盖漏雨了,雨水槽残缺了……何况有些私房不是砖体结构的,而是板夹泥的——多是俄式住房。
不少俄国人尤喜板夹泥的住房,与耗资多少无关,与审美的关系更大。板夹泥分两种——一种外墙镶木板,一种外墙抹洋灰。所夹之“泥”也不是一般泥土,而是按比例掺入锯末子的混合土;如此这般的“泥”具有保暖和防火的作用。冬季内墙一点都不凉。隔两三年,他们会将外墙用颜色灰料或油漆喷刷一遍,因而又簇新如初了。再配上他们中意的木栅栏围成的小前院,种上花树,自有一番童话式的美观。
但前提是,住这样的院子、房子,隔两年必得维修一次。倘一二十年内未维修过,结果就会不美好了。
它们的主人成为哈尔滨人以后,几乎谁家都没经济实力那么维修了。除“三名三高”
 人士,普通中国人的工资差别已很有限,绝大多数人家负担不起那样一笔开支。二十余年后,那些私房容貌改变——原本是洋灰外墙的,墙皮成片脱落了。当年不似现在,到处可见卖建材的小店,甚至每座城市都有建材一条街,什么建材都可以买到。当年私人是很难买到砖瓦、水泥、沙子和白灰的,那些东西国家搞建筑还得经过层层批给呢。所以,主人们只得寻找黄土,能找到就不错了。又所以,他们的住房的外墙变成掺草的泥墙了。而原本镶木板的外墙呢,木板越掉越少,便也干脆统统拆下抹成泥墙了。至于粉刷,就别起那念头了。都变成泥墙了,还粉刷个什么劲儿呢!最令主人头疼的,是铁皮房顶锈了,破了,漏了。那种铁皮,长宽规格像壁纸,用铆钉铆在一起的,隔两年必须用油漆仔仔细细刷一遍。不那么维护,破损了毫不奇怪。一旦破损,也不能整张换,哪儿去买整张的厚铁皮呀!能搞到几小块就不错了——得向有关部门申请,为修房顶倒是会批给的。铁皮补铁皮,毕竟不像以布补布以皮子补皮子般容易;那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不是谁都能干的。倘补过了还漏雨或更漏了,不是白费事了吗?又要买铁皮又要雇人补,无疑对许多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一年又一年,渐渐地,原本美观的房顶就像叫花子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了。原本窗口四边有木饰板的,自然也残缺不全了。原本的小花园呢,美观的木栅栏逐渐被树皮、树杈、带刺铁丝什么的取代了。
人士,普通中国人的工资差别已很有限,绝大多数人家负担不起那样一笔开支。二十余年后,那些私房容貌改变——原本是洋灰外墙的,墙皮成片脱落了。当年不似现在,到处可见卖建材的小店,甚至每座城市都有建材一条街,什么建材都可以买到。当年私人是很难买到砖瓦、水泥、沙子和白灰的,那些东西国家搞建筑还得经过层层批给呢。所以,主人们只得寻找黄土,能找到就不错了。又所以,他们的住房的外墙变成掺草的泥墙了。而原本镶木板的外墙呢,木板越掉越少,便也干脆统统拆下抹成泥墙了。至于粉刷,就别起那念头了。都变成泥墙了,还粉刷个什么劲儿呢!最令主人头疼的,是铁皮房顶锈了,破了,漏了。那种铁皮,长宽规格像壁纸,用铆钉铆在一起的,隔两年必须用油漆仔仔细细刷一遍。不那么维护,破损了毫不奇怪。一旦破损,也不能整张换,哪儿去买整张的厚铁皮呀!能搞到几小块就不错了——得向有关部门申请,为修房顶倒是会批给的。铁皮补铁皮,毕竟不像以布补布以皮子补皮子般容易;那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不是谁都能干的。倘补过了还漏雨或更漏了,不是白费事了吗?又要买铁皮又要雇人补,无疑对许多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一年又一年,渐渐地,原本美观的房顶就像叫花子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了。原本窗口四边有木饰板的,自然也残缺不全了。原本的小花园呢,美观的木栅栏逐渐被树皮、树杈、带刺铁丝什么的取代了。
尽管如此,住那些私房的人家仍是受羡慕的,因为一般是两室一厅有单独厨房的,虽然厅都不大,偏卧也小。而普通的百姓人家,对于“厅”尚根本没有需要意识,能住上四十几平方米的房就知足常乐了,厨房也大抵搭床睡人的。
工厂区有幸住上工人宿舍的工人之家,一般也就是一大一小两个房间的砖瓦平房,四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得五口之家才能住上,往往是三个孩子或两个孩子但有老人同住的工人之家,且要按入厂时间长短排队;排到退休前终于分到了便是谢天谢地之事。那种砖瓦平房很经住,所谓维修往往不过是由厂里换几片破碎的瓦,或正正无法关严的门,重砌一下倾斜的烟囱。而工人们反映强烈的,通常是公用下水道和公厕存在的问题。别的城市怎样我不了解,像《功夫》中那种廉租的危楼,当年在全哈尔滨市少说也有近百处。
最令人们头疼的,是那些所谓自建房及前后或左右接出来的违建房。这类住房基本是土坯墙加油毡的房顶。在北方,油毡的房顶是很临时性的房顶,既不保暖,也容易在大风天被刮破。破了怎么办呢,用油毡补上就是。那是没任何技术含量的活儿,家家的男人都可以做好。哪儿破了,剪下片油毡用木条钉上,再多刷几遍沥青即可。一个时期内油毡是能买到的,后来又买不到了。房顶漏了的人家不得已,将防止小孩尿湿了被窝的一种油布剪成大大小小的油布片东一片西一片地补上房顶。油毡是黑色的,油布是酱黄色的,看上去具有“后现代”拼图的感觉。那种油布是由在桐油中浸过的帆布加工成的,油纸伞的油纸也是那么加工成的。但油布终究也属于布,夏天一晒冬天一冻,第二年又漏雨了,必须再补。所幸在当年还有油布卖,价格不算太贵,否则房顶漏了的人家简直就没招了。
土坯房也是要砌地基的,它的主人们当年都买不起新砖,只能用到处捡的断砖和石头砌地基。备料往往不足,地基一般砌到稍微高出地面的高度就作罢了。所以,若某一夏季雨天多,土坯墙根就湿得半透了,内墙反潮姑且不论,还有墙倒房塌的隐患。
是故,每一户住土坯房的大人们,都深知护墙根的重要性。护墙根当然最好用水泥,但那年月一般人家也搞不到水泥呀,炉灰就成了好东西。家家户户都不会将炉灰白白扔了,而是用来培墙根。但是接连几场大雨过后,家家户户的土坯房都会湿到墙根的一米以上,于是人们又想到了用掺入炉灰的黄土抹墙的办法——那样做了之后,湿过的外墙在晴天里干得快。问题却是,冻了一冬天后,来年春夏外墙很容易因为黏性不够成片掉落。在农村,勤快的大人几乎每年秋季都从上到下将土坯房的外墙抹一遍,没有黄土,一般黑土也行。在东北,凡土必有一定黏性。拌入麦秸,抹一遍就厚一层。十年住下来,墙体比当初厚多了。然而在城市里还住土坯房的男主人们大抵是早出晚归的上班族,哪儿有时间每年抹一次房子呢?即使能挤出时间,适宜抹房子的季节往往也错过了。并且,每年哪儿去弄到所需的黄泥和麦秸呢?又不是小修小抹,需要的黄泥和麦秸是不少的呀。所以,黄泥掺炉灰,一向是他们平时对自家土坯房进行局部维护的方法。
实际上,如果用黄泥掺炉灰抹内墙的裂缝或补块墙皮、重砌一下炉灶,效果还是不错的。炉灰的作用虽比不上细沙,但比黄泥掺麦秸的效果看起来美观。
在从前的理发铺里,理发师傅理过发后常会主动问:“头楂带走吗?”——他们为理发者备有包走头楂的报纸片。
人们带走头楂干什么呢?
以备抹墙时掺入抹墙泥里。头发多细呀,干后不着痕迹,却能起到与麦秸同样的牵连作用。但只有对原本齐平的内墙才会那样,而且即使对内墙一般人家也不会那么讲究,少数住俄式房的人家才会那样。
我下乡前,力所能及地将我家的土坯房之里里外外的裂缝或掉墙皮处抹了一遍,也将炉灶和火炕的炕面重砌了一番。那些日子,我常因缺少黄泥和工具而犯愁,做梦都梦到砖、水泥、沙子、白灰和油毡以及抹子、瓦刀之类工具。我的工具却只不过是做饭用的铲子和劈柴用的斧头。
当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一名中学同学家的墙根——他家附近的炼铁厂搬迁了,遗留下了几个篮球场大的积满铁锈的地方,铁锈近一尺厚。许多人家大人孩子齐上阵,土篮子破桶破盆都用上,争先恐后地挖起铁锈弄回家。他们将铁锈和炉灰掺入黄泥将自家墙根抹上一层,干后不但平滑有光泽无裂纹还防水;并且,是古铜色的,挺美观。这也算是从前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底层人民才智的体现吧!
当年我因为自己知道晚了,没能也弄回家一盆如法抹抹锅台和窗台,曾很沮丧。
直至2000年以后,不论是谁,只要坐在行驶于长江以北的列车上,当列车接近城市时,也不论那城市大或小,几乎总会看到铁路两旁有油毡房顶的低矮土坯房,而那些房顶上压着整砖或半砖,少则几块,多则十几块;像一盘盘象棋残局。倘无砖压着,油毡怕是早已被风刮到爪哇国去了。
当年之中国,住那种土坯房的城里人家不在少数。近二十年内,才逐渐从城市消除了。
而我成为知青后,最喜欢的劳动是抹墙。将一叉子和得不干不稀恰到好处的抹墙泥接在托板上,一抹子又一抹子厚薄均匀地抹上墙,会使我觉得那活儿干得特痛快,特舒心,特过瘾——因为我下乡前,从没能那么痛快地抹过自家的墙。我尤其爱干以水泥掺沙子来砌什么抹哪里的活儿——水泥呀,用正式的抹子而不是炒菜的铲子完成劳动任务,可是我下乡前梦里常梦到的情形呀!用瓦刀而不是斧头砍砖,一瓦刀砍下去,如果手中砖恰合本意地齐整地应声断开,那感觉是很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