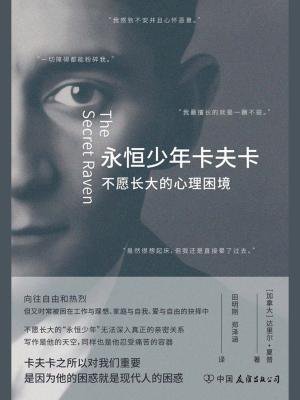女性与婚姻
卡夫卡对女性的态度表现得极为矛盾。他可以很轻松地就成为女性的知己好友,与此同时,他又害怕着她们。“女人是陷阱,从各方面窥视着人,想拉他就范。”就引自卡夫卡说过的话。
卡夫卡仅有的几次性体验显然都没有成功过。1916年7月,他写道:
除了两次例外,一次在楚克曼特尔(Zuckmantel)(但在那里她是一个女人,而我是个毛头小伙子);一次在里瓦(Riva)(但在那里她是半个孩子,而我完全忘乎所以,处于全方位的病态之中),我实际上从未同一个女人亲密过。
1916年,卡夫卡的另一则日记表明,他知道“阿尼玛效应”(anima fascinations)的驱动力(和短暂性):
不顾一切的头痛、失眠、头发花白、绝望而与姑娘们在一起,那是怎样地误入歧途啊。我算算:自夏天以来至少有6个。我无法抗拒欣赏一位值得欣赏的女子,直至欣赏得精疲力竭地去爱她。如果我不顺从的话,我的舌头确实就会从嘴里被拉出来。
很有可能,卡夫卡就是性无能。“你带着这个性别的馈赠做了些什么呢?”1922年1月,他这样自问道,“它失败了,人们最终会说,这将是一切。”马克斯·勃罗德提到卡夫卡偶尔会去逛妓院,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带着玩味的念头:
我有意穿过有妓女来往的街道。从她们身边走过令我感到诱惑,那种与一个妓女同走的可能性是渺茫的,但也绝非不可能。
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写下一封信讲述了他与女性(一个妓女)的第一次性爱经历。谈到这一点时,他感觉松了一口气,因为“再没有比这更糟糕、更淫乱的经历了”。总的来说,他对性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性交是对在一起幸福的惩罚。”
然而对于婚姻,卡夫卡却怀有神圣的憧憬。“这里没有人能从整体上了解我。”在一则日记开头里出现了这样熟悉的字眼。“如果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比如一个妻子,这就是说在各方面有了依靠,有了上帝。”在1919年年底,卡夫卡写下著名的《致父亲》( Letter to His Father )。信中他写道: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将要来到的孩子,并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1922年的日记中,出现这样的描述:
没有结束的、深沉的、温暖的、解脱的幸福,坐到他孩子的摇篮旁边,面对着母亲。
这里面也有一点儿这样的感觉:这跟你再没有什么关系,除非你需要这个。与此相反,没有孩子的感觉:这总视你而定,不管你想不想,每时每刻直至结束,每一个撕扯神经的时刻,这经常是视你而定,而且没有结果。西绪弗斯(Sisyphus)
 是一个单身汉。
是一个单身汉。
显然,卡夫卡的艺术创作就是他孤独的产物,但这种孤独的创作是有缺陷的。只不过卡夫卡每次想要结婚和“建立一个家庭”的念头都因其内心的冲突而失败了。
卡夫卡曾经与一个年轻的柏林女孩菲莉丝·鲍威尔(Felice Bauer)维持了长达五年的婚约,两人一度迈入婚姻的殿堂。1912年8月,他第一次遇见这个女孩。这段爱情体验给彼此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两人在交往期间都出现了巨大的情绪波动。1914年6月:“确信F.
 的必要性。”1916年7月:“一起生活的劳累。”他们订过婚,取消了一次,再订婚,最终还是取消了婚约。1913年8月,他给马克斯·勃罗德写信道:“我爱她,用尽了我一切爱的本能,可我的爱也在恐惧和自责中几近埋葬。”1916年,他写信给女孩,说:
的必要性。”1916年7月:“一起生活的劳累。”他们订过婚,取消了一次,再订婚,最终还是取消了婚约。1913年8月,他给马克斯·勃罗德写信道:“我爱她,用尽了我一切爱的本能,可我的爱也在恐惧和自责中几近埋葬。”1916年,他写信给女孩,说:
现在你属于我;我想,任何童话中所描述的为得到自己心上人所付出的努力,都比不上我为了得到你而付出的努力,不只过去,现在是这样,而且永远会这样。你属于我。
但这些都无济于事,1917年,当卡夫卡确诊肺结核时,这段几近辗转的恋爱关系最终迎来彻底的告别(卡夫卡做这个决定的瞬间还感到些许轻松)。卡夫卡在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及这个柏林女孩时,就对这段恋情做了总结:“五年来,我们相互抽打的鞭子已经打了不少结。”
密伦娜·耶辛斯卡(Milena Jesenska)曾是卡夫卡早期短篇小说的翻译员,负责将他的小说翻译成捷克语。在那两年里,卡夫卡曾经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问自己是否能与这位女子共度一生。实际上,他们真正见面的次数仅有两次,但卡夫卡写给密伦娜的情信却有上百封,信里充斥了绝望、喜悦、自伤和自我贬低。(马克斯·勃罗德表示:“在我眼里,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情书。”)密伦娜那时已经嫁与他人,不幸的婚姻生活仍未能让她下定决心离开现任丈夫。卡夫卡内心时常为此感到不安,他无法满足于这种恋爱状态。很快,卡夫卡的一封信就将两人的爱情之火扑灭:
我们在维也纳度过的那段共同生活的日子并非真实,这种美好只是一时的幻想,而非真实的存在。我已经“越过自己的围栏”,拼命用双手抓住带刺的围栏顶,摔下来时,双手撕裂,鲜血淋漓。当然也会有其他可能,让我们能共度一生,毕竟这世界充满了各种可能,可惜我还没有找到。
卡夫卡的两段生命中最重要的恋情都中途夭折,还有数次短暂恋爱经历的不幸告终都一一证实他内心的想法,即自己“无法与他人在精神上达成结合”:
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
1911年12月,早在卡夫卡还未明确意识到自己无法娶妻前,他就表达过对拥有自己孩子的强烈渴望,并在不知不觉中预见了他悲惨的未来:
一个不应该有孩子的不幸的人将自己可怕地禁锢在自己的不幸中。哪儿也没有一个更新的希望,哪儿也没有得到幸运之星帮助的希望。他必须带着这种不幸去走自己的路,要是他的圈子兜完了,就得知足,并不要继续纠缠这个不幸,而应该去试试,他遭受的这种不幸是不是在较长的一段路上因换了一种身体与时间的情况会丢失,或竟而会带来好运。
直到卡夫卡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才从一位女子身上体会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些许满足。这位女子就是多拉·狄曼特(Dora Dymant),她还很年轻,只有不到卡夫卡年龄的一半大。1923年的夏天,卡夫卡在波罗的海的海滨度假胜地米里茨湖(Müritz)度假时,邂逅了多拉。从此,他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回到布拉格后,卡夫卡毅然斩断所有束缚,奋不顾身地同她一起在柏林生活。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最终死在了多拉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