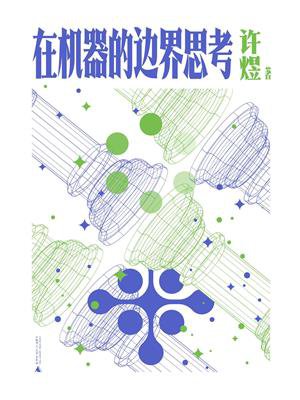4 节奏与技术
回到兰波就是回到节奏问题,让存在存在。海德格尔的新颖之处在于看到了节奏引向沉寂的可能性——这是对“暴力”一词的替代,在那里存在于与存在者的结合中揭示自身,即存在的疏朗(
Lichtung
)。让我们再次引用海德格尔向阿尔基罗库斯借用的节奏定义,“然而,要认识到,一种关系维系着人”。诗歌准备了怡合(
Gefüge
),由作品中的节奏所带出的关系(
Verhältnis
)抵达了
fügende Gefüge
——一种持存的强制力。这些关系驱使我们退后并让沉寂显现。加勒里引用了兰波的诗歌《永恒》(“L'éternité”),以之作为海德格尔的四方域的反面,我们可以把这种沉寂和接缝看作海德格尔所提出的
 。
。
再次找到的是
( Elle est retrouvée. )
什么?——永恒。
( Quoi?—L'éternité. )
是大海的离去
( C'est la mer allée )
与阳光同逝。
( Avec le soleil. )
《永恒》展示了一个海洋随着阳光而远去的场景。在这个寻找行动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宁静作为答案。诗的节奏导向就在我们眼前的 未知 ,它超越了所有的规则与人类的 正义 。它也强制此在顺从于一个运动结构,即随着阳光运动。在疏朗或事发中,海德格尔可以说理解了由节奏所引向的揭示,其中历史的此在不仅展示了人类的历史,而且展示了存在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能再引用海德格尔的论述,因为他没有讨论兰波的诗。在诗的节奏中,我们能够发现一种转换,它打开了一个世界,呈现给我们新的结构和力量。我们能够从没有侵犯性的暴力的角度来理解它吗?要详细阐述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海德格尔在《词语》中对格奥尔格诗歌的分析,这首诗最后的诗节吸引了海德格尔:
所以我放弃了,而且忧伤地看见:
( so lernt ich traurig den verzicht: )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 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 )
要学会这种放弃,诗人非常悲痛:在词语破碎的地方,无物存在。他这样说意味着什么?这仅仅是意味着,当词语与事物间直接的对应关系破裂时,事物就不复存在吗?海德格尔立即拒绝道:“绝非这样简单。”为什么诗人认识到这一点后很悲伤?
Gebricht
,源于
gebrechen
,意为缺少某物。海德格尔说,这个词意味着“错失”(
fehlen
)。如果这个词漏掉了与之相对应的事物的话,还有能被保持的关系吗?还是不再有任何关系(
Ver-Hältnis
)?诗人是忧伤的,因为词语必定要支配物,词语是物的基础,这已成为一种规定。语义学与事物间的关系,是形式逻辑也是λóγο
 (逻各斯)的核心。但是,海德格尔是想揭示λóγο
(逻各斯)的核心。但是,海德格尔是想揭示λóγο
 的另一层含义,它不是那些制约理性的规则,而是处于
的另一层含义,它不是那些制约理性的规则,而是处于
 (言说)中。
(言说)中。
 ,即摆出/摆在面前并聚集,它与今天的含义并不相同,但它源于言说。当这个词语没有与这个事物相对应时,也就是其自身敞开之时,这个词语便不再支配这个事物,这个词语让事物作为事物存在(
das Wort ein Ding als Ding sein läßt
)。海德格尔参照了古德语词
Bedingen
,一个歌德也用过的词。如果在其逻辑意义中,词与物的关系是
Bedingung
(条件),词语建基事物,那么就
Bedingnis
而言,这个词语不会建基这个事物,而是让这个事物作为事物本身而显现。如果我们现在将
fehlen
(错失)理解为一个要去触发即将到来的转变的信息,那么在这个转变中,我们注意到,诗歌节奏通过打破最普遍最熟悉的惯例,释放出对诡异的压抑(正如谢林[Schelling]所说)。
(2)
在古希腊,语言的节奏与音乐的节奏是被分开的,仅有的重叠是在诗句中,希腊时代的
此在
吟唱着它们。诗歌将成为
en avant
(超前)的,因为作为词语与事物间的和谐的节奏不再被保持。诗歌使节奏处于一种不同的方式中,当我们想抓住它时,它总是在前面,而我们最终处于沉寂之中,处于诡异之中。节奏的个体化以产生连接(
Fugen
)开始,它产生了由这位重要诗人调制的结构(
Fügungen
),一种是嵌入的(
einfügen
),一种是顺从的(
sich fügen
)。
,即摆出/摆在面前并聚集,它与今天的含义并不相同,但它源于言说。当这个词语没有与这个事物相对应时,也就是其自身敞开之时,这个词语便不再支配这个事物,这个词语让事物作为事物存在(
das Wort ein Ding als Ding sein läßt
)。海德格尔参照了古德语词
Bedingen
,一个歌德也用过的词。如果在其逻辑意义中,词与物的关系是
Bedingung
(条件),词语建基事物,那么就
Bedingnis
而言,这个词语不会建基这个事物,而是让这个事物作为事物本身而显现。如果我们现在将
fehlen
(错失)理解为一个要去触发即将到来的转变的信息,那么在这个转变中,我们注意到,诗歌节奏通过打破最普遍最熟悉的惯例,释放出对诡异的压抑(正如谢林[Schelling]所说)。
(2)
在古希腊,语言的节奏与音乐的节奏是被分开的,仅有的重叠是在诗句中,希腊时代的
此在
吟唱着它们。诗歌将成为
en avant
(超前)的,因为作为词语与事物间的和谐的节奏不再被保持。诗歌使节奏处于一种不同的方式中,当我们想抓住它时,它总是在前面,而我们最终处于沉寂之中,处于诡异之中。节奏的个体化以产生连接(
Fugen
)开始,它产生了由这位重要诗人调制的结构(
Fügungen
),一种是嵌入的(
einfügen
),一种是顺从的(
sich fügen
)。
现代技术能够担得起诗歌揭示诡异的任务,并为
Fuge
(接缝)-
Fügung
(机缘搭配)-
Einfügung
(嵌进)做准备吗?海德格尔在《兰波未死》中向诗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未来诗人之所说,是否会建构于此关系的怡合之上,并且同时为人在大地上准备一个新的栖居之所?”
 这个问题似乎也适用于现代技术,然而,海德格尔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因为语言才是他的战场。1969年,在德国电视二台(ZDF)为祝贺海德格尔80岁生日而制作的节目中,作为对原子弹和现代技术危机的回应,海德格尔在与理查德·威瑟(Richard Wisser)的对谈中说道:
这个问题似乎也适用于现代技术,然而,海德格尔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因为语言才是他的战场。1969年,在德国电视二台(ZDF)为祝贺海德格尔80岁生日而制作的节目中,作为对原子弹和现代技术危机的回应,海德格尔在与理查德·威瑟(Richard Wisser)的对谈中说道:
我在技术里看到,也就是从其本质意义上,人类被一种力量(
Macht
)控制,这股力量改变了他,而面对这股力量时他不再自由——某种东西宣告了它的存在,那是存在(Being)与人类之间的一种关系(
Bezug
)。某一天,本来隐匿于技术本质中的这种关系可能会得到揭示。这会发生吗?我不知道!然而,我在技术的本质里看到神秘的所在(
Geheimnis
),我称之为“事发/事件
”(Ereignis,
event)——根据你的推论,不是要对技术进行抵制或谴责,而是要去理解技术的本质和技术世界。对我而言,只要人们在哲学上仍然逗留在主客关系中,这种去蔽就不会发生。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理解技术的本质。

使这个事件能够发生的条件是未知的。然而,这种未知授权于诗与哲学,没有它们,一切都将沦为科学,或成为上文最后一句提到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诗相比,技术在调节节奏方面更有力量,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里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法国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安德烈·勒罗伊-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在其著作《话语与姿势》(
Speech and Gesture
)的下半部中致力于研究节奏问题。他将节奏看成一种给予我们诸如时间、空间这样的概念的力量,以及在人群中产生某种姿态与习惯的力量。根据勒罗伊-古汉的看法,技术的节奏“将野性的自然转变为人化(hominization)的器具”
 。然而,这种技术的节奏在自动化时代被改变了,它变成了一种同步的力量,逐步去除了所有的自由与想象。他哀叹道:“今天,个体都被一种节奏性渗透和制约,这种节奏性几乎已经到达了总体机械性(与人化相反)的阶段。形象主义(figuralism)的危机是机械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结果。”
。然而,这种技术的节奏在自动化时代被改变了,它变成了一种同步的力量,逐步去除了所有的自由与想象。他哀叹道:“今天,个体都被一种节奏性渗透和制约,这种节奏性几乎已经到达了总体机械性(与人化相反)的阶段。形象主义(figuralism)的危机是机械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结果。”
 像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一样,勒罗伊-古汉也看到了现代技术的危机,不过他是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而海德格尔则是从存有-历史的(onto-historical)视角出发。这种有关技术节奏之危险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在西蒙东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中找到:
像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一样,勒罗伊-古汉也看到了现代技术的危机,不过他是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而海德格尔则是从存有-历史的(onto-historical)视角出发。这种有关技术节奏之危险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在西蒙东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中找到:
工业动力阶段,状况发生了深刻改变……工人处于由机器节奏进行度量的网络之中,处于一系列使主体被置于外部的运动之中,一个完全的“技术去文化作用”的阶段出现了,同时失去了对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和舒适尺度的组合的归属感。

我们能看到,在西蒙东的描述中,节奏实际上仅仅被描述为一种纯粹的模式重复,正如我们仍在某些智能手机工厂中看到的那样。但也正是这种和技术趋势及与之相伴的偶然性密切相关的新可能性,要求对节奏和技术进行重新评估,因为人们认为技术程序不再能够提供一种节奏的多样化,进而有机与无机的共鸣不再是人化而是自动化。
 在这种转变中,勒罗伊-古汉等人注意到,对技术的节奏问题的关注从形而上学转向了政治和实用主义。
在这种转变中,勒罗伊-古汉等人注意到,对技术的节奏问题的关注从形而上学转向了政治和实用主义。
现代技术的拯救力量似乎并不来自那些关于无处不在的计算或智能物的论述,这些论述旨在调控一个完全自动化的和上手(ready-to-hand)的环境。也许我们可以效仿谢林,称其为“对诡异的压抑”(suppression of the uncanny)。如果海德格尔对于现代技术的巨大神秘性(
Geheimnis
)的想象及其去蔽的可能性能够实施,那么,节奏问题将成为切入点。这不是为了使技术转向诗,因为技术已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
 (生产),而是在技术的能力及灵活性中为一种机缘搭配做准备,即为一种允许由自身的诡异带来的未知做准备。从西蒙东个体化观点上审视节奏问题,并试图在海德格尔“转向”之后的著作中重构这样一种理解,我们的目的是表明节奏的个体化对于思考一种新的技术进程,甚至是新的本质至关重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简单的现实:技术
不能
以泰然任之的方式来
思考
,因为那样它就不再是技术,而是其他的某些东西——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并且对于技术的延续而言,它必须把节奏视为其自身、任何神秘的存在以及此在的一种可能性。海德格尔所提供的不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一种吁请,正如他在《兰波未死》中吁请诗人那样,我们将其改述为对技术专家的吁请:未来技术人员之所做,是否会建构于此关系的怡合之上,并且同时为人在大地上准备一个新的栖居之所?
(生产),而是在技术的能力及灵活性中为一种机缘搭配做准备,即为一种允许由自身的诡异带来的未知做准备。从西蒙东个体化观点上审视节奏问题,并试图在海德格尔“转向”之后的著作中重构这样一种理解,我们的目的是表明节奏的个体化对于思考一种新的技术进程,甚至是新的本质至关重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简单的现实:技术
不能
以泰然任之的方式来
思考
,因为那样它就不再是技术,而是其他的某些东西——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并且对于技术的延续而言,它必须把节奏视为其自身、任何神秘的存在以及此在的一种可能性。海德格尔所提供的不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一种吁请,正如他在《兰波未死》中吁请诗人那样,我们将其改述为对技术专家的吁请:未来技术人员之所做,是否会建构于此关系的怡合之上,并且同时为人在大地上准备一个新的栖居之所?
(本文译者:朱俊;校对:李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