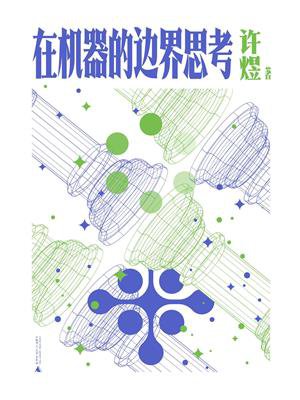个体化的视差:西蒙东与谢林
“没有真正的对立。”这是谢林和西蒙东在个体化(individuation)问题上所认可的第一原理。也即,两者都视对立为解决问题的动力,是向更高的组织秩序跃升的驱力(在这一点上,我们观察到“三”的显现。通过不断克服对立,一个存在者以亚稳态形式个体化并揭示其同一性),即在没有稳定平衡的情况下保持一致性。这个观点不一定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而更像是一种个体化模型,其中存在统一与差异。它是统一的,因为它始终是个体化的一个实例。它是有差异的,因为它既区别于自我,也区别于他者。然而,西蒙东和谢林的区别在于对“三”的本质的认识,这篇文章的任务就是要阐明这一区别。
为什么将西蒙东和谢林联系在一起?只因前者以《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而闻名英语世界,后者以自然哲学而著称?诚然,在法国,西蒙东被当作自然哲学家来解读,尤其是在对《以形式与信息的概念重新思考个体化》一书的讨论中。
(3)
但我们在此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西蒙东思想中是否有自然哲学的问题。相反,我们的目标是呈现西蒙东和谢林的个体化概念之间的视差(parallax)。
 所谓视差,是指在两种不同的视角或透镜下观察同一主体所产生的差异,从而使人更全面地理解问题中的主体。这种视差源自两种不同的认识论透镜,而这两种情况都完全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此外,这个视差随后被重新塑造为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语域,这两种语域不仅采用科学术语,在居有它的同时还对其进行转换。接下来,我打算提取这两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要素:谢林的力(force)概念,以及西蒙东的信息(information)概念。
所谓视差,是指在两种不同的视角或透镜下观察同一主体所产生的差异,从而使人更全面地理解问题中的主体。这种视差源自两种不同的认识论透镜,而这两种情况都完全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的影响;此外,这个视差随后被重新塑造为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语域,这两种语域不仅采用科学术语,在居有它的同时还对其进行转换。接下来,我打算提取这两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要素:谢林的力(force)概念,以及西蒙东的信息(information)概念。
通过“视差”的概念来解读两位哲学家,我们可以理解形而上学思维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不被认识论限制,而是将认识论作为支点,把自然科学中关于存在的问题,转变为对存在基底(ground)的追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也是思维自身的个体化,是同时面对自身和他者的个体化。这里的关键在于让两位思想家联系又分开的岔口:形式的概念。在谢林那里,有机形式扮演着个体化原则的角色,并且变形(metamorphosis)是力量统一性的综合表达。在西蒙东那里,人们发现一种个体化的原则,其既基于他对亚里士多德形质论(hylomorphism)的批判,也基于对格式塔心理学中形式概念的重新诠释,而这就带入了信息这一新的概念。
事实上,西蒙东在《以形式与信息的概念重新思考个体化》附录《个体概念的历史》(“Histoire de la notion d'individu”)中简要地阐述了谢林的个体化概念。在这篇文章中,西蒙东正确地观察到谢林个体化理论的基本公理,即“生命体由一组对立面,以及一种高于对立面的力构成”
 。然而,这篇评论仅有两页篇幅,西蒙东试图在这短短的两页内,总结谢林的多部作品。当然,在西蒙东列出的众多提出个体化定义的哲学家中,谢林只是其中之一。不过,通过参考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差异与重复》(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尤其是关于愚蠢(
bêtise
)的部分的讨论,我们能够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德里达(Derrida)在他关于“先验愚蠢”的研讨班(seminar on transcendental stupidity)上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先理解谢林的基底概念,即同时作为原初基底(
Urgrund
)和无基底(
Ungrund
),就不能理解德勒兹关于愚蠢个体化的主张。德勒兹的确在脚注中引用谢林的《自由论文》(
Freiheitsschrift
)。德里达则引用《差异与重复》中的一段话,来推进此观点:
。然而,这篇评论仅有两页篇幅,西蒙东试图在这短短的两页内,总结谢林的多部作品。当然,在西蒙东列出的众多提出个体化定义的哲学家中,谢林只是其中之一。不过,通过参考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差异与重复》(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尤其是关于愚蠢(
bêtise
)的部分的讨论,我们能够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德里达(Derrida)在他关于“先验愚蠢”的研讨班(seminar on transcendental stupidity)上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先理解谢林的基底概念,即同时作为原初基底(
Urgrund
)和无基底(
Ungrund
),就不能理解德勒兹关于愚蠢个体化的主张。德勒兹的确在脚注中引用谢林的《自由论文》(
Freiheitsschrift
)。德里达则引用《差异与重复》中的一段话,来推进此观点:
在所有形式下行动的个体化与一种在它的作用下并被它带走的纯粹基底不可分割。描述这一基底,以及由这一基底激起的恐惧和诱惑,具有一定难度。撼动基底是最危险的工作,但在一种迟钝的意志的种种昏沉环节中,它亦是最具诱惑力的工作。因为这一基底虽然伴随着个体上升到了表面,但却并不具有某种形式(form)或形象(figure)……尽管它是未规定的东西,但仍然环抱着规定,就像大地之于鞋子。

德里达坚持认为这一段与谢林的基底概念有关,这是对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德勒兹也提到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以及西蒙东从格式塔心理学中借用的“背景-图形隐喻”(ground-figure metaphor)。《差异与重复》整体上受到西蒙东的影响,而当我们考虑到谢林并没有使用“图形”这个词来谈论基底时,西蒙东对这段话的影响则变得更加明显。因此,正是通过德里达对德勒兹的阅读,我们重新发现谢林和西蒙东的相遇。在下文中,我试图在自然科学背景下,勾勒出谢林和西蒙东的个体化的中心原则,这也将澄清“三”的概念。本文分为三部分:前两部分将分别探讨谢林和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我们将在最后部分中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