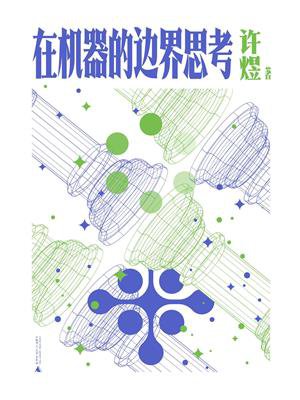1 谢林的个体化:个体化作为对立的承载者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在上述讨论中使用的德语词
Vereinzelung
,直译为“独特化”(singularization)或“原子化”(atomization)。这个词语本身并不是谢林在《自由论文》中使用的,而是海德格尔在他的关于谢林的讲座——“谢林:人类自由的本质”(“Schelling: 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中使用的,在该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现实之恶的个体化过程”(“Der Vorgang der Vereinzelung des wirklichen Bösen”)这一部分。当然,当德里达提到谢林时,他很可能是指海德格尔口中的谢林。谢林在其他书中也使用了
Vereinzelung
这个术语,例如在《论世界灵魂》(
Von der Weltseele
)中,他用它来描述原始形式(
Urformen
)的具体化。
 但这绝对不等同于西蒙东从发生论(genesis)意义上理解的个体化。我的讨论仅限于被谢林称为
Individualisierung
(英译:individualization)的概念。对于谢林而言,
Individualisierung
既代表个体化,又代表个化。而西蒙东将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个化(individualization)区分开来。后者被理解为身体专门化和心理图式化。因此,当我们谈论谢林的个体化时,我们指的是德语的
Individualisierung
;而讨论西蒙东的个体化时,我们指的是法语的
individuation
。
但这绝对不等同于西蒙东从发生论(genesis)意义上理解的个体化。我的讨论仅限于被谢林称为
Individualisierung
(英译:individualization)的概念。对于谢林而言,
Individualisierung
既代表个体化,又代表个化。而西蒙东将个体化(individuation)与个化(individualization)区分开来。后者被理解为身体专门化和心理图式化。因此,当我们谈论谢林的个体化时,我们指的是德语的
Individualisierung
;而讨论西蒙东的个体化时,我们指的是法语的
individuation
。
在《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
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中,个体化概念被认为是“自然哲学的最高问题”和“首要问题”。
 研究谢林早期作品的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他在对个体化的看法上的变化。例如,赛维尔·蒂耶特(Xavier Tilliette)在《谢林哲学与个体化问题》(“La Philosophie de Schelling et le problème de l'individuation”)中指出,个体化已经从生物哲学的问题转变为先验哲学的问题。在转向先验哲学的过程中,谢林对个体性(individuality)施加三重限制:(1)共同智能世界的限制;(2)其他智能的限制;(3)个体本身的限制。
研究谢林早期作品的评论者已经注意到他在对个体化的看法上的变化。例如,赛维尔·蒂耶特(Xavier Tilliette)在《谢林哲学与个体化问题》(“La Philosophie de Schelling et le problème de l'individuation”)中指出,个体化已经从生物哲学的问题转变为先验哲学的问题。在转向先验哲学的过程中,谢林对个体性(individuality)施加三重限制:(1)共同智能世界的限制;(2)其他智能的限制;(3)个体本身的限制。
 另一方面,丹尼尔·惠斯勒(Daniel Whistler)也展示了谢林的个体化概念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到《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
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中的变化。在这转变中,谢林拒绝斯宾诺莎(Spinoza)的个体化原则:“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
(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相反,谢林将规定视为一种肯定形式。我们并不是要协调蒂耶特和惠斯勒竞相提出的观点,也不是要详细阐述他们解释的差异。我们只是想表明,要在谢林的著作中概括出一套连贯的个体化理论,存在很大的难度。诚如上述两者所言,在谢林的思想体系中,他对个体化的理解似乎确实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是模糊的。鉴于此疑难,我们的探讨范围限于谢林的早期作品,即从他对柏拉图的《蒂迈欧篇》(
Timaeus
)的评注(1794)到《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1799)。我们仍然可以在蒂耶特和惠斯勒的评论中找到一个原理,即无限蕴含于有限之中,并构成个体化的一般过程。我们想专注于这点,并展示谢林如何使这种主张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发现相一致。更准确地说,谢林如何能够
利用
自然科学的发现来提出这一主张,并同时使其作为哲学个体化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丹尼尔·惠斯勒(Daniel Whistler)也展示了谢林的个体化概念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到《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
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中的变化。在这转变中,谢林拒绝斯宾诺莎(Spinoza)的个体化原则:“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
(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相反,谢林将规定视为一种肯定形式。我们并不是要协调蒂耶特和惠斯勒竞相提出的观点,也不是要详细阐述他们解释的差异。我们只是想表明,要在谢林的著作中概括出一套连贯的个体化理论,存在很大的难度。诚如上述两者所言,在谢林的思想体系中,他对个体化的理解似乎确实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是模糊的。鉴于此疑难,我们的探讨范围限于谢林的早期作品,即从他对柏拉图的《蒂迈欧篇》(
Timaeus
)的评注(1794)到《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1799)。我们仍然可以在蒂耶特和惠斯勒的评论中找到一个原理,即无限蕴含于有限之中,并构成个体化的一般过程。我们想专注于这点,并展示谢林如何使这种主张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发现相一致。更准确地说,谢林如何能够
利用
自然科学的发现来提出这一主张,并同时使其作为哲学个体化的出发点?
在布鲁斯·马修斯(Bruce Matthews)的《谢林的有机哲学:生命作为自由图式》( Schelling's Organic Form of Philosophy : Life as the Schema of Freedom )中,他通过回顾谢林的早期著作,如对《蒂迈欧篇》的评注和《论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 Ü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orm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等,来阐明谢林的个体化模型。回顾早期文本,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柏拉图、康德(Kant)和费希特(Fichte)的影响。例如,在《蒂迈欧篇》的评注中,谢林提出,世界灵魂是个体化的概念模型,而个体化又须理解为基于康德关系范畴中的交互作用( Wechselwirkung )和共同体( Gemeinschaft )的循环(确切地说是递归)形式。灵魂是以循环形式回归自身的无限运动,而这种形式只能作为有限的存在来呈现和把握。在谢林的《蒂迈欧篇》评注中,他还提到苏格拉底在《菲力帕斯篇》( Philebus )中对这一形式的描述:
这一形式是众神赐予人类的礼物,最初是由普罗米修斯通过最纯净的火所给予。因此,古人(比我们更伟大,更接近于众神)留下这个故事,一切事物曾从统一性和多样性(众多性)中涌现,因为它在自身内部统一无限定(
apeiron,
普遍性)和有限(
peras,
统一性):因此,我们也应根据事物的安排,预设并寻找每一客体的理念……是众神教导我们这样思考、学习和教学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矛盾浮现出来,而从这一矛盾中出现了存在的动力。正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他对费希特和谢林物质概念的评论中所言,一块石头“在浪漫主义者眼中,也把自己演绎为生命过程(
Lebensprozess
)的衍生物”
 。这种有机形式的概念与费希特的先验哲学有着暧昧的关系。一方面,它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保持距离,并在自然中找到更普遍的形式;另一方面,它继承作为存在绝对开端的无条件,即自我设定(
Selbstsetzend
)的主体。只有在此条件下,即存在能够自我设定,才能保证其作为绝对的基底。有机形式的自我设定,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物质,同时又作为物质本身构造的原则。这一无限蕴含于有限之中的公理存在于谢林的所有早期自然哲学著作中,也存在于《艺术哲学》(
Philosophie der Kunst
)中,天才能够在有限(
peras
)中刻画无限(
apeiron
),从而带来了崇高的体验。稍后我们将看到,在西蒙东个体化理论中,无限具有不同功能。
。这种有机形式的概念与费希特的先验哲学有着暧昧的关系。一方面,它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保持距离,并在自然中找到更普遍的形式;另一方面,它继承作为存在绝对开端的无条件,即自我设定(
Selbstsetzend
)的主体。只有在此条件下,即存在能够自我设定,才能保证其作为绝对的基底。有机形式的自我设定,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物质,同时又作为物质本身构造的原则。这一无限蕴含于有限之中的公理存在于谢林的所有早期自然哲学著作中,也存在于《艺术哲学》(
Philosophie der Kunst
)中,天才能够在有限(
peras
)中刻画无限(
apeiron
),从而带来了崇高的体验。稍后我们将看到,在西蒙东个体化理论中,无限具有不同功能。
谢林以类似方式阅读康德《判断力批判》(
Critique of Judgment
)中的第64节和第65节。在这两节中,康德以树的部分/整体关系为例,从交互作用和共同体的角度论述生物的有机形式。在《自然哲学的理念》(
Ideas for a Philosophy of Nature
)中,谢林提到康德的这一段落,更具体地提到有机体中绝对个体性的概念:“其部分只能通过整体成为可能,整体不是通过集合而是通过交互成为可能。”
 部分和整体的统一是通过理念而非物质实现的。理念作为“三”,包含两个潜在对立的实体。自然可以被视作一个整体,后来的《论世界灵魂》称之为普遍有机体(
allgemeiner Organismus
)。这是由两个对立概念组成的整体:一方面是机械性(mechanism),它是“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倒退”;另一方面是合目的性(purposiveness),它“独立于机械性、因果关系的同时性”。
部分和整体的统一是通过理念而非物质实现的。理念作为“三”,包含两个潜在对立的实体。自然可以被视作一个整体,后来的《论世界灵魂》称之为普遍有机体(
allgemeiner Organismus
)。这是由两个对立概念组成的整体:一方面是机械性(mechanism),它是“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倒退”;另一方面是合目的性(purposiveness),它“独立于机械性、因果关系的同时性”。
 两者相互对立,但通过理念而得以统一,自然呈现出循环形式,就像柏拉图描述的世界灵魂:
两者相互对立,但通过理念而得以统一,自然呈现出循环形式,就像柏拉图描述的世界灵魂: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极端(机械性和目的性)结合起来,我们就会产生整体合目的性的理念;自然变成一个回归到自身的循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因果关系的序列完全停止,代之以手段和目的的交互作用;个体没有整体就不能成为现实,整体没有个体也不能成为现实。

通过此“三”,其在此是理念的形式,统一并包含这两个极端,我们发现自然和精神之间的同构性(isomorphism)。这种同构性体现在《自然哲学的理念》中的著名陈述中:“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
 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元论的,它们共享一个普遍的个体化模型。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个组织力从何而来?对于早年的谢林而言,将上帝视为创造的答案似乎太容易,他在早期写给黑格尔(Hegel)的一封信中将自己认定为一位斯宾诺莎主义者。似乎在早期,谢林对斯宾诺莎的亲近和对宗教的疏远,使其萌发了自然哲学及后来的思辨物理学的思想。本文的主张是,这种组织力源自力的概念。同样地,稍后我们将在西蒙东那里看到,谢林个体化思想中的组织力则是来自信息的概念。
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元论的,它们共享一个普遍的个体化模型。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个组织力从何而来?对于早年的谢林而言,将上帝视为创造的答案似乎太容易,他在早期写给黑格尔(Hegel)的一封信中将自己认定为一位斯宾诺莎主义者。似乎在早期,谢林对斯宾诺莎的亲近和对宗教的疏远,使其萌发了自然哲学及后来的思辨物理学的思想。本文的主张是,这种组织力源自力的概念。同样地,稍后我们将在西蒙东那里看到,谢林个体化思想中的组织力则是来自信息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