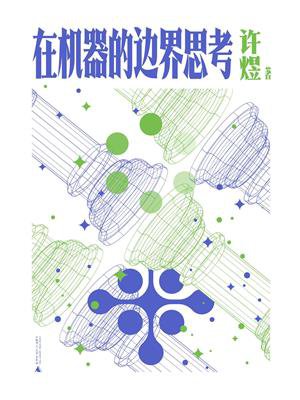2 个体化中力的概念
谢林的力作为形而上学的范畴被提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牛顿(Newton)物理学以及磁力学、电力学和化学的新发现。谢林对这些科学发现领域十分着迷,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能够分析力的相互作用。接下来,我将范围限制在谢林在阅读康德时对力的讨论,以及他对法国-瑞士物理学家乔治-路易·勒·萨奇(Georges-Louis Le Sage)的批判。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中,康德将物质定义为“空间中的运动物”( das Bewegliche im Raum )。就像笛卡尔(Descartes)对海绵的比喻,物质是占据空间的“广延”( res extensa )。在笛卡尔的表述中,物质与广延物等同起来:在宇宙中没有虚空,因为空的空间不存在。康德表述的不同在于,他赋予物质某种笛卡尔那里没有的动力。康德将物质理解为运动的存在,它占据空间不是由于它的实存,而是由于其中的动力:
解释1:物质是可移动的,因为它填满了一个空间。填满一个空间是为了抵抗每一个试图通过其运动穿透某个空间的可移动物体。一个未被填满的空间是一个空虚的空间。

命题1:物质充满一个空间并非通过其单纯的实存,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动力。

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第三部分,康德继续提供“物质的动力说明”,将两种力(斥力和引力)归因于物质。费希特从康德那里借用这两种力,并将它们转化为主体的机制:扩张力,即我(
Schrankenlose,Ich
),以及收缩力,即非我(
Schrankende,Nicht-ich
)。
 谢林则采取第三种路径,他将康德和费希特并列,并在自然和精神的同一(identification)中重新定位这两种力。
谢林则采取第三种路径,他将康德和费希特并列,并在自然和精神的同一(identification)中重新定位这两种力。
事实上,谢林从康德那里借鉴的两种力催生了一种既不能被描述为肯定也不能被描述为否定的动力学。与康德一样,谢林将物质视为引力和斥力的组合;然而,与康德及其他机械主义者,尤其是勒·萨奇(著有《关于机械化学的论文》[
Essay on Mechanistic Chemistry
,1758])不同,谢林怀疑物质是否可以先于力而被预先设定。在《自然哲学的理念》中,他声称“物质不是别的……只是直观中的原始综合(对立力量)的产物”
 。而勒·萨奇的原子论将物质看作可分的粒子,
。而勒·萨奇的原子论将物质看作可分的粒子,
 谢林则提出何为可分的终点。对谢林而言,假定粒子的存在仅仅是理解自然的常识性方法,而非哲学的方式。谢林的反提议是思辨性的:他拒绝将单个粒子的存在当作物质基础,而是坚持一种将自然看作力的发生论。当两种力互相抵消,达到平衡时,则只剩下死物质。
谢林则提出何为可分的终点。对谢林而言,假定粒子的存在仅仅是理解自然的常识性方法,而非哲学的方式。谢林的反提议是思辨性的:他拒绝将单个粒子的存在当作物质基础,而是坚持一种将自然看作力的发生论。当两种力互相抵消,达到平衡时,则只剩下死物质。
 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果在死物质中不再存在活跃和不平衡的力,那么如何解释我们面前这种对象的实存?答案肯定是:这种死物质不存在于可见自然中,因为它不可能存在。这也是谢林对牛顿关于引力的解释的批评点:牛顿的引力仅仅是吸引力,但谢林则反驳说,仅仅使用吸引力而不用排斥力是一种“科学虚构”,它将“现象本身简化为法则,但并不打算解释它”
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果在死物质中不再存在活跃和不平衡的力,那么如何解释我们面前这种对象的实存?答案肯定是:这种死物质不存在于可见自然中,因为它不可能存在。这也是谢林对牛顿关于引力的解释的批评点:牛顿的引力仅仅是吸引力,但谢林则反驳说,仅仅使用吸引力而不用排斥力是一种“科学虚构”,它将“现象本身简化为法则,但并不打算解释它”
 。然而,只有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力同样不够,谢林接着引入第三种力:重力(
Schwerkraft
)。重力将这两种对立的力包容统一,并将理念带入现实:
。然而,只有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力同样不够,谢林接着引入第三种力:重力(
Schwerkraft
)。重力将这两种对立的力包容统一,并将理念带入现实:
如果康德的扩张力和吸引力(他把我们在此之前称为“阻滞力”的东西命名为“吸引力
”)
只代表原初对立,那么他无法仅用两种力量构造物质,他仍然需要第三种力量来解决对立。对我们而言,这个力可以在普遍的无差别(indifference)中,或在重力中寻找。

重力是统一性的力,但它不仅仅是众多综合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是绝对同一性的表象,是物质和理念之间的无差别。
 因此,我们需要记住,这种无差别不是所有力的抵消,也不是虚空;相反,它是普遍性在特殊性(如沙子)或特殊性在普遍性(如液体)中的完全凝聚。在重力中表现的绝对同一性不涉及存在,而是涉及存在基底本身。在《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特别是在重力和光的关系中:前者是逃逸(
entflieht
)进夜晚的黑色基底、曙光乍现之处的夜晚。
因此,我们需要记住,这种无差别不是所有力的抵消,也不是虚空;相反,它是普遍性在特殊性(如沙子)或特殊性在普遍性(如液体)中的完全凝聚。在重力中表现的绝对同一性不涉及存在,而是涉及存在基底本身。在《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特别是在重力和光的关系中:前者是逃逸(
entflieht
)进夜晚的黑色基底、曙光乍现之处的夜晚。

这种力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范式在有机体的概念中也能找到。生命的出现不能仅通过化学作用解释,尽管正是化学作用产生有机自然所必需的无机自然。谢林承认化学作用是唯一可把握的规定性形式(
bestimmte Form
)。
 在讨论生命原则时,谢林正面回应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的构形驱力(
Bildungstrieb
)概念——当然这也是康德第三批判中的关键概念。
在讨论生命原则时,谢林正面回应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的构形驱力(
Bildungstrieb
)概念——当然这也是康德第三批判中的关键概念。
 谢林对构形驱力的批评是,它
本身
不能作为生命的本因。谢林认为构形驱力“只是自然一切形态中,自由与合法则性(
Gesetzmäßigkeit
)每一次原初统一的表达(
Ausdruck
),而不是统一本身的解释基底(
Erklärungsgrund
)”
谢林对构形驱力的批评是,它
本身
不能作为生命的本因。谢林认为构形驱力“只是自然一切形态中,自由与合法则性(
Gesetzmäßigkeit
)每一次原初统一的表达(
Ausdruck
),而不是统一本身的解释基底(
Erklärungsgrund
)”
 。让我们重申以上的论点:如果谢林拒绝构形驱力,那是因为生命需要两种力以及一种能持留矛盾且力求浑然无别的“三”。自然还有许多基本原则是个体化过程的基础。它们不是物质性的原则,而是可以用两种对立的趋势来假设的抽象原则,即作为肯定原则的统一,以及作为否定原则的差异。在《论世界灵魂》中,谢林指出布朗关于动物应激性(
tierische Erregbarkeit
)和激动潜能(
erregende Potenzen
)的理论对应于生命的肯定性和否定性原则。
。让我们重申以上的论点:如果谢林拒绝构形驱力,那是因为生命需要两种力以及一种能持留矛盾且力求浑然无别的“三”。自然还有许多基本原则是个体化过程的基础。它们不是物质性的原则,而是可以用两种对立的趋势来假设的抽象原则,即作为肯定原则的统一,以及作为否定原则的差异。在《论世界灵魂》中,谢林指出布朗关于动物应激性(
tierische Erregbarkeit
)和激动潜能(
erregende Potenzen
)的理论对应于生命的肯定性和否定性原则。
在《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中,谢林对“三”的概念运用最为明显。两种对立的力产生一个包容它们的“三”。最清晰的例子是漩涡。想象一下生产性力量就像流动的溪流,当它遇到障碍物(例如石头)时,它会受到阻碍,产生漩涡。然而,这不是一个稳定的漩涡,因为漩涡不断根据时间轴和水流中的力量而变化:
自然的每一原初产物,每一有机体,都是这样的漩涡。漩涡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变形——每时每刻都是再生产。因此,自然任何产物都并非固定,而是通过整个自然的力在每一瞬间重新产生。(我们并没有看到自然产物的存在,只是看到它们不断被再生产
。)
自然作为整体,共同创造着每一产物。

漩涡的视觉例子展示自然的无限性生成,以及它在有限存在者中的显现,并将它们置于系统中,在此系统中,这种有限存在者为自然的力(无论是诞生之力还是腐堕之力)所携带。自然生产性的力并非同质的,而是由多种基本的质(qualities)或作用力(actants)组成。
 作用力根据不同程度的构成力,不断规定着各种事物的变形过程,如水晶、树叶、人类。换句话说,自然的凝聚力并不是单向行进,而始终是由多个作用力平衡的复合力,就如普罗透斯(Proteus)般:
作用力根据不同程度的构成力,不断规定着各种事物的变形过程,如水晶、树叶、人类。换句话说,自然的凝聚力并不是单向行进,而始终是由多个作用力平衡的复合力,就如普罗透斯(Proteus)般:
普罗透斯把所有的质都纳入自己的循环之中,逐渐同化它们,因为它们可能是无限多样的。而且,历经无数次尝试,他将寻求一种比例,在这种比例中,自然所有作用力都可以在一个集体的产物中实现普遍统一。

对立的性的发展是从简单有机体到复杂有机体的个体化运动的表现。谢林写道:“急剧个体化的时刻,实际上是完整的性发育的第一时刻,是产物的完全差异。”
 蒂耶特指出,在谢林的一些边注(可能写于1799年之后)中,对立的性的发展是自然所厌恶的,同时也是自然不可避免的命运。
蒂耶特指出,在谢林的一些边注(可能写于1799年之后)中,对立的性的发展是自然所厌恶的,同时也是自然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看到“迈向个体化的最后一步”
在这里,我们看到“迈向个体化的最后一步”
 中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存在于个体中,而是存在于种类之中,个体只是种类的工具。个体消失,而种类仍然存在。
中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存在于个体中,而是存在于种类之中,个体只是种类的工具。个体消失,而种类仍然存在。
 在《哲学自然体系初步纲要》的引言中,谢林说:
在《哲学自然体系初步纲要》的引言中,谢林说:
自然是最懒惰的动物,它诅咒分离,因为分离强加给活动必要性。自然活动起来,只为摆脱这种强迫。对立面必须永远回避,以便永远找寻对方;永远找寻,以便永远找不到对方。只有在这种矛盾中,自然的一切活动才有基底。

以上内容旨在阐述谢林个体化理论的基本公理。它主要基于两种看似对立的力量之间的矛盾,产生既是容器又是统一者的“三”。个体化通过这两种力的发展而实现:承载这种对立的力标志着它的个体性。个体化通过动力形式,不断产生自然生产性的力,来维持张力和对立。然而,有限性中的无限性、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以及复多性中的统一性,并不会导致静止的存在。自然不会止步于统一性,而是不断回归自身,破坏或重建现有的亚稳态。
有了谢林的个体化概念,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德里达对于先验愚蠢的讨论。如我们所见,谢林和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在此交汇。德里达对谢林的引用,来自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的《思想的形象》(“The Image of Thought”)章节中对谢林的引用。在这里,德勒兹写道:“谢林对恶(愚蠢和残暴)的讨论很精彩,恶的来源在于它好像基底一样变得独立,而整个恶的历史都跟随此原则。”
 基底变得独立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脱离了形式。德里达引用德勒兹的说法:“动物却凭借自身的明确形式提防着这一基底。”
基底变得独立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脱离了形式。德里达引用德勒兹的说法:“动物却凭借自身的明确形式提防着这一基底。”
 并且质疑了这个似乎凭空出现的“模糊”和“不清晰”的句子背后的深意。德里达问道:“难道我们不能说人也有明确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警告他免受基底的影响,也就是说,抵抗愚蠢吗?”
并且质疑了这个似乎凭空出现的“模糊”和“不清晰”的句子背后的深意。德里达问道:“难道我们不能说人也有明确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警告他免受基底的影响,也就是说,抵抗愚蠢吗?”
 德里达在这里将愚蠢和基底等同起来是有问题的,因为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的接下来的句子中(德里达当然读过但没有引用),已经提供了否定的答案:“愚蠢既不是基底也不是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个体化在这种关系中使基底上升,而又不能给予基底以形式。”
德里达在这里将愚蠢和基底等同起来是有问题的,因为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的接下来的句子中(德里达当然读过但没有引用),已经提供了否定的答案:“愚蠢既不是基底也不是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个体化在这种关系中使基底上升,而又不能给予基底以形式。”
 这意味着基底和形式之间的关系颠倒了,基底不能再赋予形式,思维不能再个体化。它将自己“去个体化”(disindividuates)。但是,如果不讨论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就不能理解这一点。
这意味着基底和形式之间的关系颠倒了,基底不能再赋予形式,思维不能再个体化。它将自己“去个体化”(disindividuates)。但是,如果不讨论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就不能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