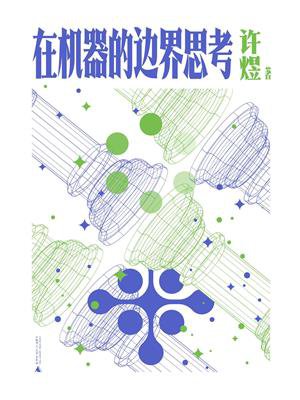3 张力与回响
与其局限于海德格尔的《物》,我们不如回溯他1936至1949年间更早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张力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并没有被忽视,而它直接关系到对于存在的连接或怡合(
Fuge des Seyns
)的理解。下列段落中,我主要参照海德格尔1936至1949年间的文本。在《论艺术的问题》(“Zur Frage nach der Kunst”,GA74)中,我们能够看到张力位于艺术作品的核心。海德格尔没有使用词语“张力”(tension),而是采用了
Auseinandersetzung
,意为“争执、对峙”。行动的问题必须从场所(place)出发来着手处理,这向我们展示了此在与空间之间的争执/对峙。海德格尔说:“显然,它与空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与空间的争执/对峙。”
 Auseinandersetzung
(争执、对峙)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立即将这一概念与胡塞尔(Husserl)的
Ineinander
(彼此融会)或
Ineinandersetzung
(交融)概念相比较,因为
Auseinandersetzung
不是统一,而是差异。在《技术与艺术》(“Technik und Kunst ”,GA76)中,我们再次读到关于
Auseinandersetzung
的问题:“用技术手段呈现技术过程并不等同于,也永远不会是艺术与技术的对峙。那么,究竟什么是
Auseinandersetzung
?谁与之对峙,并通过谁与之对峙?”
Auseinandersetzung
(争执、对峙)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立即将这一概念与胡塞尔(Husserl)的
Ineinander
(彼此融会)或
Ineinandersetzung
(交融)概念相比较,因为
Auseinandersetzung
不是统一,而是差异。在《技术与艺术》(“Technik und Kunst ”,GA76)中,我们再次读到关于
Auseinandersetzung
的问题:“用技术手段呈现技术过程并不等同于,也永远不会是艺术与技术的对峙。那么,究竟什么是
Auseinandersetzung
?谁与之对峙,并通过谁与之对峙?”

如果说争执/对峙是可取的,并且可以与前个体中的张力相媲美的话,那么,这不正是构成诗作与非诗作之间作品差异的节奏的可能性吗?在《技术与艺术》的第二条笔记中,海德格尔比较了艺术(
Kunst
)和技术(
Technik
),追问道:“在集置的时代,艺术是什么,要如何存在?”他回应道,艺术必须艺术地做出决断,以至“答案就存在于并仅存在于这样的艺术中,在其自身的事发或事件(
Ereignis
)中”
 。艺术品作为被实现出来之物(
Werk als Gewirktes
),它驱使事物工作,海德格尔继续说道:“但是,另一种意思是,产出的作品处于无蔽之中,让存在呈现在眼前(
Vor-liegen-lassen
)。”
。艺术品作为被实现出来之物(
Werk als Gewirktes
),它驱使事物工作,海德格尔继续说道:“但是,另一种意思是,产出的作品处于无蔽之中,让存在呈现在眼前(
Vor-liegen-lassen
)。”
 现在,艺术问题回到了语言问题或逻各斯(λóγο
现在,艺术问题回到了语言问题或逻各斯(λóγο
 )。正如海德格尔在其关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讨论中所揭示的,逻各斯的本质是:让其一起呈现在眼前(
das bei-sammen-vor-liegen-Lassen
)。
)。正如海德格尔在其关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讨论中所揭示的,逻各斯的本质是:让其一起呈现在眼前(
das bei-sammen-vor-liegen-Lassen
)。
如果对于节奏的呈现而言,争执/对峙是其成为可能的条件,那么,这个呈现本身是什么?而它又意味着什么?在对兰波的评论结尾,海德格尔参照了特拉克尔的“沉寂”(
Geschwiegen
)的概念,将其当作对未知的揭示。他说:“这种沉寂是另一种纯粹的中断(
Verstummen
)的沉默。它的不再言说是一种已经在说。”
 沉寂,或者沉静,不能在“缄口不言”中找,而是要在语言中、在逻各斯自身中寻找。沉寂的观点在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尤其是当提及荷尔德林《面包与美酒》(“Brot und Wein”)的一个具体诗节时:
沉寂,或者沉静,不能在“缄口不言”中找,而是要在语言中、在逻各斯自身中寻找。沉寂的观点在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尤其是当提及荷尔德林《面包与美酒》(“Brot und Wein”)的一个具体诗节时:
为什么古老而神圣的剧院也沉寂了,
( Warum schweigen auch sie, die alten heiligen Theatre, )
为什么现在不舞蹈庆祝,不歌颂欢乐?
(
Warum freuet sich den nicht der geweihlte Tanz?)

舞蹈是一种伴随着音乐的有节奏的活动。现在的问题是:沉寂如何能被理解为既是语言也是节奏?我想回到海德格尔1958年的文本《词语》(“Das Wort”)中对格奥尔格诗文的解读。海德格尔在谈到一篇关于沉静的诗时,将节奏定义为:“节奏确实不意味着变动或流动。节奏是寂静的,它连接着歌唱与舞蹈的行动,并由此让我们休憩。节奏馈赠寂静。”
 他继续写道:“在歌曲中我们听到,当我们注意到连接(
Fuge
)时,结构/怡合(
Gefüge
)就会显现自身。”
他继续写道:“在歌曲中我们听到,当我们注意到连接(
Fuge
)时,结构/怡合(
Gefüge
)就会显现自身。”
 现在,节奏成为一种作为机缘搭配(
Fügung
)的结构(
Fuge
)的个体化。
Fügung
和
Fuge
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诗歌产生节奏,并带来一种“提前”——一种沉寂,它揭示出与存在彼此结合的“机缘搭配”,即作为
现在,节奏成为一种作为机缘搭配(
Fügung
)的结构(
Fuge
)的个体化。
Fügung
和
Fuge
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诗歌产生节奏,并带来一种“提前”——一种沉寂,它揭示出与存在彼此结合的“机缘搭配”,即作为
 (真理)的无蔽。早在1935年,在《形而上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GA40)中,海德格尔就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
Antigone
)做了阐释,也尝试解决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在哲学上的对立,即关于存在的思想家与关于生成的思想家之间的对峙,正如伯姆(Boehm)所指明的,在这种阐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试图表明“形而上学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相同”。
(真理)的无蔽。早在1935年,在《形而上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GA40)中,海德格尔就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
Antigone
)做了阐释,也尝试解决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在哲学上的对立,即关于存在的思想家与关于生成的思想家之间的对峙,正如伯姆(Boehm)所指明的,在这种阐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德格尔试图表明“形而上学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相同”。
 海德格尔在他所引用的第一个诗节指出,人类是最诡异的(希腊文:τò δεινóτατον,德译:
das Unheimlichste des Unheimlichen
,或译诡异中最诡异的)。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对于古希腊人而言,δεινóν(诡异者)穿过对立于存在的冲突(
Aus-einander-setzungen des Seins
),存在与生成的张力在这里成为根本性要素。诡异者有两个意思:暴力和威临一切的或骇人的。第一部分是暴力(
Gewalttätigkeit
),或暴力行动(
Gewalt-tätigkeit
),它构成了作为
海德格尔在他所引用的第一个诗节指出,人类是最诡异的(希腊文:τò δεινóτατον,德译:
das Unheimlichste des Unheimlichen
,或译诡异中最诡异的)。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对于古希腊人而言,δεινóν(诡异者)穿过对立于存在的冲突(
Aus-einander-setzungen des Seins
),存在与生成的张力在这里成为根本性要素。诡异者有两个意思:暴力和威临一切的或骇人的。第一部分是暴力(
Gewalttätigkeit
),或暴力行动(
Gewalt-tätigkeit
),它构成了作为
 (技艺)的人类本质。人类就是跨越界线的
此在
,在这样的行动中,此在不再有家,变得无家可归(
un-heimisch
),因而成为诡异者。
(技艺)的人类本质。人类就是跨越界线的
此在
,在这样的行动中,此在不再有家,变得无家可归(
un-heimisch
),因而成为诡异者。
 这种暴力与
这种暴力与
 相关联,后者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技术,而是知识。不过,它是一种导致行动的“知”:
相关联,后者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技术,而是知识。不过,它是一种导致行动的“知”:
我们用合式(
Fug
)来翻译这个词(
dikē
)。这里我们首先从合缝(
Fuge
)与榫合(
Gefüge
)的意义上来领会合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合式领会为机缘搭配(
Fügung
),即威临一切者行使其存在力道的谕令;最后,合式被领会为严丝合缝般的榫合(
fügende Gefüge
),而这一榫合则强逼出适合(
Einfügung
)与顺从(
sich fügen
)。

Fuge
的语词游戏及其派生含义如
Gefüge,Fügung,fügende
Gefüge,Verfügung,sich fügen
在翻译中完全丢失。
 这个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上通常被翻译为“正义”的词,对海德格尔而言首先是一种合缝、一种榫合/怡合,然后指向某物的机缘搭配。那么是谁在指导呢?德语中
glückliche Fügung
常译为“幸运的巧合”,但它并非完全偶然的,而是由一种外在力量所致。最终我们看到一种强制的力量,被强迫者只能屈从,从而成为怡合结构的一部分。用
Fug
替代
Gerechtigkeit
,这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是另一种打开存在问题的尝试,据古希腊人所说,“与
这个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上通常被翻译为“正义”的词,对海德格尔而言首先是一种合缝、一种榫合/怡合,然后指向某物的机缘搭配。那么是谁在指导呢?德语中
glückliche Fügung
常译为“幸运的巧合”,但它并非完全偶然的,而是由一种外在力量所致。最终我们看到一种强制的力量,被强迫者只能屈从,从而成为怡合结构的一部分。用
Fug
替代
Gerechtigkeit
,这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是另一种打开存在问题的尝试,据古希腊人所说,“与
 (正义)相比,拉丁文
iustitia
(公平、正义)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基础,
(正义)相比,拉丁文
iustitia
(公平、正义)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基础,
 源于
源于
 (无蔽、真理)”
(无蔽、真理)”
 。
。
 是威临一切的合式(fittingness)。
是威临一切的合式(fittingness)。
 (技艺)的暴力行动和存在的威临一切(
Übergewältigend
)间的对抗是必然的,因为“历史性的人类此在意味着:其存在被设定为一种裂隙——那存在的过度暴力(
Übergewalt
)显现时所冲破的裂隙,使得裂隙本身在与存在的碰撞中粉碎”
(技艺)的暴力行动和存在的威临一切(
Übergewältigend
)间的对抗是必然的,因为“历史性的人类此在意味着:其存在被设定为一种裂隙——那存在的过度暴力(
Übergewalt
)显现时所冲破的裂隙,使得裂隙本身在与存在的碰撞中粉碎”
 。在这个暴力的戏剧性事件中,人对存在的突袭来自存在以及
。在这个暴力的戏剧性事件中,人对存在的突袭来自存在以及
 (自然)的统治引起的急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迫?因为存在的过度暴力变得威临一切和骇人,从而引发了恐惧和焦虑。在海德格尔看来,
(自然)的统治引起的急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迫?因为存在的过度暴力变得威临一切和骇人,从而引发了恐惧和焦虑。在海德格尔看来,
 (技艺)和
(技艺)和
 (
dikē
,正义)间的这种
Auseinandersetzung
(对峙)能够被理解为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它也完全符合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但需要看清楚,分-合-对峙本质上就是聚合到一起;而合式本质上则是相互对应的东西”
(
dikē
,正义)间的这种
Auseinandersetzung
(对峙)能够被理解为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它也完全符合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但需要看清楚,分-合-对峙本质上就是聚合到一起;而合式本质上则是相互对应的东西”
 。
。
以嵌合作为对
 (
dikē
)的理解,再次在1946年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GA5)中被采用。在那里,海德格尔反对尼采和古典学者赫尔曼·狄尔斯(Hermann Diels)将
(
dikē
)的理解,再次在1946年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GA5)中被采用。在那里,海德格尔反对尼采和古典学者赫尔曼·狄尔斯(Hermann Diels)将
 译为βuβe(审判)或
Strafe
(惩罚),并认为应该将
译为βuβe(审判)或
Strafe
(惩罚),并认为应该将
 译为
Fug
(嵌合,合式),秩序安排(ordering)和严丝合缝的秩序(
fugend-fügende Fug
)。
译为
Fug
(嵌合,合式),秩序安排(ordering)和严丝合缝的秩序(
fugend-fügende Fug
)。

 则译为
Un-fug
(脱节,断裂,失序)。朝向敞开的作为暴力的
则译为
Un-fug
(脱节,断裂,失序)。朝向敞开的作为暴力的
 在该文本中却未被提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猜测,这个文本正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写,而当时海德格尔正因为曾加入纳粹而受到公开的谴责,不得不隐匿这种暴力的必要性。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最后部分,海德格尔问道:“还有救吗?当且唯当有危险时,才有救。当存在自身被推向最极端的程度,当源于存在的遗忘产生逆转的时候,危险就会出现。”
在该文本中却未被提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猜测,这个文本正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写,而当时海德格尔正因为曾加入纳粹而受到公开的谴责,不得不隐匿这种暴力的必要性。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最后部分,海德格尔问道:“还有救吗?当且唯当有危险时,才有救。当存在自身被推向最极端的程度,当源于存在的遗忘产生逆转的时候,危险就会出现。”
 关于危险的问题,海德格尔随后在1953年的《论技术问题》中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提到古代技术的概念完全被现代技术概念给遮蔽了。现代技术由巨大的暴力构成,并使自身远离了存在问题,且使得每一件事物都变成了持存物(
Bestand
),现代技术的本质变成了集置。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危险是对存在的遗忘的最高表现,它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之终结,其中存在已经被完全抽离,而诸存在者都被视作持存物:
关于危险的问题,海德格尔随后在1953年的《论技术问题》中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提到古代技术的概念完全被现代技术概念给遮蔽了。现代技术由巨大的暴力构成,并使自身远离了存在问题,且使得每一件事物都变成了持存物(
Bestand
),现代技术的本质变成了集置。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危险是对存在的遗忘的最高表现,它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之终结,其中存在已经被完全抽离,而诸存在者都被视作持存物:
原子时代正在到来的技术革命浪潮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头晕目眩。终有一天,计算之思将作为唯一的思之方式被接受和实践。

然而,危险是一个新的开端的必要条件,也成为一种拯救力量出现的条件,正如海德格尔引用的荷尔德林诗所示:“急难所在,亦生救渡(
Wo aber Gefahr ist,wachst Das Rettende auch
)。”如果不是一种诗意的栖留与思的话,那么,这种拯救的力量是什么?《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最后一句肯定地回答道:“那么,思必须在存在之谜上作诗。这使得思考的曙光靠近待思之物。”
 海德格尔这时的说法显然是指向技术与诗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在关于诗成为唯一的拯救力量的论述中,诗是某种不同于技术的东西吗?或者,技术也能参与到诗意的
思
中,构成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吗?更确切地说,是
技术性的
吗?让我们回到《形而上学导论》中去发现是否有一种海德格尔想寻回的、由希腊语词
海德格尔这时的说法显然是指向技术与诗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在关于诗成为唯一的拯救力量的论述中,诗是某种不同于技术的东西吗?或者,技术也能参与到诗意的
思
中,构成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吗?更确切地说,是
技术性的
吗?让我们回到《形而上学导论》中去发现是否有一种海德格尔想寻回的、由希腊语词
 构成的原初技术性(technicity)。仅仅有共鸣还不够,因为节奏必须“超前”,共鸣只是启动一种节奏,是使作品成为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的开始。在过度暴力(存在)以及暴力(技术)的交互作用中,一个作为
构成的原初技术性(technicity)。仅仅有共鸣还不够,因为节奏必须“超前”,共鸣只是启动一种节奏,是使作品成为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的开始。在过度暴力(存在)以及暴力(技术)的交互作用中,一个作为
 的宇宙秩序被施加,作为思与存在的结合,如巴门尼德诗所示,这两种力量被综合。被综合之物不是辩证法中的“三”或者是对
的宇宙秩序被施加,作为思与存在的结合,如巴门尼德诗所示,这两种力量被综合。被综合之物不是辩证法中的“三”或者是对
 的颠覆,
的颠覆,
 而是一种使
而是一种使
 (
Un-fug
,脱节)必须认可
(
Un-fug
,脱节)必须认可
 (
Fug
,合式),两者聚拢(beingtogetherness)的境况。在这种争执中所展现的节奏不产生共鸣,而是冲突,由暴力带出了一种对存在之所(
Da
)无尽的揭示。这种对峙有时也可描述为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海德格尔把它与艺术作品的本源联系起来。
(
Fug
,合式),两者聚拢(beingtogetherness)的境况。在这种争执中所展现的节奏不产生共鸣,而是冲突,由暴力带出了一种对存在之所(
Da
)无尽的揭示。这种对峙有时也可描述为世界与大地的争执,海德格尔把它与艺术作品的本源联系起来。
在《哲学论稿》(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GA65)中,与
Fuge
相关的节奏问题变得明朗起来。对于任何可能的事发而言,回响(
Anklang
)与传送(
Zuspiel
)成为基本要素。海德格尔建议去理解这本书旨在阐述的内容,即古希腊初期思想的接缝(joint)或连接/关节(juncture)(
Fuge des anfängliches Denkens
)。海德格尔描述了关于这个任务的三重运动(如下所列)。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序列,榫合/怡合(
Gefüge
)—支配/占有(
Verfügung
)—机缘搭配(
Fügung
),为此在的顺从(
sich fügen
)做准备。海德格尔命名了六种连接,依次为回响(
Anklang
)、传送(
Zuspiel
)、跳跃(
Sprung
)、建基(
Gründung
)、将来者(
Zukünftigen
),以及最后之神(
Der letzte Gott
),而我们能在它们之间找到一种隐匿的交织。
 回响与传送是“土壤与旷野”,它们为纵身飞跃/跳离(
Absprung
)做准备,在跳跃中敞开遮蔽状态而为此在的建基做准备。我们可以根据加勒里和西蒙东的量子跃迁的概念来理解这种跳跃,因为它作为阈值,导致个体化的存在及其环境结构的转变。回响与传送为这种跃迁做准备,直到
Auseinandersetzung
的张力或强度到达某个特定的点。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结构将产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这些连接形成了统一体,它彰显或区分将来者。这个事件召唤着此在站立在最后之神的暗示面前,在神秘力量的面前。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结束部分写出“连接——遵从于召唤的安排,建基
此在
”
回响与传送是“土壤与旷野”,它们为纵身飞跃/跳离(
Absprung
)做准备,在跳跃中敞开遮蔽状态而为此在的建基做准备。我们可以根据加勒里和西蒙东的量子跃迁的概念来理解这种跳跃,因为它作为阈值,导致个体化的存在及其环境结构的转变。回响与传送为这种跃迁做准备,直到
Auseinandersetzung
的张力或强度到达某个特定的点。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结构将产生。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这些连接形成了统一体,它彰显或区分将来者。这个事件召唤着此在站立在最后之神的暗示面前,在神秘力量的面前。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结束部分写出“连接——遵从于召唤的安排,建基
此在
”
 。他继续写道:
。他继续写道:
1.在这种创建中严密的榫合( Gefüge )并没有松动,就好像有争议(在哲学上总是有争论)是不可能的:在其建基于本质的彻底的发育成熟中来理解存在的真理。
2.这里的处置( Verfügung )只允许一个个体穿过一种通路,同时放弃审视其他也许更重要的道路的可能性。
3.这种尝试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榫合/怡合(
Gefüge
)与处置(
Verfügung
)仍然是存在本身,是其真理暗示与抽离的一种机缘搭配(
Fügung
),是对其真理的隐示和抽离,那是某些不可预见之事。

我们能看到,海德格尔在《哲学论稿》(1936-1938)中所处理的和《形而上学导论》(1936)相一致,在《哲学论稿》中
Fuge
变成了思考的主要对象,而《形而上学导论》中所描述的暴力变成了“居有事件”(the event of appropriation)的部分。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声称
 不是艺术,并且既不是技能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而是另一种“知”(
Wissen
)。
不是艺术,并且既不是技能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而是另一种“知”(
Wissen
)。
 这种对知识的重视,策略上允许他将
这种对知识的重视,策略上允许他将
 (无蔽、真理)与
(无蔽、真理)与
 (言说)、
(言说)、
 (逻各斯)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在论及行为/行事的意义(海德格尔在暴力行动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时便遇到了一种模糊性: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有一种没有行为而只有语言的行动?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能够找到的仅有的可能性是
泰然任之
,让存在者保持原样来为神秘之开启做准备。泰然任之是使自身处于做与不做之间,是无为与无欲的思与行动。然而,在这种无为中,
Gewalttätigkeit
(暴力行动)消失了,因为这里既没有暴力(
Gewalt
),也没有行动(
Tätigkeit
)。哲学家休伯特·德莱福斯(Hubert Dreyfus)参照日本文化将海德格尔泰然任之的例子用于当代技术:
(逻各斯)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在论及行为/行事的意义(海德格尔在暴力行动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时便遇到了一种模糊性: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有一种没有行为而只有语言的行动?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能够找到的仅有的可能性是
泰然任之
,让存在者保持原样来为神秘之开启做准备。泰然任之是使自身处于做与不做之间,是无为与无欲的思与行动。然而,在这种无为中,
Gewalttätigkeit
(暴力行动)消失了,因为这里既没有暴力(
Gewalt
),也没有行动(
Tätigkeit
)。哲学家休伯特·德莱福斯(Hubert Dreyfus)参照日本文化将海德格尔泰然任之的例子用于当代技术:
在这里我们再次将眼光放到日本。在当代日本,一种传统的、非技术性的对存在的理解仍然与最先进的高科技生产与消费并存。电视与家中的神像共用一个架子,就像发泡塑料杯与陶瓷杯并存。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能够拥有技术而不需要对存在进行技术性的理解,因此,很显然,对存在的技术性理解能够与技术设备相分离。

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不太确定是否真的是这样,特别是当面临消费主义时,我们传统的“神秘力量”不见了——就在电视旁边消失了。事实上年轻一代完全沉浸在技术物中,并且被数字技术的加速吞没。相反,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策略。从根本上说,“泰然任之”是一种处理技术物的策略,只是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是一种通过回到语言来处理问题的极佳策略,因为那是他的专长。那是一种“非技术性的或非强制的态度”,
 它至少没有意图控制什么,假如不是有意识地要逃离技术的话。语言体现了人类与存在关系的历史。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技术的发展是一种使欧洲人远离希腊源头、远离存在问题的过程。希腊意义上的存在的转变,以及其与来自罗马时期(直到今天)的语言的关系的演变,就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对海德格尔来说,信息学的出现凭借形式逻辑和数学化正在逐步边缘化语言的可能性,并因此加剧了对存在的遗忘。在《兰波未死》的结尾,海德格尔提出了他的忧虑:“语言学与信息学即将对语言造成的摧毁是否不仅会侵蚀诗的优先性,甚至还会侵蚀诗自身特有的可能性?”
它至少没有意图控制什么,假如不是有意识地要逃离技术的话。语言体现了人类与存在关系的历史。对海德格尔而言,现代技术的发展是一种使欧洲人远离希腊源头、远离存在问题的过程。希腊意义上的存在的转变,以及其与来自罗马时期(直到今天)的语言的关系的演变,就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对海德格尔来说,信息学的出现凭借形式逻辑和数学化正在逐步边缘化语言的可能性,并因此加剧了对存在的遗忘。在《兰波未死》的结尾,海德格尔提出了他的忧虑:“语言学与信息学即将对语言造成的摧毁是否不仅会侵蚀诗的优先性,甚至还会侵蚀诗自身特有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继续说道:“当我们询问自身这个问题时,兰波仍然重要,如果诗人和思者仍然留心‘让自己成为对未知的先知’的必要性……兰波诗所说的东西,我们是否足够清晰地听到了它的沉寂(
Geschwiegen
)?”
海德格尔继续说道:“当我们询问自身这个问题时,兰波仍然重要,如果诗人和思者仍然留心‘让自己成为对未知的先知’的必要性……兰波诗所说的东西,我们是否足够清晰地听到了它的沉寂(
Geschwie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