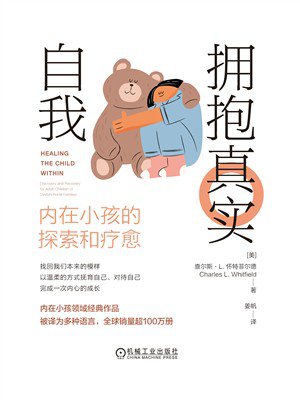第3章
何谓内在小孩
无论感觉有多疏远、多模糊、多陌生,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内在小孩”,那是我们心中的一部分,这部分本质上是生机勃勃的、充满活力的、有创造力的、充实的。那是我们的真实自我——我们本来的模样。霍妮、马斯特森(Masterson)等人将其称为“真实自我”(real self)。有些心理治疗师,包括温尼科特与米勒,将其成为“真我”(true self)。在酒精成瘾与家庭治疗领域内外,有些医生与教育工作者,也称之为“内部小孩”(inner child)。
在父母、其他权威人士与机构(如教育机构、媒体,甚至有的心理治疗机构)的“帮助”下,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压抑与否定自己的内在小孩。一旦我们内心的这一重要部分得不到抚育与自由的表达,就会出现一个虚假的、依赖共生的自我。我会在表3-1中进一步描述这两个部分的自我。
内在小孩或真实自我
在本书中,我会交替使用如下术语:真实自我、真我、内在小孩、内部小孩以及高级自我(Higher Self)。这一部分也被称为我们“最深刻的自我”(Deepest Self)、我们的“内核”(Inner Core;James,Savary,1977)。这些术语指的都是我们内心中的那个核心部分。对这个部分,有一种描述讲得很好:我们感觉最真实、最真诚、最有活力时的自我。表3-1描述了真实自我与相对应的虚假自我各自的一些特征。
表3-1 真实自我与虚假自我的一些特征

(续)

真实自我是自然的、豁达的,充满爱,乐于奉献,善于沟通。真我能够接纳自己与他人。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他都会用心去感受,也会将其表达出来。真实自我会接纳我们的感受,不加以批判,也不感到恐惧,他允许这些感受存在,并将其看作评价与欣赏生活的有效方式。
内在小孩善于表达、充满自信、富有创造力。他可以像孩子一样纯真,而这是一种最高级、最成熟、最具适应性的孩子气。他需要玩耍,需要乐趣。然而,他有时也是脆弱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很开放,乐于信任他人。他会顺应自己、顺应他人,也会顺应世界的自然之道。但就真正意义上的力量而言(第11、15章会讨论这个话题),他又是强大的。他会适度地放纵自己,乐于接受他人的付出与抚育。对于我们所说的无意识——那个广阔而神秘的领域,他也愿意敞开心胸。他关注我们每天从无意识中接受的信息,如梦境、挣扎与疾病。
由于他总是保持真实,所以能够自由地成长。当虚假自我忘记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的同一性时,真实自我始终会记得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紧密相连。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真实自我也是隐私自我(private self)。我们有时会选择不与人分享内心的感受,谁又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呢?也许是害怕受伤或遭到拒绝。有人估算过,我们平均每天只花15分钟向他人展示真我。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都倾向于将真实自我保密。
当我们的言行和感受“出自”真我,或者我们就是真我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充满活力。我们可能会因受伤、悲伤、内疚或愤怒而感到痛苦,但我们依然感到自己充满活力。或者,我们会因满足、幸福、备受激励或欢欣鼓舞而感到快乐。总而言之,我们倾向于活在当下,感到自己是完整的、圆满的、正常的、真实的、纯粹的、理智的。
从出生到死亡,在我们生命的各个阶段与过渡期,我们的内在小孩都是自然的、流动的。要想做真我,我们不必付出任何努力。他就是原本的样子。如果我们顺其自然,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无须特地付出什么努力。其实,任何努力都是在否认对真实自我的觉察与表达。
虚假自我
与真实自我相反,另一部分的自我通常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紧张、不真实。我会交替使用以下术语:虚假自我(false self)、依赖共生的自我(co-dependent self)、不真实的自我(unauthentic self)或公共自我(public self)。
虚假自我是一种掩饰。他是抑制的、受限的、害怕的。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早期精神分析理论所说的自我(ego)与超我(super-ego),永远处心积虑,自私而吝啬。他心怀嫉妒,爱挑剔、理想主义、喜欢责备他人、苛求完美。
虚假自我与真我疏离,始终以他人为导向,关注别人想要他成为的样子,并且过度顺从。他付出的爱是有条件的。他会掩饰、隐藏或否认自己的情绪。他还会编造虚假的感受,比如在听到“你好吗”的时候,我们总是敷衍地答道“我还好”。这种迅速的反应往往是必要而有用的,能帮助我们免于意识到虚假自我的存在,这种意识会让我们感到害怕。虚假自我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何感受,也可能知道自己的感受,但会将感受贬低为“错误的”或“糟糕的”。
虚假自我缺乏适当的自信与果断(就像真实自我那样),他往往会显得咄咄逼人或消极被动。
用沟通分析中的脚本术语来讲,虚假自我倾向于做“批评的父母”。他不愿玩耍与享乐,假装“坚强”,甚至装出一副“强大”的样子。然而,他的力量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他往往害怕、多疑,而且具有破坏性。
由于虚假自我需要退缩与控制,他便放弃了抚育他人或得到他人抚育的机会。他不会顺其自然。他总是自以为是,试图排斥来自无意识的信息。即便如此,他依然倾向于不断地按照无意识的模式行事,而这种模式往往会带来痛苦。因为他常常忘记我们的同一性,所以会感到很孤立。他还是我们的公共自我,即我们所认为的别人对我们的期望,甚至还会发展成我们对自己的期望。
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扮演虚假自我的角色时,会感到不舒服、麻木、空虚,或者处于一种做作而拘束的状态。我们感觉自己不真实、不完整、不纯粹,甚至失去了理智。在某些层面上,我们感觉有些东西不对劲,有些东西是缺失的。
矛盾的是,我们往往觉得虚假自我是我们的自然状态,我们就“应该”如此。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那种状态成瘾或产生执念了。我们过于习惯虚假自我,以至于做真实自我都会感到内疚,就好像出了问题一样,好像我们不该感到真实而有活力一样。改变对这个问题的想法,都会让人感到恐惧。
这种虚假的、依赖共生的自我似乎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在媒体和日常生活中,这个概念已经被阐述或提及过无数次了。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求生工具、心理病理现象、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以及受损的或防御性自我(Masterson,1985)。它会对自己、他人和亲密关系造成损害。然而,这种概念是一把双刃剑。它有一些用途,但用途有多大?在什么情况下有用?下面这首由查尔斯·C.芬恩(Charles C. Finn)所作的诗描述了我们与虚假自我所做的许多斗争。
听听我没说出口的话
不要被我欺骗,
不要被我的面孔欺骗。
因为我戴着面具,一千张面具,
我害怕摘下面具,
它们没有一张是我真正的面孔。
伪装是我的第二天性,
但请不要上当。
千万不要上当。
我会给你一些假象——
我很有安全感,
我的表面充满了阳光明媚、宁静安详,
自信就是我的名字,沉稳就是我的招牌,
我波澜不惊,我胸有成竹,
我不需要任何人。
但请不要相信我。
我看似从容,但那只是伪装的假象,
总在变化,总在隐藏。
表面之下,没有满足。
表面之下,藏着困惑、恐惧与孤独。
但我恨这感觉。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一想到自己的弱点,我就惊慌失措,害怕原形毕露。
正是为此,我才不顾一切地戴上面具,
装出冷漠世故的外表,
来伪装,
来保护我不受那会心的眼神的伤害。
然而,如果接踵而来的是接纳,是爱,
那个眼神就正是我的救赎,我唯一的希望。
我心知肚明。
我筑起高墙,我作茧自缚,
而那正是唯一能将我从自己的禁锢中解救出来的东西。
唯有那个眼神,能让我相信我不肯相信的事实:
我有价值。
但我不会告诉你这一点。我不敢。我害怕。
我害怕你的眼神之后没有接纳,也没有爱。
我害怕你会看不起我,嘲笑我,
而你的嘲笑会置我于死地。
我害怕我其实一文不值,毫无长处,
我害怕你会看到这一点,然后排斥我。
所以我玩起了我的游戏,我绝望的伪装游戏,
做出自信的样子,
内心颤抖得像个孩子。
于是,金玉其外的面具开始列队游行,
而我的生活只剩下了表象。
我温文尔雅地与你闲谈。
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意义重大的话我却闭口不谈,
绝不提及内心的哭泣。
所以,若我做出惯常的样子,
不要被我说的话所欺骗。
请仔细倾听,试着听听我没说出口的话,
听听我希望能说的话,
听听我为了求生所需要说,却不能说的话。
我不喜欢躲藏。
我不喜欢玩肤浅虚伪的游戏。
我想停止这种游戏。
我想做真实、率真的自己,
但我离不开你的帮助。
请伸出你的手,
即使那似乎是我最不想要的。
只有你能抹去我眼中那空洞的目光。
只有你能将我唤醒。
每当你亲切、温柔、鼓励地待我,
每当你出于关切而努力理解我,
我的心就会开始长出翅膀,
瘦小的翅膀,
羸弱的翅膀,
但依然是飞翔的翅膀!
你的触碰能给我带来感受,
你有力量为我带来生机。
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
我想让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你可以成为造物主,真正的造物主,
能够创造我这个人——
如果你愿意。
只有你能推倒我躲藏的高墙,
只有你能揭开我的面具,
只有你能解救我,
把我从那恐慌和不确定的阴影中,从那孤独的监狱中
释放出来——
如果你愿意。
请你一定要愿意。不要离我而去。
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
长期坚信自己毫无价值,就能筑起坚固的高墙。
你越靠近我,我越可能盲目地反击。
我反抗的正是我所渴求的东西。
但有人告诉我,爱比高墙更坚固,
于是我寄希望于此。
请试着用你有力的双手
推倒这堵高墙,
但请用你温柔的双手
爱抚敏感至极的小孩。
你也许会想,
我到底是谁?
我是你熟悉的人。
因为我是你遇见的每一个男人,
也是你遇见的每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