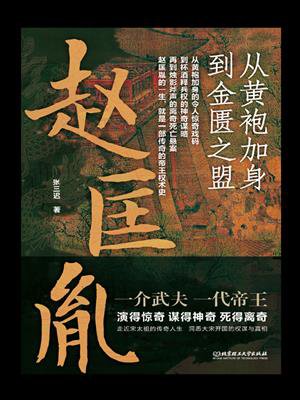第十一章
壮志未酬
柴荣不但领悟了佛学的真谛,更领悟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
乱世当前,想要生存下去,靠佛教的阿弥陀佛、诵经修行,靠孔圣人的仁义道德、之乎者也,都是万万不能的。想要结束乱世,将太平盛世带回人间,必须依靠战争和武力。
这是一个残酷的法则,却是唯一的道路。
于是,在经过一年左右的休整后,柴荣准备再度出征。这一次,他将矛头指向了北方的契丹。
按王朴《平边策》中“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平定天下的流程应该是先攻南唐、后蜀,在平定南方后,再攻取幽燕,取得河东。但柴荣是个懂得因时权变、相机而行的实干家,他认为当前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北伐时机已经成熟,无须死守先南后北之策。
柴荣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后周经过持续多年的改革,经济得到了发展,军力也变得强盛,士气更是持续高涨,已经具备了统一天下的实力;先后攻取后蜀四州和淮南十四州,逼迫两个强敌屈服称臣,南方局势现已稳定,暂无南顾之忧,因此可以集中兵力进行北伐。
反观对手契丹,在辽穆宗耶律璟的昏聩统治下,正处于帝国的衰落阶段。耶律璟堪称契丹史上最极品的皇帝,他作息极不规律,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埋头睡大觉,晚上载歌载舞,宴饮无度,以至通宵达旦,不休不眠,人送绰号“睡王”。
这位“睡王”不但睡功了得,杀人也不眨眼。可能是因为经常颠倒昼夜,导致“睡王”内分泌失调,这位仁兄性格暴躁、喜怒无常,动辄滥杀无辜,身边的近臣整天提心吊胆,人人自危,生怕“睡王”一不高兴就砍了自己的脑袋。
在这个昏庸残暴之主的统治下,契丹皇室内部矛盾重重,各地少数民族叛乱不断,一片乌烟瘴气,国势大不如前。
除了契丹实力下降外,另一个因素也促使柴荣做出了北伐的决定。
《平边策》的作者王朴是位奇才,不但文韬武略了得,还精通阴阳律历、算术及占卜,据传他甚至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柴荣曾向他提过一个问题:“朕究竟能在位多长时间?”
王朴含糊其词地回了一句:“三十年后的事,非臣所能知也。”
这个回答很不明确,甚至可以说答非所问,但满心期待的皇帝却认为王朴的意思是说自己能在位三十年,当即放豪言道:“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三十年足矣!”
好一个三十年足矣!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是柴荣即位的第五年。想要实现第一个十年规划确定的阶段性目标,柴荣还有不到五年的时间。
柴荣认为,要想平定天下,光挑后蜀、南唐这种软柿子捏是没有用的,大周与契丹必有一战。迟战不如早战,缓战不如速战,现在就是决战的最佳时机!
柴荣不再犹豫,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北伐的决断。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二十九日,十万大军取道沧州(今河北沧州),兵分水陆两路。柴荣乘坐龙舟由水路北上,一路畅行无阻,战船舳舻相接,船帆遮云蔽日,连绵数十里,气势恢宏,直指幽州。
千军万马绝尘去,不取幽云誓不还!
踌躇满志的柴荣想到过胜利,想到过失败,却绝对没有料到这次北伐的结局。
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御驾亲征不是他辉煌的起点,而是他生命的终点。与此同时,赵匡胤也是心潮起伏,开始不停地思考。
此次北伐,赵匡胤是绝对支持的。
柴荣这位英明神武的皇帝具备常人难以企及的领袖天赋,从治理国事、处理朝政,到行军作战、锐意改革,从来没有失策过,而赵匡胤要做的就是坚定服从和坚决执行皇帝的决策。
而对赵匡胤这位总能完美执行自己决策的优秀下属,柴荣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北伐幽燕,柴荣任命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跟随自己由水路北上。
赵匡胤十分兴奋,他认为这次北伐又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一旦攻取幽燕,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必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只是张永德、李重进地位相当稳固,牢牢占据着禁军的头两把交椅,除非发生奇迹,否则赵匡胤想要超越这两位大佬,几乎是不可能的。
算了,算了,尽人事,听天命吧!赵匡胤默默告诉自己。
战事的进程进一步坚定了柴荣的信心。仅仅半个月,周军就取得一系列堪称辉煌的战绩。
四月十七日,周军抵达宁州(今河北青县),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投降。
四月二十六日,周军抵达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契丹守将经延辉举城投降。四月二十六日,赵匡胤率先锋抵达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契丹守将姚内斌举城投降。
四月二十九日,契丹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刺史刘楚信举城投降。五月一日,契丹瀛洲(今河北河间)刺史高彦晖举城投降。
短短十数天内,后周以数万步骑,几乎不发一箭一矢、不费一兵一卒,便收复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瀛洲、莫州、宁州等三关三州十七县,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户人口。
关南沦陷让契丹高层患上了后周恐惧症,主和派开始占据上风,有些胆小怕事的大臣甚至主张直接把幽州送给后周,让他们得了好处,自动退兵。
危急时刻,那位醉生梦死的“睡王”耶律璟居然如梦初醒,迸发出了令人称奇的战斗激情,表示自己绝不能放弃幽州,并开始紧急军事动员。
耶律璟一方面任命南京留守(幽州乃契丹之南京析津府)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率城内守军坚决抵御周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动员亲密盟友北汉出兵侵扰周军侧后方;最后,耶律璟决定亲自前往南京督战。
别看耶律璟平时浑浑噩噩,关键时刻头脑却很清醒。他知道幽州的重要性,一旦丢了幽州乃至幽云十六州,契丹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自己连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
在耶律璟的调度下,契丹各部军马迅速集结,从各地赶赴一个共同的目标——南京(今北京)。
与此同时,后周的攻势依然不可阻挡。
五月二日,周军进据固安(今河北固安)。五月五日,周军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
固安、易州两地距幽州仅数十里,占据这两处就好比在幽州城南架设了两门远程大炮,只等柴荣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发动对幽州城的攻击,一场改变历史的大战即将爆发。
然而,这场大战终究没有被引爆,只因为一个人的重病。
上次征讨淮南,生病的是皇后符氏;这次北伐幽州,生病的换成了皇帝柴荣,而两者患病的结局竟也一致。
五月二日,就在后周攻下固安的同一天,一向体魄健壮的柴荣突然发病。
柴荣这次发病毫无征兆,所患何病及病症表现史籍也没有明确记载。有资料说柴荣背部长了“疽囊”(毒疮),不治而亡,并认为这是他废佛导致的因果报应;还有史料记载说柴荣在北伐途中淋过一场大雨,进而有人推断柴荣很可能因此感染风寒,导致不治。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柴荣患病当日情况并不严重,所以他坚持在瓦桥关休息,准备病情好转后再进攻幽州。哪知天不遂人愿,尽管柴荣耐下性子又是吃药又是休息,病情却仍不见好,甚至日趋严重,就连给他看病的御医都无计可施。
柴荣的确是五代十国最伟大的君主,但他也有缺点,那就是在工作上事必躬亲,长期下来,积劳成疾。
早在显德元年初,柴荣亲征取得高平大捷后,就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帝王生涯,经常加班加点处理政务,呕心沥血推进各项改革,频繁御驾亲征领兵作战。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就算铁人也承受不了,更何况是血肉之躯的皇帝。
事实上,有不少大臣对柴荣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有的批评还很直接:“皇帝您英明神武,事无巨细,一概包揽,表面上对国家是好事,实际上却未必。就算尧舜这样的先贤圣君,也要找人分担工作,何况是您呢?皇帝是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哪能凡事都亲力亲为呢?作为皇帝,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放权给大臣,您只管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奖惩,就可以垂手而大治了,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当然,这种理想化的治国模式是很不现实的,恐怕没几个人能办得到,所以柴荣一向把这类建议当作耳旁风。
对个人能力的自信、对权力的追逐,以及急躁的性格是柴荣事必躬亲的原因,毕竟自己谋划的战略构想、自己制定的方针政策,由自己执行是最有效率也最能保证效果的。
或许正因此,一直积累在柴荣体内的病患才终于集中爆发,击倒了这个志得意满的年轻皇帝,再也没让他站起来。
五月七日,柴荣的病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留在前线了,所有将领都劝他班师回京。
五月八日,在对新占领的关南进行防御部署后,柴荣无奈地长叹数声,下诏班师回京,轰轰烈烈的北伐在一片大好形势中落下了帷幕。
柴荣没有完成收复幽燕的既定目标,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数天后,辽穆宗赶到南京,见后周已经撤军,关南地区又防御严密,就放弃了重夺关南的企图。从此之后,关南地区回到中央政权手中,成为防御契丹的前沿阵地。
五月三十日,柴荣回到京城。此时他的病情愈加严重,身体也更加虚弱,只有头脑还算清醒。他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是时候安排后事了。
柴荣一共有七个儿子,前三个儿子均死在刘承祐操纵的灭门惨案中,后面四个儿子分别是宗训、熙让、熙谨、熙诲。
有这么多儿子,柴荣倒不用担心没人继承皇位,但问题是这四个儿子都出生在郭家灭门惨案之后,所以即便是长子柴宗训,也才七岁。纵观五代前朝,年纪轻轻就即位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善终的,这让柴荣倍感忧虑。
柴荣回想起了先皇郭威。
当初正是郭威在病重之际,拖着羸弱不堪的病体为柴荣扫除了王峻、王殷两大障碍,将他推上皇位,实现了皇权的顺利交接。现在,同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他决定像郭威一样为自己的继承人排除一切威胁。
柴荣首先对最高军政机构进行了调整,任命枢密使魏仁浦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末相),和另两名宰相范质(首相)、王溥(次相)共同组成后周的行政领导班子,分掌大权。
与此同时,柴荣还命宰相为“参知枢密院事”,这意味着宰相获得了军事决策的参与权。表面上看,这是对宰相权力的强化,实际上是通过让更多人参与军事决策来分散权力,避免权力过度集中,这历来是分权制衡的不二法门。
对于这套文人构成的班子,柴荣还是比较放心的,真正让他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将,特别是执掌禁军的将帅——李重进和张永德。
柴荣对这两位亲戚的猜防不是一天两天了。李重进比柴荣年长,性格沉稳,又曾当着先帝郭威的面宣誓向柴荣效忠,柴荣相信他不会违背誓约,但张永德就难说了。
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柴荣的妹夫,年纪比柴荣小,但见识、声望和能力都胜过李重进。特别是在高平之战、征伐淮南、北伐幽燕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张永德的很多见解都与柴荣不谋而合,深受柴荣器重。
柴荣性格强硬,一旦认定某件事情,无论谁劝谏都难奏效,但张永德是个例外。
高平之战后,柴荣曾向众将征求对樊爱能、何徽的处理意见,很多人都主张从宽处理,只有张永德一人坚持要严惩不贷。柴荣最终听取了张永德的意见,痛斩数百名逃跑将士,严肃了军纪。
北伐幽燕患病时,众臣极力劝说柴荣班师,但柴荣仍然不想撤军,甚至闭门谢客,拒绝接见任何人,还是张永德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得以晋见,且成功说服柴荣班师回朝。
可以说,张永德是柴荣最亲近、最器重的股肱之臣。但也正因为如此,当柴荣生命临终之时,他反而成了柴荣最不放心的人,不仅因为他的资历和能力,更因为他的名望与地位。
张永德这个人性格宽厚,待人和气,且长期在军政一线混迹,人脉资源很广。自从显德三年(956年)担任殿前都点检以来,张永德始终掌握着这支最精锐、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亲信故旧遍布禁军,就连赵匡胤都受过他的恩惠。
这样一个人,如果在柴荣死后有所图谋的话,几乎没人可以控制。
退一步讲,就算张永德自己没有谋反之心,也难保他的属下贪图富贵,欲立拥戴之功。柴荣命不久矣,必须对张永德有所防范。而一桩神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柴荣的决心。
在从关南撤军途中,周军中有人报告发现一截木头,木头长约三尺,上刻了五个字——“点检做天子”。
点检,即殿前都点检;天子,当然就是皇帝。顾名思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殿前都点检当皇帝”,而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恰恰就是张永德。
历史上木头说话、石头显灵的异象并不罕见:“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不用想就知道,是有人在偷偷搞政治把戏。
这套把戏放在平时绝对忽悠不了柴荣,但在眼下的非常时刻,为了继承人的安全,为了大周的江山永固,柴荣只能选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柴荣不会对张永德痛下杀手,也没必要这么做。他担心的其实不是张永德这个人,而是他手中的权力,只要解除他的兵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月十五日,卧床不起的柴荣做出决定:免去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一职,由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接替。
对柴荣来讲,这次人事任免是他死前最重要的一项决定,但他不会知道这也是一个最重大的错误,一个自相矛盾的选择。
柴荣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他以赵匡胤取代张永德,是以小概率事件取代大概率事件,因为赵匡胤的资历和势力都比不过张永德,抢班夺权的可能性小得多,但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违反了分权制衡的一贯原则。
柴荣之所以提拔赵匡胤,很大程度是为了牵制李重进、张永德。李重进和张永德素来不和,和赵匡胤也没什么交情;赵匡胤和张永德虽然关系不错,但他是柴荣嫡系,是一名资质才干均不下于张永德的帅才,绝不会轻易受其拉拢。柴荣提拔赵匡胤做殿前司的二把手,也有牵制张永德的考虑。
这样一来,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格局,三人分掌禁军,谁对禁军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又很难打破这种制衡,这无疑是最稳固、最安全的。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最先打破这个格局的正是亲自设计这个格局的柴荣。怀着对命运不公的愤懑,怀着对大周江山的美好期望,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油尽灯枯的柴荣驾崩,享年三十九岁。
柴荣在位五年有余,时间虽短,却功勋卓越、政绩辉煌,以致很多人为他大呼不公,认为他是被历史忽视的杰出帝王。
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柴荣的名字或许不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为人熟知,但知名度从来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柴荣的伟大也不需要以此来衡量。事实上,几乎所有学者都给了柴荣非常高的评价,就连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写就于北宋的史书亦对他不吝赞美。《资治通鉴》高度评价了柴荣短暂却辉煌的一生:
上在藩,多务韬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军,号令严明,人莫敢犯,攻城对敌,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动容;应机决策,出人意表。又勤于为治,百司簿籍,过目无所忘。发奸擿伏,聪察如神。闲暇则召儒者读前史,商榷大义。性不好丝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养成王峻、王殷之恶,致君臣之分不终,故群臣有过则面质责之,服则赦之,有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各尽其能,人无不畏其明而怀其惠,故能破敌广地,所向无前……
司马光评价说:“《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